以独特视角讴歌民族国家意识——15年后重看《大染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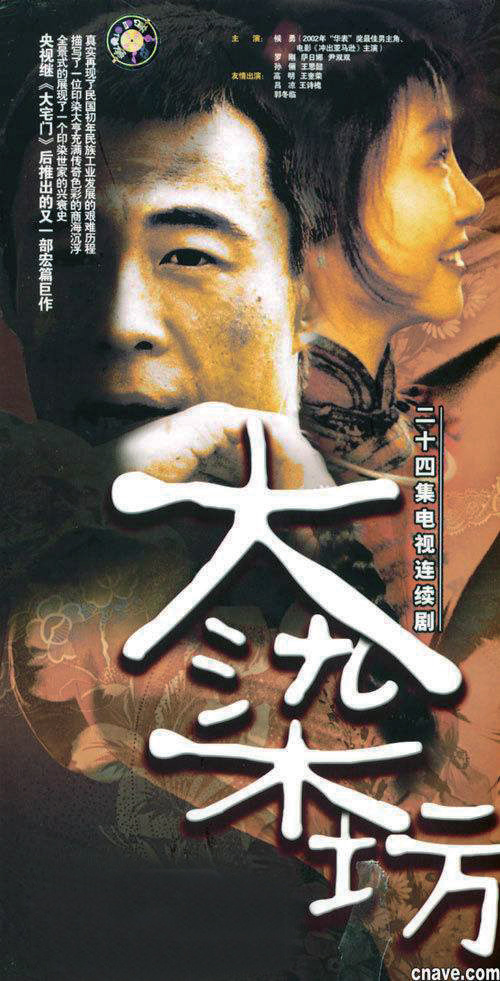
面临新的国际竞争与挑战的世纪之交,中国电视人从民间记忆中追寻中国形象,探索出一条以民间化视角重述历史的“年代剧”之路,同时也体现了他们振奋民族精神的不懈追求。以《大染坊》《闯关东》为代表的年代剧在新世纪之初热播并受到广泛好评,是对他们这一追求的最好肯定。
通过文学艺术建构起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是20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目的是将“个人”整合到“民族”之中,以获得民族认同的同一性。这一使命,在20世纪前80年由小说和电影完成,而电视剧在世纪之交加入到这一队伍中,并凭借其在受众方面的优势一跃成为“想象中国”的主力军。
“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政治形式,而“现代性”所张扬的“求新意志往往导致吉登斯所指出的“历史的断裂”这一“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妙的远景,但此“断裂”势必会带来自我认同的危机,进而发展为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因此,在对现代民族国家进行“想象”的同时,现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们在美学上又表现出自觉地向“传统”回归的倾向。传统文化可以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另一方面,世纪之交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也为民族国家意识的弘扬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如果说近代以来苦苦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国问题”纠结于三大核心:“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单位如何富强,在国际(国族)间的不平等竞争中取得强势地位”,“中国传统的价值理念与西方价值理念的冲突如何协调,民族性价值意义理念和相应的知识形态如何获得辩护”,“如何维护中国传统终极信念的有效性”,而“中心破灭后的重建则成为中国的现代性核心话题”,那么,在世纪之交已发展变化了的时代背景与国际形势下,重提这些“中国问题”仍有其价值和意义。不过,“重建”尚未完成,“彰显”与“推广”的任务又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成为“中国问题”的新核心。正是基于这样的心态和时代文化背景,众多文学艺术家才会在弘扬民族国家意识的现代性追求(同时也是主流意识形态)指引下,主动寻求能够完美融合民族国家意识与传统风格的题材,以集传统与现代于一身的表现手法去构建新的民族国家形象。以《大宅门》《大染坊》等一大批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传统风格的剧作为代表的传统商业文化电视剧的涌现,正是他们为新的“中国问题”给出的一个答案。
同为传统文化,又有“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分野。与同时期的众多古装剧不同,拍摄于2002年的24集电视剧《大染坊》避开了正襟危坐的庙堂文化,选择了更为生气蓬勃的民间立场。其独特艺术魅力就在于有效地以民间视角融合了民族国家意识与鲁商精神,并由此在风云激荡的新历史语境下,重新树立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大染坊》的创作与成功,契合了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两大诉求。其一即是向传统文化回归、以昔日的辉煌构筑今天参与国际竞争的心理优势。主人公陈寿亭的出生地周村地处齐国腹地,齐文化中浓郁的商业色彩和开拓精神无疑是他参与商业活动的最佳指引;自明末以来,周村逐渐发展为华北地区重要的浆染业中心。因此,以艺术方式再现这一重要商业现象、发掘其中蕴含的丰富商业文化,有其重大价值和意义。第二种诉求则伴随着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的消解、商人地位的提升、“商场”成为当今国际竞争主战场的观念深入人心等种种变化,中国商人的形象迫切需要重塑。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神话及其在外敌入侵面前夭折的悲剧,天然地具有戏剧张力和艺术可塑性;同时,民族资本家大多是在传统商业文化浸染下成长起来的,其文化背景中的家国情怀、义重于利、拼搏进取、团队精神等因素,极易与民族国家意识汇合而成为放大这一人群形象的关键点。这些因素,都是受众易于接受传统商业文化电视剧的心理前提。
《大染坊》全剧时间跨度30余年,情节主要在胶济铁路沿线周村、青岛、济南三地展开,尤以济青两地的商战为主。主人公陈寿亭的人物原型即是剧本作者陈杰的祖父,其创作出发点之一便是要让祖父的传奇经历得以传之后世。这种血缘关系天然地打破了一般传记作品创作中作者与传主之间的隔膜感。陈杰基本上是通过家人口耳相传的方式得知祖父经历的,事迹的传奇性和传承方式的口传性,以及他本人的教育背景和业余作家的身份都促使他在撰写剧本时自觉地选择了民间视角,从民间文学资源中汲取营养,从而塑造了一个极富民间色彩的民族资本家形象。
陈寿亭性格特征的关键词,可以概括为豪爽、自信、朴实、仗义、爱国,这是鲁商的典型特征,同时也是古往今来文艺作品,特别是评书、快书、戏曲等民间文艺形式为山东人物形象设置的“共性”。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秦琼、武松等山东好汉的影子。同时,这个目不识丁、只能通过旁人读报纸获取信息的民族资本家形象,与剧中曾留学欧洲、至少也上过国内大学的卢家驹、赵东初等人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了突出这些性格特征,创作者不惜采用漫画式的表现手法。非常突出的一点便是陈寿亭对待“吃肉”的态度。现有的对《大染坊》中“民间性”的评论,多将目光集中在主人公从以评书为代表的民间文化中汲取的营养,或是他对待西餐、咖啡、中式对襟大褂的态度上,却忽略了剧中人屡屡提及的“吃肉”这一细节。在《大染坊》中,陈寿亭对“吃肉”表现出一种近乎痴迷的态度:他的工厂吸引工人的卖点,是顿顿有肉吃;即使因为竞争压力暂时停工,他仍然要求伙房买鱼;当他看到伙房采购食材只买来半片猪肉,会大声斥责采购人员,并且吩咐“从今天开始,每天四片子猪”;而他衡量事物的价值,也往往用肉价作为参照……对于这种心理,创作者让陈寿亭自己做了解释:当赵东初笑话他“动不动就是炖肉,这都什么年代了”时,他坦言:“不管什么年代,这炖肉就是过年”。这种朴素的情感、土得掉渣的语言表达方式,在以往反映民族资本家的文艺作品中是看不到的。对“吃肉”的朴素认知,彰显的是对“白手起家”“勤俭持家”和“富贵不能淫”的认知与想象。
除了“吃肉”之外,剧中还有一个常被评论者忽略的民间文化符号——象棋。在《大染坊》中,象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民间文化元素,它不仅符合陈寿亭的身份,也是陈寿亭商业智慧的重要来源。“一炮巡河,三言御倭”的评价,更是将象棋中体现的智慧上升到了爱国主义的层面。
在剧中,卢家驹曾对陈寿亭说:“你的人格魅力别人是不能比的”,并用“让人放不下”来解释“人格魅力”,无意中点出了陈寿亭这一形象的“卡里斯马”特性。卡里斯马人物的历史原型往往来源于神话传说等民间文学作品,因此,将陈寿亭塑造成“卡里斯马人物”,也是《大染坊》一剧民间性的重要表现之一。而卡里斯马人物的重要作用——对其他人物的威慑、驯化,在剧中则有一种模式化的表现:孙明祖、林祥荣等人起初同陈寿亭竞争,在商战中费尽心机却最终败下阵来,在感受到陈寿亭义薄云天的人格魅力之后,心甘情愿地加入同藤井、訾家斗争的阵营。孙、林在剧作中先是以“反对者”的角色出现,最终转化为“主体”的“辅助者”。这种情节设置,比起让一个形象自始至终充当“辅助者”或“反对者”能获得更大的戏剧效果。
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性”的凸显自然是《大染坊》民族国家意识与鲁商精神的重要契合点,但为了增强剧作的凝重风格,创作者还是将重点放在了民族工业同外族入侵进行斗争的悲壮性上。剧作前半部分的整体基调是轻松的,这与民间化、通俗化叙事模式的采用不无关系,剧中的各处桥段,在民间故事和古典小说戏剧中似乎都能找到其影子和原型;但当剧情发展到济、沪、津、青四地民族资本家联合对抗藤井洋行及其走狗訾家的经济攻势时,剧作的基调立即转为凝重而悲壮。但观众对这一突变并未感到突兀,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观众已经意识到剧情将要发展到民族矛盾激化的时间段;另一方面也与创作者在剧作开始不久便安排藤井登场、早早安排下“草蛇灰线”、酝酿最后的高潮冲突不无关系。这样的结构安排,既符合观众的审美习惯与审美期待,也使作品达到了应有的思想高度,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效果。
导演胡玫曾指出:“日本在战后处在一种混乱的特别萎靡的社会心态里,当时出了一些特别棒的导演,他们拍了一些振奋日本民族精神的片子,把日本男人的魂魄重新加以整理,对振奋当时社会心态起到很好作用。这是他们的功绩,提升了这个民族的精神”。而在面临新的国际竞争与挑战的世纪之交,中国电视人从民间记忆中追寻中国形象,探索出一条以民间化视角重述历史的“年代剧”之路,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大河剧”的启发,同时也体现了他们振奋民族精神的不懈追求。以《大染坊》《闯关东》为代表的年代剧在新世纪之初热播并受到广泛好评,是对他们这一追求的最好肯定。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