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的记忆书写:犹疑于轻重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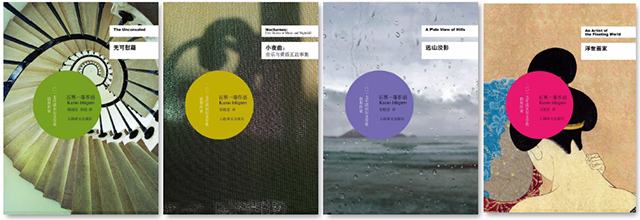
今年的诺奖颁给了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似乎再一次令中国读者大跌眼镜。相比较其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如彼得·汉德克和村上春树,石黑一雄显然没有引起亚洲读者包括中国读者太大的关注。然而,和去年的鲍勃·迪伦相比,这次似乎“正常”了一些。石黑是获过英语文学界的权威奖项“布克奖”的作家。那部《长日留痕》以极为东亚式的精致细腻的叙述风格打动了广泛读者。笔者还记得几年前阅读《长日留痕》时对其精确叙述的感受。与《长日留痕》相比,同样基于“第一人称”个人心中的回声,石黑的《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显示出了另外一种音乐性风格。或许由于其题材和叙述上的多样性,如今再次阅读石黑一雄其他作品,总给人一种在语言品质上的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性恰可能是读者重新全面理解石黑一雄的重要切入点。
闪避重大史实的记忆书写
以《长日留痕》为转折,石黑较早的两部小说《远山淡影》《浮世画家》均以战后日本为背景,讲述了两种人的回忆和生存状态,人物结构大体相似。据作者说,第二部的主人公小野增二恰是从第一部作品中的人物催生而出。《远山淡影》讲述日本战后一对母女搬离到英国之后女儿自杀的故事。小说在叙述上设置了很多暗喻,尤其提到了另一对意欲移民美国的母女,暗示正是女主追忆自身生活的另一幅影子。回忆主体和他者之间实际上是同一个人。在简洁的场景描写中,给人一种凛冽惊悚的感觉。《浮世画家》写战后日本艺术家、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前者相比,他看来不再是受害者,身上却带着国家和社会加之于他的过去的“原罪”。小说围绕日常生活和嫁女风波,同样语焉不详地暗示了战后一代的生存状态。上一代的战争伤痕、下一代移民和流散的伤痕,以及生活文化传统因战败被迫改变的伤痕,主人公们在各自的伤痕中反刍记忆,酿成目下静谧清冷的状态。石黑一雄直接从人物个人生活体验出发,以刻意闪避重大史实的描述方式,营造了某种隐秘的效果。而短篇小说《团圆饭》同样以阴郁的笔调反刍战争和离散的伤痕。渡边先生自杀、母亲的离世以及“河豚”作为一种大受战后时代欢迎的意象,烘托出《团圆饭》背后的人世伤痕。
石黑一雄将小说场景放置在自己的裔地日本,暗含着对于童年“故乡”的回望。战争、移民、新的英式生活的混杂感受,都通过他看起来事不关己的叙述得到纾解。他似乎擅长将自己的作品附着于历史和艺术之上,同时,又闪避这“大历史”,从而造成颇类“私小说”的奇特文风。
新记忆题材的开拓
在此之后,石黑一雄放弃了“战后日本”写作,将目光转向了英国历史,《长日留痕》恰是他题材转型的标志,也是笔者看来他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部小说,他同样用两种时间叙事(记忆与现在)的方式讲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看起来呆板无趣又迷恋自我身份尊严、职业操守的人的故事。结构完整,语言流畅、风格节制而静谧,十分具有艺术感染力。作品反思了个人在历史面前的些微“抵抗”,具有强烈的反讽效果。此后,石黑一雄又写了音乐家主题的《无可慰藉》,殖民素材的故事《上海孤儿》、以及克隆人故事《别让我走》。由此可见,石黑一雄的“野心”很大,他试图自觉驾驭不同题材。
《无可慰藉》讲述一个钢琴家赖德往返于城市旅馆之间演出的亲身经历和心理流动,各种奇遇与尴尬处境,给人一种怪诞疏离之感,体现了作者的孤独、无聊和寂寞。《上海孤儿》则以1937年被日本包围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一个从小生长在上海,成年后成为侦探的人重返故地寻找父母遗踪的故事。石黑一雄试图揭示背后的日本、英国和中国之间的侵略与战争记忆。5年之后,石黑一雄把目光转向了科技造物。《别让我走》讲述了一群克隆少年只能承担器官捐赠命运的惨淡故事。或因其独特的题材,2010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电影把石黑隐秘而残酷的作品风格改造成带有忧伤色彩的英伦爱情故事。结尾女主角凯西说:“我所不确定的是,我们和受赠人的人生是否截然不同,大家一样会终结”。似乎说明了石黑一雄塑造克隆人生背后想要探讨的人性真相。
相比较那些沉重压抑的浮不上来的作品,据说是他在写作《被掩埋的巨人》瓶颈期所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要显得轻松了许多,这些短篇以音乐线索,讲述了不同类型的艺术家的惨淡而荒诞的生活。这些作品如一首首连缀的爵士乐,令读者在接受上也相对自由和轻快了许多。《被掩埋的巨人》则是石黑一雄颇费心血的宏大巨制。他将目光再次聚焦到了公元6世纪的英格兰,讲述了一对年老的不列颠夫妇逐渐揭示“和平”掩埋下利用屠杀来获得统治权的血腥过往的故事。小说以隐喻的方式展示了历史、记忆和遗忘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也是石黑一雄作品中一直延续的“记忆书写”。不同的是,似乎出于更为宏大的叙事策略,作者开始使用第三人称。在叙事风格上跨度很大,会让人想起近日风靡全球的奇幻文学以及相关影视作品。石黑一雄说这是一部“社会和国家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的小说。“仇恨和复仇的意识一直存在,之前只不过被隐藏了而已”,其实,任何国家都存在着‘被掩埋的巨人’”(《如何直面“被掩埋的巨人”——石黑一雄访谈录》,陈婷婷译,2015年)。很显然,石黑一雄善于发掘那些在有机的社会整体秩序之外的存在方式,其中包括移民者、貌合神离的伤痕者、失败的艺术家、克隆人。石黑一雄通过他们独特的存在挖掘人性深处另外的可能性空间,以期反思和质疑现有整体中那些看起来“没有记忆”的正常秩序。正如他在上述访谈中所说:“对于那些你所确认的事,对于那些特别摄人心魄的事情,是需要谨慎考虑的。”或许,这正可以验证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对他的评价:“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相联系的幻觉之下的深渊。”
“理性旁观”背后的内在印记
尽管石黑一雄对那些“内心写作”作家给予怀疑和嘲讽,但关心他的读者可以发现,他作品中一贯打上个人烙印的内面书写。石黑一雄五六岁随父母离开日本。他少年时期一直保持着和日本亲戚的联系,他的祖父和父亲也和他有着良好的关系。33岁时,石黑一雄才重返日本。此时他已写下了那些日本素材的作品《远山淡影》《浮世画家》。也许正是这次“回归”的旅程让他彻底与往昔的日本记忆诀别,回到英国,乃至更广阔的“边际”世界。
石黑一雄的青年时代恰逢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世界从文化到政治上的风起云涌,让他在梦想成为理想主义的文艺青年之外(梦想成为第二个鲍勃·迪伦),开始思考剧烈严肃的世界问题。他曾经在苏格兰做过志愿者,在美国西海岸流浪三个月。期间他目睹了艺术上的流离者,也看到了严酷的底层社会问题。这段观察让他拥有了“一种洞察力”,“让我看出人是多么脆弱”,“人如何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跌倒,又是怎样因此而毁掉了自己的人生”。(《如何直面“被掩埋的巨人”——石黑一雄访谈录》,2015年)在他后来成为作家之后,还能在作品中塑造一个个失败的艺术家形象,但在更深处,吸引他的,或者说挑战着他内在思绪的,则是严肃的社会历史变迁给人带来的伤痕和忧伤的记忆。例如,在小说《别让我走》中,他虚构了一批捐赠器官的克隆人的成长历程,这些克隆人只是一群被利用的“废物”,却仍然能够生长出艺术的毛细血管和爱情的本能,仍然渴望能够像正常人那样生活。恰恰是在这样一种矛盾中让人反思现代性所带来的人的工具化和人性内部之间的深刻矛盾。
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作家固定于一种思维模式是危险的。石黑一雄的小说几乎刻意闪避同一种题材或者写作模式。他善于通过唤醒记忆引发道德力量,善于对国家与国家和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乃至国家和制度内部的记忆进行反思。他以小人物的视角讲述故事,暗示历史与个体之间的不可分割,揭示“罪”与“罚”的共通性。天蝎座的石黑一雄,一如他所景仰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类人性深处的罪恶与良善有着天然自觉的质疑与思考。他说:“世界并不尽如人意,但是你却可以通过创造自己的世界或者对世界的观念来重组世界或者适应这个世界。”很显然,石黑一雄开拓的各种论题,对于人类重新认识过往,从而继续向前具有带反思意味的警示作用。
缺陷:犹疑于轻重之间
石黑一雄不断地寻求多变的题材,自觉地寻求突破,在叙事上独具风格,善于回望历史事件对于个人经验的渗透。他不是那种热衷于讲故事的线性叙事者,而是使用了偏离、分裂、矛盾性的叙述风格,沉迷于给读者营造一种奇怪的欲言又止的氛围。
总体而言,这些作品在水平上可说是参差不齐。他的故事常常是冷漠和不温暖的,即便是温暖,看起来也是类型化的、僵硬的,是不可爱不活泼的。例如《浮世画家》中,叙事随着记忆的符号流动,淡淡地、闪避地传达一种暗喻式的个人命运和时代的暧昧纠葛。这种断裂式的写法,往往不是出于作品中人物情绪和发展的需要,而是作者出于制造神秘感或者痛感的需要而“安排”的。他的作品人物并不能应对这样的宏大素材,给人一种无力的软绵绵的感觉,同时也无法以一种轻盈的张力来强化主题。一切都是轻微的梦幻般的行动。即使作品中看起来较为明丽与温柔的人物,如《远山淡影》中的“悦子”、《浮世画家》中的“节子”,也都似曾相识,仿佛让人回到了小津安二郎影片中某种静谧的“原节子式”的风情。又如作品中的小孩子,如《远山淡影》中的万里子、《浮世画家》中的外孙一郎,身上都有某种冷漠诡异的个性,孤独、寂寞,身份感紊乱,散发出“被迫的”压抑气息。那些漫溢的无聊的生活细节代替了人物塑造,使得后者显得异常平庸。《远山淡影》《浮世画家》充斥着一种无能的力量,正如作者在文中使用的隐喻地名“犹疑桥”一样,摇摇晃晃,缺乏力量。石黑一雄曾自称常用旁观的态度看待英国,因为身份特殊,在成长过程中一直打“日本牌”,可他自己却又是一个毫不懂得日语的人。有人认为,石黑一雄是一位非同寻常的“读者——敏感”型作家,他高度地认识到身为代言人及表现不断增长的混合性世界村落的责任。(钟志清编译:《寻觅旧事的石黑一雄》,1994)
到了《被掩埋的巨人》,故事叙事节奏上断裂、人物同样无力、故事情节上“似曾相识”,即使转换了人称,也并没有“讨好”他起初建立的带有更深层次的历史伦理框架。甚至被人称作“老虎空有捕获大象的志向却误入了花丛”。(瘦竹:《评〈被掩埋的巨人〉》,2016年)。所以,小说中所讨论的问题,无论是代际的价值观(《远山淡影》《浮世画家》),还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争论(《被掩埋的巨人》),都显得不那么理所当然。
很显然,石黑一雄并不是那种纯粹的体验型作家。他从写作技艺和素材的需要出发,用极为寡淡和平常的风格,对人物刻画采用一种闪避的方式,缺乏渲染的热情。正如村上春树曾以隐晦的语言评价他说,他的作品“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拥有某种远大眼光,有意识地将某些东西综合。将几个故事结合起来,以期构筑更为宏大的综合故事”,“那种稳扎稳打、累积起一个个种类各异的世界的踏实工作,我唯有怀抱深深的赞赏之心”(《与石黑一雄这样的作家同处于一个时代》,2010年)。尽管石黑一雄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在市场化的时代只适合英国或其他国家的小众读者阅读(2008年,德国《时代报》,安娅译),但相信他的有意无意的丰富题材,使得其作品在通俗、多元文化背景下将更受欢迎。
石黑一雄在接受采访时曾坦白自己的创作很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勃朗特的影响,这暗示了他将人性之罪融入日常生活的表现手段。与契诃夫的“日常”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性”相比,石黑一雄作品中的人物缺少力量,往往不像前面二位作家那样能自觉营造故事氛围,却造成一种稍显刻意的碎片式的语言风格。这种碎片式的语言风格却往往构不成艺术上的“疏离感”,进而给人一种“出戏”的感觉,包括他尝试的科幻、生物技术的题材,也似乎缺了些什么。相比之下,英国文学里,经典如D.H.劳伦斯,先锋如杰夫·戴尔,身上同样能够看到带有某种绝望、荒诞、忧郁氛围的记忆书写;但同时,又能够从他们身上找到持久的深情和一种文学上的轻盈。与他们相比,石黑一雄压抑到了浮不上来,细腻到了琐碎。
然而,基于石黑一雄在英语读者群里盛大的荣誉,但愿正如他所说,他的作品只适合一部分英国读者阅读,他的那些看起来并不成功的作品,可能是基于翻译和不同文化背景所导致的结果,而不是石黑一雄的文学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