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风格与《被掩埋的巨人》的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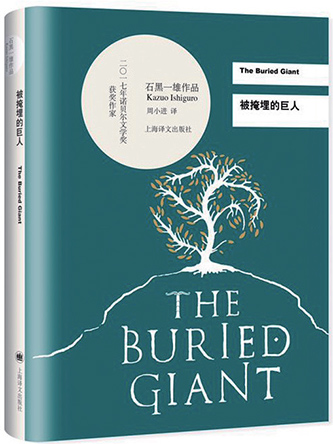
普通读者了解石黑一雄,可能是在他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实际上,国内研究英美文学的学者早已非常重视石黑一雄,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就开始关注他的文学创作。出版界也非常关注石黑一雄,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已出版中文译本,不过总体上,石黑一雄的作品在国内并不畅销,书卖得“不好不坏”,和村上春树的作品无法相比。可以说,在获诺奖之前,石黑一雄的中国读者群基本限于小众和专业研究者的范围之内。而在国外,他的读者群体则要庞大许多。《长日留痕》和《别让我走》都销售了百万册以上,超出了不少诺奖得主的新作。
35岁获得英语世界最高的布克奖,62岁获得诺贝尔奖,这在文学界是不多见的。石黑一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专业写作,文学之路可谓走得一帆风顺。好在他对这点早有清醒认识,名气越大,他的写作越严谨,最初两三年出一本小说,后来相隔5年,最近的一部小说《被掩埋的巨人》则打磨了10年。与奈保尔、库切等诺奖得主相比,石黑一雄的写作速度慢得多。
我开始翻译石黑一雄的作品是在2014年,当时上海译文出版社已经获得他所有作品的版权,包括尚在修改中的新作《被掩埋的巨人》,这是他阔别文坛10年后的作品。3月,译文社编辑联系我翻译此书。我拿到的书稿上明确标识着“第11稿”的字样,经纪人发到全球各语言译者手里的,就是这个版本。该书的英文版首发时间定在2015年3月,中文译本最终于2016年1月出版,这个速度算是相当快了。
《被掩埋的巨人》全文大概只有10万英文单词,我有一年半的时间来翻译,应该说是比较充裕的。实际上,真正用于翻译的时间却短得多,大半年的时间都花在反复阅读原作上。我之前读过一些石黑一雄的作品,还看过根据他小说改编的电影,对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也有所关注。根据我对他以前作品基调和文字特点的理解,觉得再现他的风格可能是翻译中即将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前期花了很多时间去揣摩和体会。
在作品主题方面,石黑一雄常常把人的过去和现在、民族的历史和当下杂糅在一起,主要人物不多,情节简单,几个人一起去做一件普通的事情,比如旅行,但是随着故事展开,这些人物的过去、群体记忆、民族历史等,都会逐渐呈现。从根本上讲,石黑一雄是把人放到宏大的历史和漫长的时间中去写。他的视野不仅跨越国家、民族,也跨越时间和历史,因此,他的作品总笼罩着一股伤感、悲观、宿命、无奈的情绪。给人的感觉是,在作品开头看到几个大大的人,随着镜头在时间、空间上越来越远,最后读者看到的,不过是无限空间中的几只小蚂蚁。
在叙事风格方面,石黑一雄的大部分小说中都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作者进入一个人物的内心,再借用这个人物的口吻,娓娓道出故事,细腻、亲切,但往往很不可靠。这不是因为人物在撒谎,而是随着故事的推进,讲故事的人慢慢显露出他的狭小和无助来。讲故事的人能吸引和感动读者,只是作者石黑一雄已经在他背后慢慢展开了一块硕大的历史幕布。
从文字层面上看,石黑一雄是个文体家,文风独树一帜,有时不看作者也能猜出是他的手笔。他的语言朴素,几乎不用复杂的意象和修辞,不用华丽的词藻和铺陈,而是更喜欢用动作和对话。初次读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重复读下来就越来越有味道,思考和感受的空间也越来越大。他用词简单平实,中国读者如果阅读原著,只要英文尚可,恐怕不需要频繁地查字典;他的句法往往也不复杂,一个句子跨三行就算比较长了。他行文喜欢用名词、动词,使用形容词却很谨慎,有点像海明威,经常用对话去推动情节、塑造人物。
考虑到石黑一雄作品在主题、叙事和文字上的特点,我在翻译的过程中特别注意风格的再现。我以前翻译的一些作品,或遣词造句华丽繁盛,或修辞手法丰富新颖,或有很多特定地域特定文化的内容,需要花很多工夫去查阅资料,推敲中文的表述,必须经常在“增”与“减”、“异化”与“归化”之间找平衡。但《被掩埋的巨人》不同,主要的挑战在于风格等值,这不是局部困难,而是作品全局性的问题。译者心里要一直放着整本书,综合考虑主题、风格、情节、视角,当然还有文字的表层意义。风格的重现是个很微妙很考验人的过程,不同的译者很可能有不一样的处理方法,也是比较能体现译者主体性的地方。
《被掩埋的巨人》用词简省,全书不过10万字,石黑一雄却花了10年写就,相信是经过字斟句酌。何况我拿到的稿子已经改过11遍,所以翻译时在文字上一点儿也不敢马虎,多少有些诚惶诚恐。翻译过程中,通过出版社和他的经纪人,我又陆续收到他的一些小修改,从中也能看出他对文字的考究。后期的修改一共十几处,主要有几类。一类是偶尔的拼写或语法问题。一类是名词或动词的改动,例如用“seat”(座位)替代“chair”(椅子);用“raiders”(劫匪)代替“Norseman”(挪威人)和“Viking”(维金海盗);用“crops”(庄稼)代替“potato”(土豆);用“barred”(拴住的门)代替“locked”(锁住的门),因为5世纪的英格兰可能还没有椅子、维金海盗、土豆、锁等概念,这些主要是让用词更符合历史情况,基本上都是作者根据其他人提出的意见修改的。
还有一类后期改动特别值得注意,是石黑一雄自己做的修改,主要是删除几个形容词。例如第11稿中的“one(smell) of old slaughter”(旧日杀戮的气息),后来删除了“old”。到第11稿还要删除形容词,算是比较大的改动了,这也说明了石黑一雄对风格雕琢的在意和极强的文体意识,只是最终的文字平易自然,不太容易看得出来。我在翻译时,一直绷紧一根弦,基本上不“增”,太书面的表述、四字格、长句等的使用都很谨慎,比如原文是“树”,就不译成“大树”或者“一棵树”,原文是“亚瑟”就不译成“亚瑟王”。
在句法层面,我尽量避免繁杂的长句或急促强烈的短句,除了几个比较紧张的打斗场面之外,尽力保持语调的舒缓流畅,原文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希望译文也有类似的阅读感受。这一点有时候可以通过标点符号实现,或者添加“吧”“啊”等语气词,或者寻找更精练的汉语词汇,或者调动语序,但实际翻译中往往更灵活微妙,一定程度上要依靠对风格和文字节奏的把握,没有定法,大量对话的处理尤其如此。
翻译过程中,另一个与风格相关的考虑是石黑一雄的叙事技巧。《被掩埋的巨人》虽然文字平实,叙事层次和角度却极为丰富繁杂。有时候短短一句话,就能划出几个时间层次来,一举击破时间的线性,将读者专注当下的目光强行拉开。比如全书开篇第一句:“要找到后来令英格兰闻名的那种曲折小道和静谧草场,你可能要花很长时间”,表面上是传统的开场,要写故事发生的地点,实际上写的是漫漫的历史长河:今天作为读者的你、“小道和草场令英格兰文明的”现代、故事正在发生的远古,三个时间段划得层次分明却不露声色。用第一人称叙事,还邀请读者“你”入场,却没有第一人称常有的现场感和参与感,惟余历史的纵深。在翻译中,处理这种情况主要是处理时间问题,中文里没有时态,要在短小的文字空间里表达出时间的层次,又不能过多地增词而损害风格,有时也颇费脑筋。
在《被掩埋的巨人》中,时间就像一个一直在场的人物,如同哈代笔下的自然。人物的视角在现在和过去之间穿行,当下的事情在缓缓发生,过去的记忆却层层叠叠,像不息的暗流漫上来,淹没了当下,最终裹挟着当下滚滚而去。石黑一雄一面邀请读者听他慢慢讲述一个故事,一面把一切都扔进时间的长河里,包括他的故事,包括人物和人物的记忆,表面上却假装生活平淡、一切照常。很多作家写的是人物穿过历史,石黑一雄写的是历史穿过人物;很多作家写的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写的是历史的车轮在原地重复碾压。从哲学上讲,这其实是一种很可怕很绝望的存在体验。这种视野似乎有着非常深刻的东方哲学渊源,在西方作家中并不多见,可以说这就是他作品的基调和风格吧。谈到音乐时,石黑一雄曾说,他最喜欢的音乐,是歌词欢愉但唱得忧伤,大概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描述《被掩埋的巨人》。
译无止境,石黑一雄获得诺贝尔奖,中译本要面临更多读者的检验,作为译者,我内心多少是有些惶惑的,相信这种感觉,所有的译者都很熟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