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下的旅人》(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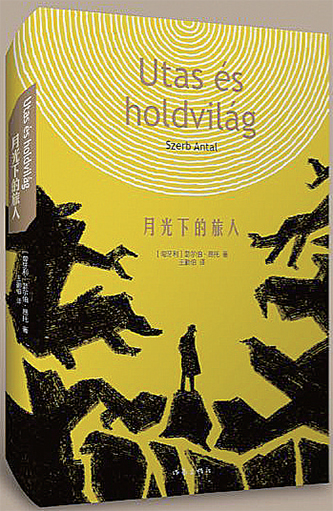
回到屋里。
“先休息一下,然后再决定我到底想要什么,或者说我是否真的想要那些什么,只有确定以后,我才会给艾娃写信。我对她的态度变得有些怪怪的,若是我告诉她昨晚为什么不回家,恐怕她根本不会相信,那实在够荒唐。”
无意识地脱下外衣,他开始洗漱。“洗漱还有什么意义吗?”但他只犹豫了一瞬间,之后接着洗漱,沏了茶,捧起一本书读了一阵,躺下睡过去。
他在门铃声中醒来。匆忙下床,感觉一身轻松,恢复得不错。刚才下过了雨,不像前些天一样热。
打开门,进来一位老先生。是父亲。
“你还好吧,我的儿子。”父亲说,“我坐火车中午到的。真高兴你在家。我现在饿了,想你跟我去吃午饭。”
父亲毫无预料地出现,让米哈伊无比惊讶,但他内心最强烈的情绪并不是惊讶,也不是窘迫和羞愧——当父亲环视房间并努力在脸上不表现出对他身处的穷陋环境的恶心。另一种强烈的感受占据了米哈伊内心,这种感受是他早年常去国外时每次归家后总会些许体验到的。离开较长时间再回去,他总是带着同样的恐惧发现父亲更老了。但父亲没有、从没有像现在一样老。最后一次见到他,他仍然是那个举止威严、富有自信的男人,一辈子熟悉的模样。或者至少米哈伊的印象如此,这些年他一直住在老家,察觉不到父亲身上缓慢发生的变化。现在,相隔几个月之久,他清晰地注意到了。岁月侵蚀了他的面容和形体,尽管痕迹还不够深刻,却已不可否认地展示出他的老去:他的嘴形已失去一贯的坚固,双眼疲惫憔悴(当然,他坐了一夜火车,按他一贯的节省,可能是三等车厢),头发更白了,吐字不再那么清晰,甚至有些口吃,初次听见很是吓人——或许有不精确之处,但残酷的事实摆在眼前:父亲已完全是个老人。
和这些相比,艾娃,他寻死的计划,甚至意大利本身,全都显得无足轻重。
“我不能掉眼泪,现在不能。父亲会加倍瞧不起我,且他有可能猜出我是为他流泪。”
他定了定神,摆出一副最中性无表情的面孔,每次面对家事他都会摆出这副面孔。
“父亲,非常感谢你来这里。大夏天的,你跑了那么远,肯定是有特别重要的原因。”
“对,我的儿子,特别重要的原因。但也没什么坏消息。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尽管你没问起,我还是要跟你说你母亲兄弟妹妹都很好。我看得出你也没有特别严重的问题。现在我们去吃午饭吧。你带我去个素净馆子。”
“爱尔琦和波托基·佐尔丹前天来找过我。”父亲午饭时说。
“什么?爱尔琦在布达佩斯?他们在一起?”
“对,波托基去了巴黎,他们和好了,他把爱尔琦接回了家。”
“但为什么?怎么会这样?”
“我的儿啊,我不可能知道,且你也能想得到,我不会去询问。我们只是谈了生意上的事情。你很清楚,你的行为……怎么说呢……你如此古怪的行为,尽管我也不那么吃惊,却让我在爱尔琦面前处境非常难堪。非常麻烦的财务问题。就现状而言,几乎没有可能清算股份还钱给爱尔琦……但你应该也知道这些,我想提沃多尔在信里都说过了。”
“对,我知道。你恐怕不会相信,我一直担心得要命,总在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爱尔琦跟我说佐尔丹……还是你接着说吧。”
“感谢上帝,没发生不好的事情。他们来找我就是商量怎么撤资。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非常有灵活性,就连我自己也惊讶不已。我们在所有细节上都达成了一致。他们没有半点催促之意,我也希望我们能顺利解决这个问题,不必面对更大的麻烦。而且,最近你哥哥彼得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新客户。”
“但佐尔丹,就是波托基,他态度真的很好吗?我不太明白。”
“他的表现绝对绅士。私下里说,我觉得,爱尔琦回心转意让他欣喜若狂。他当然也是在遵照爱尔琦的想法。爱尔琦是个真正体面的女人。米哈伊,真得够可恶才……好吧,我已发过誓不对你进行斥责。你一直是个不一样的小孩,你清楚自己都做了什么。”
“佐尔丹没有说我坏话?他没说……”
“他什么也没说。压根儿没提起过你,在当时的氛围里,这也很正常。爱尔琦倒是说到了你。”
“爱尔琦?”
“对。她说在罗马和你见过面。她没告诉我细节,我当然也没多问。她说你现在的情况很危险,你认为全家人都和你翻脸了。不,你不用解释什么。我们家里人一直慎重对待各自的私事,我们得继续这样。我不想了解任何细节。只是爱尔琦建议,若有可能,我亲自来趟罗马,劝你回布达佩斯去。用她的话说,我来接你回家。”
接他回家?是的,爱尔琦太了解米哈伊,一语中的。她肯定父亲能把米哈伊像个逃课的学童一样领回家。她也一样清楚,米哈伊的天性里有服从的倾向,他会像一个犯错被捉的男孩一样表示服从,但同时内心又有保留,以后有机会再跑。
聪明绝顶的爱尔琦。除了回家,他已没有办法。可能还有一条路,然而……他想通过死亡去逃离的外部因素,看上去都已消失。佐尔丹心满意足了,家人焦急地等他回去,没有人想要迫害他。
“所以我来了这里,”父亲接着说,“我希望你立即全部了结这里的事情,今晚就和我一起坐火车回去。你知道,我没有太多时间。”
“不好意思,这件事对我太突然了,”米哈伊说,从恍惚中回过神来,“今天早上我想到了很多事情,唯有回布达佩斯没想过。”
“我明白,但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想回家呢?”
“没有,只是请让我缓口气。你听我说,你现在去我住处休息一下也不差,睡个午觉。我同时可以整理一下思绪。”
“好吧,随你便。”
米哈伊整理好床铺让父亲躺下,自己坐到大扶手椅里,开始仔仔细细地反思。他的做法是回溯各种感受,考量它们的强度。他习惯于这样去确定自己想要什么、可能想要什么、有没有可能去要。
他真的想死?他还想像托马西一样死?他回忆起这一欲求,寻找与之相连的甜蜜。但他感觉不到任何甜蜜,相反,是倦腻和疲惫,好比性爱结束后的感受。
他又意识到为什么有此倦腻,因为他的欲求已被满足。就在昨夜,那户意大利人家里,他在恐惧和幻象中实现了少年时代以来困扰着他的欲求。尽管外部现实中什么也没发生,但在内心的现实里他却已完全经历过了。因此,他已算满足,尽管可能不是永永远远,但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已从这一点、从托马西的鬼魂里解脱出来。
艾娃?
他注意到书桌上有一封信,出去午饭时被放到那里的。该是昨晚就到了,但隔壁女房东忘了送过来。他站起来,读着艾娃的告别信。
米哈伊:
你读到这封信时,我已在前往孟买的路上。我不会来找你。你不会死。你不是托马西。托马西的死只属于托马西,每个人都得找到自己的死法。
上帝与你同在。
艾娃
晚上,他们确实坐上了火车。谈着公司里的事情:父亲讲述着米哈伊离开这段时间公司里发生的事情,接下来的各种动向,以及考虑为米哈伊指派什么样的新职责。
米哈伊聆听着。他要回家了。他将去尝试15年以来从未做成的一件事:从众。或许这次能做到。这是他的命。他投降了。他逃不掉。他们都比他更强大:父亲、佐尔丹、公司、所有人们。
父亲睡着了,米哈伊看着窗外,想在月光下分辨出托斯卡纳群山的轮廓。他得继续活着。他得活下去。他也会活得像废墟里的耗子。但毕竟是活着。只要人活着,总还有可能发生点什么。
(摘自《月光下的旅人》,作家出版社出版)
只要人活着……
让我们先看看作者的照片。眼睛紧紧箍住智慧的额头,像一个大学文学教授。
他就是大学文学教授。(或者不是这样?或许他更像一个永远的局外人?)
他写过关于匈牙利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的专著,文思精奇。直至今日,高中生仍在对其专著死记硬背,高中生的父亲则像看小说一样重新翻阅它们。书名就是《匈牙利文学史》《世界文学史》,这两本书在匈牙利如此受欢迎,以至于这位小说作者时不时被掩盖了。瑟尔伯有生之年亦曾对此有所知觉,他在日记里写:“令我难受的是,人们总说我是文学史专家。我是作家,我的主题暂时是文学史。”
“一副神秘莫测的开朗面孔,一双令人不安的无辜眼睛”,一位文学批评者这样写道,而且,他这幅寻常大学教授的肖像里有着某种“靠不住”的东西。
我认识一个女人——我本也可以写更多关于她的后记——她说,《月光下的旅人》对她就像一个彩色玻璃球,随着光线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她14岁时读到本书,对环意旅行兴趣浓郁,确实如此,我们跟随着米哈伊在意大利四处旅行和寻找——寻找什么——当然是寻找我们自己!24岁时,她被死亡主题吸引,那时她并不惧怕死亡。34岁时,她在周边朋友身上找到了书中人物原型,从一个也是胸部巨大的朋友身上似乎看到瓦妮娜,又从另一个身上透视出瑟佩特内奇,大话连篇的家伙,肚子里总是有什么话可说,还透视出那个神秘的波斯人,一头勉强被驯服的老虎,诸如此类,不再列举。44岁时,她又读了一遍这本书,现在她关注的是书中语言,一种气质高贵、旋律悠扬、深入心扉的轻音乐。
瑟尔伯属于高贵的匈牙利作家之列,和他同龄的马洛伊也位于其中,当然,还有高贵中的最高贵者:科斯托拉尼。
让我们来做比较文学:就像提早70年听说布鲁斯∙查特文。小说章节的断点就像莫尔纳尔 的戏剧,或者像昆德拉小说的结局。像翁贝托∙艾柯在上小节思想、文学和艺术史课,如此轻松随和,如此信手拈来。
只有在英国小说里能读到这种简洁、扫射又可亲的句子,例如:“……她去了巴黎,所有在绝望之中想开启一段新生的人都选择去那里”。或者这样美妙的句子:“我可不喜欢和其他人不同的人。其他人是够恶心的。但和他们不同的人也不例外。”
这是一部“艺术小说”,内文佳句成堆。
想象中的、或令人无限沉思的小说中心人物是乌尔皮厄西·托马西,少年时代的挚友(或挚爱)。他和艾娃就像(又一次就像)出自让·谷克多的《可怕的孩子们》。一切都围绕着托马西。他是我们内心渴望的目标,他并不存在,但他存在过。他是怀旧的对象。
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像瑟尔伯一样让我看到这样清晰鲜明同时又残酷无情的怀旧,这份怀旧与善感无关,更非矫揉造作的媚俗,不是从记忆中啄出的美好葡萄干,他的记忆是一切,关于乌尔皮厄西家大大小小的一切。这样一份怀旧在整体上是一份激情又痛苦的记忆,亦从未被企及。
米哈伊在自己身上发现人类。或者是文明人在此处发现尚未文明化的先祖?在他们身上,死欲尚未被对死后世界的向往淡化。在他们身上,厄洛斯和桑那托斯仍然手牵手并肩而行……
米哈伊游移在对成人世界的怀疑和对世界孩子气的渴望之间,也持续面对着来自庸俗的威胁。这就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人。这本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变体。“他不可理喻地承受了他未曾承受的一切”,瑟尔伯曾在一部短篇小说中写道。
这本书在匈牙利如此受欢迎,无论是对人类有爱的人,对自己有爱的人,对存在有爱的人,还是对学术有爱的人。当然还有对生活有爱的人。对爱情,对死亡,对精神,对疯癫,对往昔,对文明。一部伟大的情爱小说。
瑟尔伯把我们带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古老的世界——并不是由小说主题或情节带入,而是他的语言,他的思维方式,他的视野,他的理性神秘学,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时不时买顶新帽子,但没有愚笨的回响,也没有刻意的戏仿,从一本书的角度来说,它兼具向导性、教育性和娱乐精神。
当你已把这本轻灵空旷的书读到尽头,当我们愉快的讲座走到结尾,一个锐利的小问题却劈头盖脸不请自来:我们现在将如何面对生命中的躁动,充满激情的躁动,它有时被称作爱,有时是不适。
我们的耳朵里是小说最后一句话:“只要人活着,总还有可能发生点什么。”
(本文为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为德语版《月光下的旅人》写的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