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塔菲耶夫《鱼王》:造化有时 万物有期
来源:文艺报 | 于明清 2017年09月04日07: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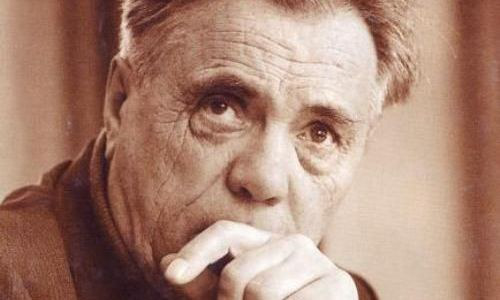
阿斯塔菲耶夫

自然,是《鱼王》中最鲜明的形象,也是这部作品给人最深切的感受。《鱼王》是维克托·彼得罗维奇·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的短篇叙事集,单行本出版于1976年,作品令作家荣膺1978年的苏联国家文学奖。小说本应由13个篇章组成,但在出版时被书刊检查机关删掉了两章:“达姆卡”和“没心没肺”。前者很快获准刊登,后者按当时检查人员的话说,“200年后才有机会见天日”。苏联解体后,小说终得以完整面世。近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版《鱼王》中译本发行,终于让小说在问世40余年后,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再度获得圆满。
《鱼王》是一部描写自然与人的作品——自然在前,不是人与自然,这是作家多次强调的次序,也与中国道家对道、天、地、人四者的定位有相通之处。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主题颇为丰富,自然、社会、战争、道德、爱情、宗教等等均有涉猎。这些主题里,自然占据着某种超然的地位。作家的主人公们往往将大自然当作治愈创伤的场所,《忧伤的侦探》里,索什宁的女儿身体羸弱,但是一离开城市,来到村庄里就变得健康好动。《该诅咒的与该杀死的》之中,德国军人与苏联军人只要脱下军装的束缚,在河里游泳,马上变回平等互动的自然人。自然离开人,依旧岿然不动,可人离开自然,便会有所缺失。《牧童与牧女》中的德军将领在作家眼中不过是个被迫与土地分离的可怜农民。《鱼王》里的集体农庄建设需要农民大规模迁徙,这在阿斯塔菲耶夫看来并不具备正义感,因为它导致人与生身之境的分离。
自然是《鱼王》里的精神家园,是信仰所在,是一个可以代替教堂的神圣地方。短篇《一滴水珠》的标题就具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意味。这滴饱满凝重的椭圆形水珠垂挂在柳叶的尖梢上,映照出静谧到极点的世界。嘈杂的社会被挡在了叶尼塞河的另一边,水珠折射出没被撼动过的原始森林,尊重森林法则的猎人在静默沉思中寻求与自然的交流,感悟生命、信仰的意义。五彩斑斓的生命没有因为夜晚的漆黑而褪色:黑貂在树梢上奔走;大雷鸟钻进花花绿绿的树丛,去孵花花绿绿的蛋;火红色的北嗓鸦从树枝上拧下了淡紫色的雪松果;灰色的鹡鸰钻进红茎花冠的花丛里去吃昆虫。幽暗的夜色中,人们看不到,却借助灵性的眼感觉到了这些美丽的色彩。在原始森林的星空下,人们凭借对自然的内心感应,感到“极顶的寂静和新生婴儿在诞生之日囟门上的搏动”,仿佛看到“独一无二的圣灵在世上翱翔的刹那来临了”。作家说:“在这天堂般的宁静里,你会相信有天使,有永恒的幸福,罪恶将烟消云散,永恒的善能复活再生。”西伯利亚森林的纯净夜色、星空为人类提供了一个逃避尘俗的庇护所,仿佛是接近终极实在的一个不可侵犯的圣地。人们通过凝视滔滔巨浪、仰望午夜星空而获得的敬畏和谦卑感绝不亚于在教堂中所得。“星星那神灯样的光辉,那种神秘莫测的超凡拔俗,总会在我的心里引起一种夹杂着痛苦和忧郁的慰藉。如果有人对我说‘彼岸世界’,那么我想象的不是什么阴曹地府,不是黑暗,而是这些微弱的、遥远的、一亮一亮的小星星。”宗教起源于对自然的敬畏,抛却不同文化赋予信仰的窠臼,回归自然,也许才能直达信仰的本质。
自然是《鱼王》里的物质家园,人类的生身之境。它在《鱼王》一篇中有了具体的化身——一个具有性别、不容亵渎的女性形象。这个短篇的两位主人公一个是代表自然、代表海洋的鱼王,另一个是高人一等的渔夫伊格纳齐依奇,人类之王。伊格纳齐依奇在叶尼塞河里下的排钩勾住了一条大鱼,但在捕鱼的过程中他自己也被排钩拽到水里,差点和大鱼同归于尽。传说中隐身在大河深处的鱼王,如今出现在钩子上,它的两只眼睛“光秃秃的,没有眼睑,没有睫毛,像蛇一样冷漠地盯着人看,隐含着某种深意”。鱼王撞上人的排钩,也把人拽进水里。“河流之王和整个自然界之王一起陷入绝境。守候着他俩的是同一个使人痛苦的死神。”食物链上,鱼和人之间似乎有千山万水,远得可以忽略二者的关联。《在黄金暗礁附近》一篇中,柯曼多尔曾经居高临下地嘲笑鱼的痛苦。“鱼儿会哭泣吗?谁又能知道呢?它在水里本是湿的,即使哭泣也看不出来,而且它又不会叫喊。要是会叫喊的话,整条叶尼塞河,而且何止是叶尼塞河,所有的河流和大海岂不要吼声如雷。”他在想这些的时候,心里泛起的并非同情,而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得意:既然鱼儿不会叫喊,它们就活该无声无息地死去。但是,在这条简单的排钩上,在这个缩短的链条中,我们却读到,鱼的痛苦和人的痛苦如此接近,人类与自然只能选择共生或是共死。在失血的迷狂状态中,在昏黄色的灯光里,伊格纳齐依奇终于低下高傲的头,开始忏悔自己的罪孽。鱼王细皮白肉,胖鼓鼓的、柔软的肚子含有某种女性的意味,让他想起曾被自己玷污的女友格拉哈。面对格拉哈,伊格纳齐依奇一直怀有强烈的罪恶感,他曾用各种方式希望得到格拉哈的谅解,但都没有成功。从此,他不再对任何女性动手动脚。侵犯女性在他看来是沉重的罪孽。“你要承受全部痛苦,为了自己,也为了天地间那此时此刻尚在作践妇女、糟蹋她们的人!”作家所说的“她们”中显然也包括特殊的女性——鱼王。伊格纳齐依奇在潜意识里已经将鱼王和格拉哈相混淆,分不清自己“在这河上干什么?等待饶恕?等谁饶恕”。他对格拉哈的愧疚自然地转移到了鱼王身上,而鱼王是作为水族、自然界的代表出现在这场争斗中的。格拉哈、女性、鱼王、自然,这些形象合而为一后,伊格纳齐依奇终于确认:“大自然也是个女性!”他也确实侵犯了大自然,“你掏掉了它多少东西啊。”侵犯女性是一种罪孽,侵犯大自然同样是罪孽。这样,阿斯塔菲耶夫就把大自然纳入了人的道德体系之内。雨果曾断言,在人与动物、花草及所有造物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完整而伟大的伦理,这种伦理虽然尚未被人发现,但它终将会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人类伦理的延伸和补充。从人类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伦理学的进步也可看作是平等程度的增加和应用范畴的扩大。从封建专制到民主制度,从男人享有专权到妇女解放运动,每一次平等范围的扩大都代表人类的进步。在《鱼王》里,阿斯塔菲耶夫这个权利扩展到人类范围以外。在人的忏悔中,鱼王伤痕累累地没入水中离去,大自然似乎暂时与人类达成和平。而在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里,人类无法毁掉树王,只能自欺欺人地将它没入水下。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里,母狼阿克巴拉一家虽然殒命,但是月亮中的狼神比尤利·安娜依然在孤独地嚎叫。这些隐身于天地中的自然神和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一样,沉默地守护着孕育了人类生命却因此受到伤害的自然界。
自然在《鱼王》里拥有人的化身——阿基姆。在《鲍加尼达村的鱼汤》一篇中,我们结识了这个作家笔下最完美的自然人。阿基姆似乎只有自然性的一面,其社会性的一面则被作家有意抹去。“在鲍加尼达村出生和长大的小阿基姆,上学读书之前从来也不知道世上还有其他的村镇和居住地。他从来没在哪儿受过洗礼,从来没有一本花名册上登记过他的名字,他是自由自在地来到这个世界的。”从阿基姆身上,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于大自然的赞美和尊敬,对戕害人类本性的所谓现代文明的否定和拒绝,对物质财富冷酷无情地追逐的厌恶,对接近自然的田园生活的向往,对人性复归自然,同自然和谐相处的渴求。阿基姆是个热爱自然的人物,是一个狩猎能手,对森林了如指掌,了解自然的法则,能同荒野和睦相处。他在大自然中学到了一系列的美德:怜悯、谦恭、勇敢和忍耐。他不计代价地拯救艾丽雅的生命,把最珍贵的药毫无保留地用在她身上,把最好的食物送到她面前,尽管对方只是个素不相识的自私的人,最初对他的牺牲并无感激。阿基姆把扶危救人看得远远高于合同上规定完成的狩猎指标的价值。在他的价值观念中,人的生存权利是第一位的,远远超过了人的社会价值。因此,他会安葬对自己充满敌意的盖尔采夫,而不会像格罗霍塔洛那样,对自己师傅的呼救声置若罔闻,任凭其在水中死去。
自然是《鱼王》中真与美的典范。惟有真实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才是美的。《图鲁汉斯克百合花》里有一种美丽的百合花,名叫“萨兰卡”。它生长在高山上,“红若朱唇,形似小喇叭,花心深处像覆盖了一层白色的天鹅绒,寒霜雾凇似的花蕊仿佛透出丝丝意想不到的暖意”。这是一件世间罕见的艺术珍品,一经发现就盛开在作者的心里,永不凋谢。叶尼塞河岸边“排排巨浪卷着白色的浪花一刻不停地涌过石滩,撞到礁石上,水花四溅,随即化为阵阵青烟”,河边居住的老人临终前都会让人把自己抬到石滩上,因为这壮丽的景色会给人以生命不朽的信念,帮助他们庄重地离开人间,走向另一个世界。阿斯塔菲耶夫的西伯利亚山河有大刀阔斧的雄伟壮观,也一笔一画地呈现温婉细腻,处处传达着大自然天真未凿的美。作家热爱自然的真与美,不能容忍人类将一己私意强加于自然,用矫揉造作来毁坏它的质朴。在作家看来,光秃秃的科技城、深入丛林的铁路、河上的水电站既是愚蠢,更是罪过。“大自然的一切奇迹都是这样,它那变幻无穷的美只有在它的‘生身之境’才能保存下来。”占有并不代表获得,有时反而意味着失去,就像上钩的细鳞鱼一样,你能远远地看到它的脊背在阳光下闪亮的色彩,可拿到手里后,却再也欣赏不到。
自然,是《鱼王》最重要的描写对象,自然法则是作家判定是非善恶的分水岭,爱自然的人,必然爱自然而然的生命方式,阿斯塔菲耶夫于1985年出版过一本叫做《事事有定时》的集子,题目就是源自《圣经·训道篇》中“事事有定时”一节。《鱼王》的结尾更是全文引用训道者的言语。“造化有时,万物有期”,道法自然的智慧在东西方文化里产生共鸣。天地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是否也因其豁达地不争人类个体利益,以自然万物为先,才让我们百读不厌,欲罢不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