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结与放逐之爱——周洁茹《到香港去》中的女性困境

周洁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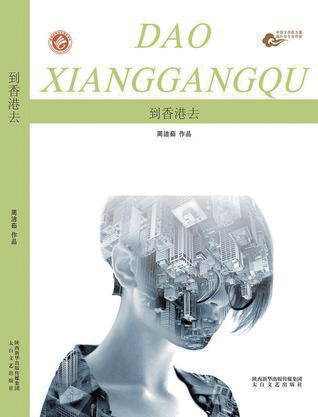
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终结与最后之人》中预言,资本主义将是人类的终极形式,历史将会终结,即便会有事件发生,但不会再有整体性的更迭。平庸的人们将会坦然接受自己的生活,再无革命的勇气与欲望,成为“最后之人”。
这种历史终结意识在周洁茹的小说集《到香港去》中是明显的。小说集中,她不断书写那些遭遇中年危机的、无聊且平庸的香港新移民师奶。“无聊”、“无所事事”、“愚蠢”、“婚变”似乎成为这些女人共有的标签。《到广州去》的静待儿子长大的女人,《邻居》中不是在观察邻居就是在做梦的“我”,乃至《佐敦》中像祥林嫂一样碎碎念孩子择校问题的格蕾丝,都是这类被自己生活困住、在可预见的时间里生活不会发生变动的现代人。这些角色好像走到了时间的死胡同,被看不见的墙壁限制着,在生活安稳的表象下,却有着来到“历史终结”的恐慌与不安。
在《到香港去》中,周洁茹对于这种精神危机有多方面的书写。而在她这里,最重要的被解构的崇高价值自然就是爱情。
作者在《到广州去》一文中设置了一个旅居香港的主人公“她”,去往广州与自己青梅竹马的初恋相见的故事。“她”面对“丈夫”接二连三地添置“小老婆”的现实,在毫无尊重的家庭环境中,只能选择悲观地接受现实,不去想明天,把儿子凑合养大。现实是“香港生活平静,吃饭睡觉,儿子慢慢长大”。“她就是回不去了。就这么空空荡荡。反正也是一转眼,什么都是瞬间。不去想明天,明天就是儿子长大。”时间无限停滞,空洞,并且按部就班。似乎一切时间的价值就在于消耗,一切都在预计中,不会发生更多改变。然而“她”的理想世界却是另一番景象:“十五六岁的女孩,春天的晚上,后门口,桃树下,对门的年轻人,一面,一句话,你也在这里吗。千万人之中遇见的人,千万年之间的一个瞬间。”在“她”的理想的时间长河中,虽则万年,仍然会期待一个未来的终点,在一个特别的时刻会有一个人在等待着她。显然,她无法接受历史终结的事实,而依然在脑中构想自己的崇高价值——理想的爱情,并准备好为此奋不顾身一回。这段引用文字显然是对张爱玲《初恋》的致敬,然而整篇小说却是对于《初恋》的翻转。
周洁茹并不想写作一个陈词滥调的爱情故事。她极其细致不避烦琐地描写“她”去往广州不断遇到的各种琐碎状况。而这一切纷繁的乱象,也是出轨的女主人公矛盾内心的外化。在几经周折之后,“她”终于来到广州,然而迎接“她”的不过是男人出于身体需要的求欢。虽然“她”为他给“她”夹了一筷菜而感动落泪,不过最后还是完全没有犹豫地离开了他。
周洁茹在这篇小说中塑造了一个想要从无尽的时间空洞中解脱出来“真正爱一回”的女人,然而她的英雄主义却被现实消解得粉碎。如果说张爱玲在《初恋》中呈现的是蛮荒现实中微小的温存可能,周洁茹则在《到广州去》中将这种浪漫彻底颠覆,变为一个笨女人的幼稚行为。周洁茹早期小说中也常见对于艳遇或爱情的解构,然而那些女子却是秉性高扬青春逼人,独立的她们可以将这种解构归于对他者(男人、现实)的失望,而自己却依然可以是个独立的新女性。而周洁茹《到香港去》中的女子,却常常是生活的失败者,出轨反而变成麻醉自己、逃离现实的手段。虽然她们带着或多或少甚至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希望,但她们的失望情绪却是指向自己的,是既有生活中找不到出路和未来的无奈。
所以她们出轨。她们出轨并不是全然因为爱,相反有时是因为没有爱。《到广州去》中现实感情干涸的“她”自不必说。 《邻居》里强调自己是出轨不是偷情的格蕾丝;《旺角》中完全不爱自己高智商教授丈夫的“她”。周洁茹在描绘一个“历史终结”时代的同时,并不满足于陈述事实。她亦有志于书写一些不满现状、螂臂挡车的女人们。
《到香港去》中并非所有的女主角都出轨。像《佐敦》里的阿珍和《到尖沙咀去》里的陈苗苗,就是十足的老实女人。拿着单程证的阿珍得照顾瘫痪的坏脾气丈夫,还得找工作供孩子读书。她反复告诉自己:“还能坏到哪里去,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没有什么是会被浪费的。”陈苗苗在婚姻破裂时,始终相信她出轨的丈夫“他自己是不想离婚的……全是我公公婆婆的主意”,“只跟朋友们一起打打篮球,玩玩玩具”。她们的自我麻醉是对抗绝望的良药,是她们不愿接受“现实即使不变坏也不会变得更好”的困境的挣扎。
如果说香港文学常常带上了“离散”的成色,那么,周洁茹笔下的“离散”似乎比这些创作走得更远。《到香港去》书写了许多城市边缘人——香港新移民的故事,以及他们在历史终结、时间停滞中的放逐之爱。同时,周洁茹并无意于将《到香港去》驯服为一城之文学,虽然有着香港的城市背景,但她笔下的故事反映的更是现代人的精神难题与历史困境,带有普遍意义。《到香港去》中那些勇敢而无望的女子,所要突破的是自己的人生桎梏与女性身份的枷锁,更重要的是,这也是她们对于现代性问题与人类历史问题的一种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