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麦克尤恩《儿童法案》:从福楼拜到麦克尤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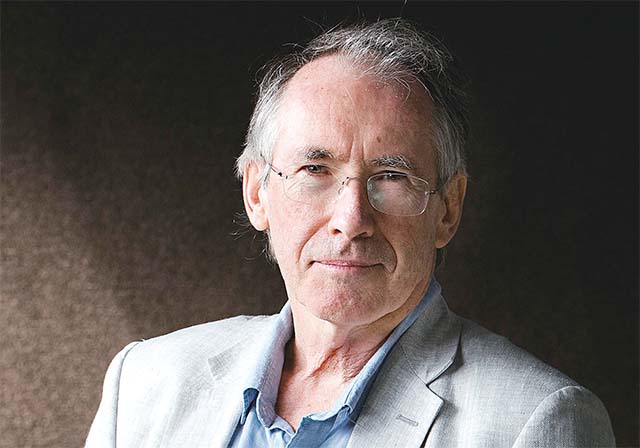
伊恩·麦克尤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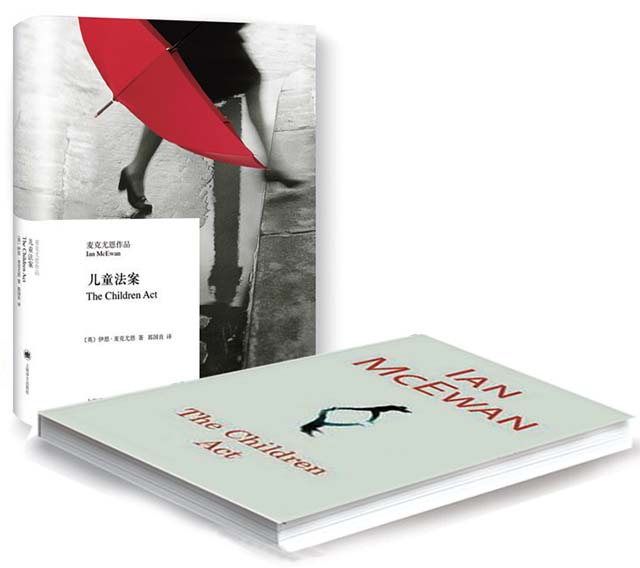
《儿童法案》中英文版
在麦克尤恩的最新小说《儿童法案》里,所有的宗教徒都是陪衬,而他们的分歧在“坚信给无望局面赋予理性”的大法官菲奥娜这里皆成为旧时代的迷狂。这一点很有趣,也尤其引人注意。有人说,作者也许是想颠倒地模仿格雷厄姆·格林,即在理性的视域内审查宗教——可另一方面,文本中的所有声音又都明确地指向了对理性审判的顶礼膜拜,以及对启示律法的嗤之以鼻。读者能够在小说文案上读到这样的介绍语:“一个道德与法律的困境:到底是尊重宗教信仰、个人意志,还是应该坚持生命至上的原则?背负着文明社会的沉重枷锁,人性的天平最终将向哪一边倾斜?”倘若如此看待,便根本没有困境可言,而文明社会也并不背负外在的沉重枷锁。果真有枷锁,那只是文明社会的内在症结:小说无非是将自身展示为理性的又一次大获全胜——尽管理性也不乏做出如下虚伪而无能的表白:“法庭对其特别信仰不予置评,只是指出这些信仰显然被人们真诚恪守着”。简单地说,如此解读《儿童法案》,理性便似乎成了一种新的宗教,舍此文本并无他物。
小说情节上的安排多少有些类似于拉斯·冯·提尔的电影《反基督者》,即在文本里设置另一重文本,让两个文本由并行不悖到交错鸣响。影片的女主角本有心理隐疾,后来在森林的寓所内研读欧洲历史上迫害女巫的卷宗时忽而疯掉。而小说里的大法官菲奥娜同样将自我分割为日夜,在白天她忙于处理事关儿童保护的案件,在夜晚要面对并不和睦的家庭。作者将故事的重心主要放在了白天,宗教徒亚当一家因为信仰的缘故拒绝为命悬一线的亚当输血,而菲奥娜出于世俗的公正想要拯救这个男孩。这一脉的写法老实讲并不复杂,无非是以文本之轨迹映照人心的幽微。并且如上面所说,对理性与信仰对峙这种解读的过分坚持,很容易将小说引向失败。然而,就小说描述来看,作者恰恰是忠实于日常生活的。
它忠实于对以下事实的洞悉:乏味的日子底下藏着许多败絮,或者还有令人心惊的暗流。菲奥娜与杰克30多年的婚姻原本是齐头并进的两条直线,后来都向外部做弧形运动——杰克因为菲奥娜多年不育而谋划出轨,菲奥娜则纠结于同亚当若即若离的关系——接着两人再次归于平行。作者采用反高潮的笔法绝非是一种偶然。较之奸情人命的澎湃写法,反高潮系晚近以来才有的态度,也更适合于揭示晚近以来才有的问题。问题,毋宁说是虚无。人们不只在婚恋里双方拒绝包容彼此的虚无,事实上,当下的生活本相正是每个人都拒绝包容和承认另一个他者的存在权利。不过麦克尤恩叙述的背后,连所谓的儿童福祉也仅仅是读者期待下小说叙事貌似合理的归宿。但这个文本得以成立,只在于它调动起另一种解读,并以此对前一个方案施以倒转:理性并未大获全胜,反倒是沉浸在时代的精神状态里不可自拔。有怨恨:“她几乎无法忍受她出现在她的视线里。现在需要的是一场争吵,一场旷费多时、有数个回合的争吵。在这其中,可能会有与主题无涉的愤恨,他的悔悟中肯定少不了诸多埋怨,可能要过上几个月她才会让他睡到她的床上,而另一个女人在他们中间制造的阴影可能永远不会消散”;有内疚:“脑中的音乐已渐渐消散,此刻另一种古远长久的情绪却不期而至:自责。她自私自利,执拗易怒,表面不露声色实则野心勃勃。她只顾追求自己的雄心,却还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她选择这条职业道路的本意并非在于自我满足。她还断然拒绝将两三个原本会是体贴、极具天赋的个体降临到这世界”。抑或融合了以上情绪:“凄惶与愤怒的糅合。或者说,是渴望和狂怒的交杂。她既希望他回来,但又根本不想再见到他。她还心怀羞愧。可是她犯了什么错呢?一心扑在工作上,疏忽了丈夫,让一桩冗长的案子搞得她心绪不宁?而他有自己的工作,情绪也变化多端。她受尽了屈辱,但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只得假装一切安好。她觉得自己遮遮掩掩,心情沮丧。难道那就是愧疚感?”
故事开始时,菲奥娜与杰克都拒绝对对方做出让步,于是一拍两散。菲奥娜躲入忙碌的工作,在法庭上见到了不计其数的关于孩子的离婚案件,但无论是控方还是被告,菲奥娜从未见到一起主动达成和解的案例。在亚当初步康复后,菲奥娜便拒绝回复所有亚当写来的信件,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最后,当亚当追随着菲奥娜的行程赶来与她见面时,她仍然是拒绝。杰克中途回到家,双方与其说是和解,倒不如说是延续之前的生活。小说真正的高潮出现在最后几页,是由一次拒绝引起的。在第4章结束前,菲奥娜拒绝了亚当寄宿在她家的请求,而在大约40页以后,菲奥娜平静地对丈夫讲起一直被作者排除在文本之外的信息:几周前,亚当在一次疾病复发的抢救中拒绝了输血的方案,并因此去世。可以推测,在被拒绝与主动拒绝之间,亚当并未耗费多少时间去思忖何去何从(一种决定的思忖总是瞬间到可以忽略不计)。也正是这最后一次拒绝使得此一虚构文本得以成立,并且逆向式地贯穿和决定了整个文本的基调:无穷无尽的拒绝。
自然,宽恕的无能正暗示着怨恨的根深蒂固。小说中法庭的裁决可能只是象征的一瞥,它与理性或启示均没有关联,不过是意味着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审判。这正是时代遍地怨恨的缩影。与此同时,麦克尤恩在涉笔把握这些问题时,并未逾越福楼拜设置的界限:菲奥娜评判是非对错,但作者并不评判。虚无主义从来都不是没有道德,恰恰相反,道德狂热分子从来都是时代虚无主义的症候。那么,小说是否存在“道德”呢?至少我们可以说福楼拜之后的小说不再有“道德问题”:作者不再背负道德的代言人这一职责。以此来看,《儿童法案》那仅有的一次高潮甚至不成为高潮,而不过是对理性训谕与人道主义的嘲讽。
如果说现代文学始于将传奇性与日常性并置的福楼拜,那么福克纳与卡佛自然都可以说是福楼拜的子嗣,虽然他们仅仅是继承了传奇性与日常性的其中一端。拒绝是所有文学的母题之一,但麦克尤恩便不会像福克纳那样不厌其烦地用上几页笔墨来渲染被拒之后的情形(如《押沙龙,押沙龙!》里少年萨德本被拒绝从正门进入之后的心理描写),而只是对冲突过后的残局予以描述:亚当死了。在这里,他秉持的是卡佛或耶茨的衣钵。
冯内古特曾称赞理查德·耶茨的《复活节游行》云:“福楼拜以来,少有人对那些生活得苦不堪言的女性抱以如此的同情”。联结耶茨与福楼拜的,写法上的传承倒还在其次,归根结底是不予同情。不予不等于有或没有,乃是不动声色。本文开篇尝试的那一类解读,就预设了光明与黑暗的争斗,并且光明与善将战胜黑暗与恶。在小说里,是理性之光驱除了启示的阴影,菲奥娜拯救了命悬一线的亚当。果真如此吗?不要忘了亚当最终是死了的,理性并没有再一次如期而至。采用反高潮的写法既合乎文学史的发展逻辑,也适宜于时代本身的逻辑(文学史总是在微妙地回应时代)。麦克尤恩写作的时代已非福克纳写作的时代,进而言之,那种重振与重整时代秩序的雄心壮志早已丧失殆尽。如此写出的小说——如果作家是忠实或真诚的,如果这忠实与真诚又一概指涉了他对时代本身的洞悉——那么这样的作品便再无可能为读者提供廉价的鼓舞与安慰。
这样说绝非诋毁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复归现实主义的那批作家,总的来说要更看重巴尔扎克式奇迹轶闻的地域性和传奇性,尽管它又将此上升到寓言的高度,并以此观照平庸的世间;而对复归现实主义、秉持福楼拜日常性一面的作家而言,则可能压根儿就感受不到创造传奇寓言的必要,因为日常生活正是全部。《复活节游行》的译者孙仲旭曾说,这本书还是有些过于冷酷了。对当代的写作来说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作者也不必再次期待一个文学上的道德乌托邦能够降临人间。诚如卡佛所说:“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它们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达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儿童法案》又有了一些新特色。麦克尤恩的冷未必更彻底,却是要更含蓄以及更隐晦,甚至阅读时的精力都像是在应付叙述的沉闷,但合上书后又猛然觉察到一些陌生的情绪正在生长,让你为此背脊发凉。
福楼拜曾将艺术的最高境界规定为“既非令人发笑或哭泣,也非让人动情或发怒,而是像大自然那样行事,即引起思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麦克尤恩的《儿童法案》多少是朝着那个方向前进的。如果它伤害了我们,那也不是文学的过错。坦白讲,这恰恰是文学的责任:文学只是以此让我们在震惊之余思索这个时代——如果可能的话,克服这个时代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