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卉《沈绣》:史笔耿丹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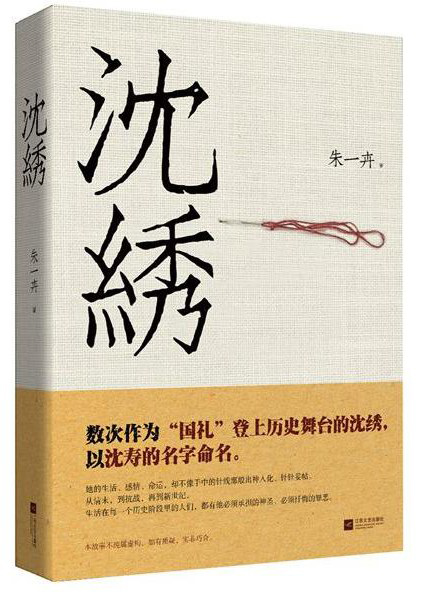
朱一卉从事小说创作已经有不少年头了。他的写作路子很宽,在我的印象中,他似乎没有驾驭不了的题材,这或许与他的新闻记者的主业有关。对于小说写作来说,生活的积累是最重要的。过去有段时间曾经流行过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的说法,这实际上是矫枉过正的话。稍有点小说阅读经验的人都知道,好作品留给人的还是它所提供的经验世界,时代、社会、生活、场景、人物、故事与情感,甚至某种气息。有些场景与人物让人终生难忘。这里面的道理说白了就是小说要写得结实,有干货。干货是什么?就是经验。而经验不能全靠想象和虚构,最终还是有赖于生活,有赖于对生活的提炼。这就是朱一卉这样的作家厉害的地方。
《沈绣》显然是朱一卉写作上的又一次拓展,这一次他要向自己挑战了,他将笔触伸向了历史的深处。我不止一次听朱一卉谈起过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从人物到故事,从构思到语言,甚至一些具体的细节,可见他对这部作品的重视,也能想象到在他的心里,作品盘桓已经有些时日了。我自然非常期待。因为一个作家写作的疆域到底有多大,只有从他纸上的不断跑马圈地中才能看得出来。朱一卉正值年富力强的创作旺盛期和成熟期,有那么多的积累和思考,此时不放开手写一写还待何时?我之所以这么期待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题材太值得写。我说的是张謇。在现代中国,我还想不出有哪一个人能说他与张謇是无关的,相反,我们每个人几乎都与这个近代传奇人物有着联系,或者直接,或者间接,哪怕从未听说过他。因为张謇的事业首先是开创性的,这个从传统走出来的晚清状元做的都是四书五经里没有的事情,都是开天辟地“第一”的事业。更因为张謇的事业几乎无所不包,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艺术、社会保障等广泛的现代社会领域,给传统中国的现代社会生活转型创立规矩,模范成型,其影响之大已经到了让我们身处其中而习焉不察的地步,我经常说,与其说张謇开创的是事业,不如说他创造的是生活。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名号不可以冠在他的头上了,因为他从事的事业太多太多。当一个人所从事的事业无所不包时,任何一个领域或行业的称谓都会显出局限。这是一个虽然从每桩实事做起却心存高远的人,孙中山对张謇说他自己做的都是“空”的,而张謇做的是实事,这里有对张謇的褒奖,也有对自己生命的感喟。但他是否知道张謇的心事呢?我以为张謇也是有着与孙中山一样的“空”的心事的,只不过各人走的路不一样罢了。张謇没有走革命的路,他走的是实业建国的路,走的是全面的社会建设的路。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不要说是文学书写,即使是历史叙事我们都做得很不够。现在,朱一卉想到了这位同乡的伟人,以文学来与他对话,走近他,走进他,实在是让人欣慰的事。
当然,朱一卉这次写的并不是张謇的人物传记,甚至都很难说张謇是小说的主人公。这大概就是历史小说与单纯的历史的差别,也是作家与史学家在处理同一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在视角上的差异。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可以小说化,更不是历史人物的所有行止都可以成为小说的内容。面对历史与历史人物,小说家要发现,要选择,更要重新叙述和重新解读。朱一卉抓住了张謇与沈寿的故事和传说,抓住了沈绣这一传统工艺在传承过程中的诸多传奇。这是朱一卉的眼光所在,由此,他个性化地完成了历史向小说的转换性书写。有限的历史被拓宽了,实在的史实变得灵动了。朱一卉在历史留下的空白处展开了想象,在历史的断裂处施展了小说的缝合术,在宏大历史的罅隙处注入了情思……可以看出朱一卉为这部作品的丰富性做出了相当的努力,他打通了历史与当代的阻隔,成功地使叙述穿行于时间的隧道中。他吸取了类型小说的许多元素,增加了叙述中的曲折与悬疑,从而增强了故事的戏剧性。他在史料与知识上也做足了功课,并且力求将其文学化,比如对《雪宧绣谱》的穿插引用,一方面再现出张謇与沈寿的具有舞台效果的对话场景,另一方面又传达出了沈绣的艺术精粹,使作品显出了博雅风姿。
由此,我想强调一下这部小说的文化意义。我以为,作为一个南通人,朱一卉对南通的书写不仅是他的文化选择,也是一个地方性文人文化自觉的体现。张謇的事业与影响既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南通的,而沈绣作为地方工艺无疑是南通文化的瑰宝。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说,都值得大写特写。所以,我认为应该从地域文化上评价《沈绣》的文化价值。如今的情形是,社会的开放程度正在加大,信息流通日益频繁,任何一个地方都与国家、与世界相通,经验也在不断被复制,而在文化层面,个性与区别性的地位也在降低,这跟古典时期恰成对比。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看重如《沈绣》这种地方文化写作的存在。它说明,第一,地方依然存在,经验的差异依然存在;第二,地方写作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生产的重要渠道,它构成了与“通用写作”具有区别性特征的写作类型与写作风格;第三,就中国目前的地域文化与民间经验而言,地方写作显示出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沈绣》的地方性写作是坚实的,是本土的,它不是他者的田野调查,不是奇异景观的炫耀,而是由当地作家书写的历史记忆和创造的当代审美经验。所以,它在地方文化书写的保真度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地方文化精神的提升上具有本土的强大基础。这样,我们就能在更高的层面认识到这部作品对南通自然与人文描写的意义,意识到南通文人传统与工艺传承梳理的价值,意识到作品浓郁的南通风情与语言的意味。这样说不是把朱一卉的作品说低了,恰恰说明这一写作的不可替代。
(《沈绣》,朱一卉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