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琼《玫瑰庄园》:玫瑰庄园里的“拾荒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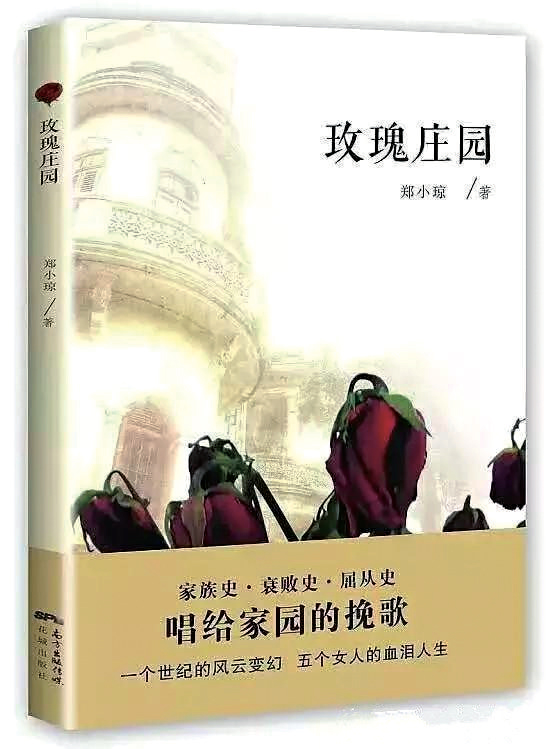
作为郑小琼近15载打磨而成的最新诗集,《玫瑰庄园》使用了一个不无暧昧的标题。字面上漫溢出的西式浪漫,难免让人想象骑士与公主的罗曼史,但实际却刚好相反,祖父与五位与之成婚的祖母,在拆解浪漫叙事的同时,呈现出一片东方式样的古典荒园:“落花遍布小径,后厢房凉气逼人/秋玫瑰开放祖母的脸庞,针线里/云集她的迷惘,她用哀叹的针/绝望的线绣出玫瑰花园的秋景。”(《针线》)整部诗集中的“玫瑰”指涉着肃杀之秋而非生情之春,而祖母用绝望之线绣缝荒园,俨然女诗人撰写整部诗稿的隐喻。诗人绣缝的不仅仅是祖辈的家族史,20世纪初华夏动荡的东方民族史,也在这座“玫瑰荒园”中获得了寓言式的面孔。
自2005年起,郑小琼花了不少精力阅读先秦文与南北朝辞赋,在诗集形式与内容上呈现鲜明的复古倾向。每首诗由“四行六节”切割出颇为整饬的面貌,蕴含着诗人对诗歌格律传统的自觉追逐,而在统一的形制之下,则填充有丰富的古典措辞与意象,并注入带有“黑色美学”“颓废美学”意趣的“诗心”,宛若罩上一层六朝气韵与晚唐风致。“香炉、经卷,神龛上祥云”(《云》),乃至征人思妇、妆台迟暮、斜阳昏鸦、残菊泡酒、蜀绣青瓦……琳琅繁华的古典素材堆叠出带有东方美学兴味的“语言珍玩”。诗人精巧地为每一首诗镶嵌意象用作标题,整部诗集如次第展开一扇扇屏风,玫瑰也不过是屏风上古旧的雕花,屏风之下则涌动着祖辈置身其中的古老中国的生活、伦理与情感。现代诗人于古典荒园中,拾掇起残存的文质,并将语言雕花,实现了自我的东方化。
在时空观念上,诗人将“庄园”等价为“荒园”的创作意图颇为明晰,譬如《梅》中:
“阴沉的天空,显影于碎石小径/错别的寂静在枝头,像冬日清澈的疼痛/从雪到冰,它都有骨头般的晶莹/风摸到冰冷的梅花与庄园//梅花是冬日庄园唯一跳动的心脏/它还保持着人间尚余的温暖,开放的瞬间/它红色的光芒像春天的序曲,像暗示的比喻/传来黑暗中庄园的宿命”
这一段似乎内在勾连着鲁迅小说《在酒楼上》对“废园”的描摹。不过,与鲁迅笔下的斗雪繁花在废园中释放出的亮色与生命力不同,郑小琼的红梅则暗示着庄园黑暗的终极性宿命。这种“废墟美学”携带着沦亡与消逝的种种隐喻,犹如园中罹难或井中溺毙的家族魂灵,在一次次回返中加速着“荒园”的鬼气森森:
“井水淋湿月亮、星光,如今它/荒芜,淤积,青藤缠绕旧辘轳/青石板幽凉,荒草留下时间皱纹/青衣姐姐夜半歌声,淹溺的伯父//桐树还生长,开花,往事似井边/桐花,一串串悬挂哀怨与悲伤/雨落井中,远处,水滴的声音,落入/井中,伯父亡灵,沿潮湿井壁升起”(《井边》)
2007年,郑小琼在诗集《两个村庄》中收录了早期写就的几首《玫瑰庄园》组诗,业已显现出另一种村庄空间的书写策略:与雷蒙·威廉斯将村庄的形象及其张力置于城市的对照面加以观察的思路不同,《玫瑰庄园》并未刻意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村庄的摧毁与改造(当然,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反思,在《纯种植物》等诗集中仍有体现),整部诗集的“村庄”只是一个虚化的背景,或者说,只是一座具象化的“荒园”。它充当着家族史乃至古老中国衰变的象征,如《雀鸟》引用的《牡丹亭》“都付予断井颓垣”,隐微地指向了恒常性的东方时空观,现代化的进步史观让位于自然轮回的宿命,这种宿命在诗人体内再次降临。
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一文中,借助诗歌《拾荒者的酒》发明了一个喻指波希米亚人的“拾荒者”形象。对于郑小琼而言,其无法绕过的“打工诗人”身份,似乎难以在《玫瑰庄园》这样一部回归东方古典传统的精微之作中得到安置。然而,本雅明的“拾荒者”形象,恰恰为诗人提供了妥帖的身份和解释:一度朝不保夕的底层工人生活,使得郑小琼毋庸置疑地遭遇了最朴素的“拾荒者”体验。写作《女工记》时,她合理地延伸为诗人层面上的“拾荒者”,背后连通的则是角色自身的反抗性与道义心;从《女工记》到《玫瑰庄园》,不过是“拾荒者”角色的扩展而非断裂,诗人在家族与民族、历史与文明的高度上,建构了一座东方荒园,并以“拾荒者”的第一叙述者身份守护其间,“用心擦拭着旧宅的边界”(《星辰》)。“拾荒者”不仅为诗人写作提供了原发性的立场和动力,连贯着工人、女性、诗人等各种身份的转换,还直接将“火药桶和啤酒桶的气味”带到了玫瑰庄园中,催生出了整部诗集的另一个重要思想维度——带枪的玫瑰:
“潮湿地图溢出祖国的残缺,他在园中/读时间的宗教与忧郁,战火在远方/燃烧,似枝头的残花,漆黑、溃烂/人间掺满倭寇铁蹄带来的沧桑……去西北或西南,重庆或延安/故国的枪口长出鲜红的玫瑰/他不适应庄园生活的守旧与压抑/花开得如此苍白,空气中有霉味”(《奔》)
“‘别为我担心’你信中第一句话/我想象亚热带的丛林,野兽与疾病/孤寂与饥饿、生与死、枪与玫瑰/思乡病,黑汁般的光与戴安澜将军”(《异乡》)
“在后园的银杏叶片,战火/切割国家的天空,废墟中长出殉难者”(《戏》)
诗人拾掇起民族战争史中的家国记忆。那些难以言说的历史残片,成为拾荒的重要对象。正如张清华所言,郑小琼所显示出的初步的成熟,正在于“从在场的劳动者主体到人文性思想主体的转换”。然而,在宏大的历史和民族话语面前,诗人仍清醒地坚守着个体言说者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在个与群等多重视阈的交错中呈现出复杂的张力,并尝试给出女性抑或东方式的判断,正如《诉》结尾处对“文革”见证者“她”的定格:
“将她钉在某个不幸的点她眼里的辛酸/已经被时间磨平显然她无法理解那些庞大的词/她有着的却是中国传统的良善或者屈服命运/上天注定的选择她用此来安慰内心的怨诉”
(《玫瑰庄园》,郑小琼著,花城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