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品荐
特约撰稿:李林荣
《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加】施吉瑞著,王立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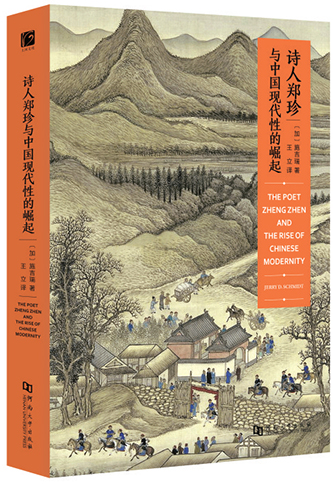
“中国的诗人和散文家正是思想史的建构者,研究他们的作品往往可以窥知他们的思想。倘若忽视宋诗派和桐城派,19世纪中国思想史则永难完善。”年逾古稀的德裔加拿大学者施吉瑞在他这部新译成中文版的著作里,恳切而又犀利地作出这样的论断。宋诗派、桐城派当然也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但对于它们的肯定,摆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以降近百年来的现代文学和文化的价值观念背景中,显然是一种极具挑战意味的说法。
自青年时期就钟情于中文,并且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本科期间、在台湾游学期间、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和博士期间,随陈世骧、于大成、李祁、叶嘉莹等学习研究中国古典诗歌,之后又以此为业,长期坚守汉学教席,投身从唐宋直至晚清的诗歌、诗人和诗学研究,出版了解读杨万里、范成大、黄遵宪、袁枚思想生平和创作道路的专著。这样的求学和治学履历,少有地执著,也少有地瓷实。它足以佐证:施吉瑞这部英文初版于2013年的近著《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学术品质是多么严正、文化态度是多么深情。
在55万字的厚重篇幅内,清末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年间蜗居故乡贵州一带的平民诗人和学者郑珍的人生画卷和精神世界,得到了全面细致的展现、阐释和评价。受科考屡败、家境寒素、地处偏僻等条件所限,平生大多数时候都只是一介布衣的郑珍,虽置身文化衰退和价值崩解的大时代前夜,却连位卑而忧国、匹夫而担天下责的最起码的话语资格都无从获取。甚至他晚年遭逢乡间严重兵乱,被迫数次离家避难,稍得安顿时,为提醒官府妥为善后、革新政务,而做了一生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上书谏言,得到回应却是一通耻笑和被斥为“疯狂”。零散西南各地短时间充任学官的经历,成了郑珍灰暗生命历程中作为一个文人和学者的少数几点事业上的亮色。
但尽管如此,按照施吉瑞从返回史实和直面史料的角度重新把握历史本相的认识方法,走出一再用新材料去重复验证成见和旧说的误区,我们就会看清而且也同意:郑珍经由其诗文创作所体现的思想,确实包含和体现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比如,对于汉学的理性主义思维的汲取,对于新的个人价值的标举和对于群体传统的质疑,对于汉学和宋学调和融合的不懈努力,对于种族偏见、女性歧视的摒弃和反其道而行的富有包容度的国家认同和人性关怀,对于终极意义上的乐观主义取向的艺术表现和人生追求,对于医学、科技和各类实学的热爱和践行,对于现状的批判和社会政治变革的期许,以及最后一点也是贯穿其为学为人后半行程的最重要的一方面实践——对于他自己所信奉和坚持探索的思想理念不遗余力、竭尽所能的向后辈和向外界的传承与传播。
这些今天可以概之以“现代性”的独特认知和精神特质,在历史现场固然没能使郑珍从他所处的时代性的负疚、焦虑、疏离、迷茫等负面的群体文化情结中彻底挣脱出来,但征诸可靠史载,郑珍的思想通过他为数不多但确有历史影响的亲密朋友和弟子,实实在在地流传和汇合到了近代中国思想和社会艰难转型的大潮流中。而对于这一思想流脉源发之处的种种生动细节,这本着力替一位当代视野中的“小人物”正名加冕的大部头书,毫不吝惜地把一多半的篇幅,都用做了解析和阐发他以诗为主的创作。诗言志,志不应仅止于缘一己私情,更可以包举世情和人性、天下和时代、见识和学理。在古今演变的文化分水岭上,诗是包袱,也是依靠。这样的新旧文体辩证法,在被重新发现的郑珍及其同时代人这里,又一次得到了有力的印证。
《小说修辞学》,【美】韦恩·布斯著,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7月出版

从中国的小说创作和理论批评都以波浪相逐的潮流化状态向前发展的1980年代走过来的人,对《小说修辞学》大多不陌生。它最初的两个译者和出版社都是不一样的中译本,分别于1987年初春和深秋在广西和北京面世,距今整整30年了。书中剖析和阐发的有关小说创作和接受的各个环节的基本机理,不少已成中国文坛上众所周知的常识,以至于很多人都常以为这些认识是我们本来就有的。
但实际上,正如译者之一周宪在此次重新印装出版的修订版中译本序言中所说,这本书被中国文学界广为接受的30年,同时也是它被片面化地误读和选择性地肢解的30年。作者韦恩·布斯身为美国文学批评界“新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第二代中坚,无论是在他这部学术代表作首次出版的1960年代初,还是1983年该书发行第二版之际,面对前者所处的“新批评”正盛之势,或后者所处的欧陆解构主义和叙事学风行的语境,其一贯的价值依归和方法立场都恪守在重归古典修辞学伦理根基,沟通形式美学、文化政治和社会道德实践的大前提下。
全书3编13章,每一编的每一章都层层深入地贯彻了上述思路。而且恰好与我们在30多年前和今天以不同的形式所需要解决的重建和深化文学与时代及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课题相类似,《小说修辞学》的各编各章里每一处的论述和分析,都不是平地起高楼式的玄想或空论,也不是刻意标新立异、从荒野或飞地上施工,而是从对于小说和现实关系的一整套陈腐、板结的僵化认识和思维定势切入,条分缕析地破解、拆除它们,在清理它们的消极影响、透视它们的漏洞和偏失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全新的更加稳固、更富实际效能的有机的小说修辞学和文学伦理学。
只有了解到这一层次,这本在跨语际、跨国界和跨时代的理论旅行中早已化成“我们的经典”的《小说修辞学》,才能真正发挥出它本来就有的一份针对欧美文论的流行风气展开批判和谋求突破的可贵力量。就这个意义来看,如今它的修订版中译本崭新上市,正可谓恰逢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