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雨魂魄的阴阳两界——童伟格小说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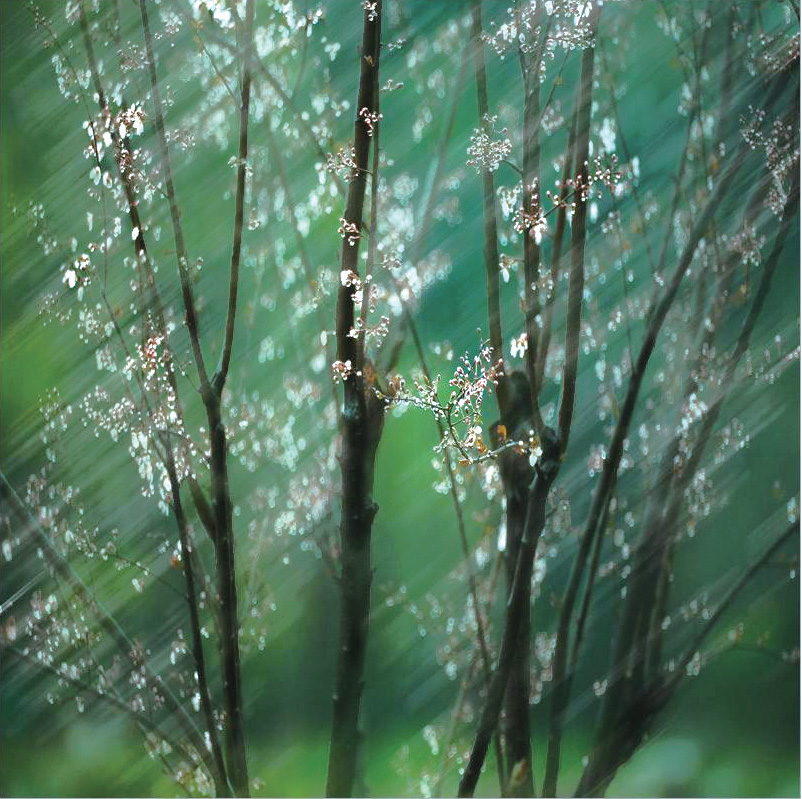
在阅读童伟格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无伤时代》和《西北雨》时,细心的读者也许会被这样一处有趣的细节所迷惑:在《无伤时代》里,主人公“江”孑然独居于“大城”(台北?)一间斗室中。因为在这间由房东家厨房改造而成的斗室里每晚都失眠,江总会在天未亮时出门,走进一所大学并坐在人工湖边呆看黑夜,等待黎明。此时,诡异的景象出现了:
江总会看见林子里、小径上、临湖的骑楼底下,任一处有光无光的所在,到处都挤满了老去程度不一的人们。
老人家们做着种种奇特的举动——有人拼命用背撞一棵树;有人坐在栏杆上猛击自己的膝盖;有人半蹲着像要蜕皮的蛇一样双掌狂磨自己的脸;有人扳胳膊;有人缩肚皮;有人腿架在铁椅上;有人赤脚来来回回在一条铺满碎石的小路上奔跑。江低头离开,暗自发誓一定要分明记清这没有人喊痛的地方。但江每次都失败。一走回斗室,他就倒地不醒,什么都不再记得了。
如果说,初读《无伤时代》的读者会因这个宛如一部悄无声息放映着的鬼片式的场景而肾上腺素分泌激增,那么,当一模一样的鬼魅景象几年之后再次出现于《西北雨》中,给人的感觉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惊悚感,而是透出浓郁的怪诞氛围。再往前回溯,我们还会惊讶地发现:即使是两部情节截然不同的小说,即使一个是由房东家厨房改造而成的斗室、一个是搭建于顶楼的铁皮小屋,两位主人公生活的环境却是一模一样,都是一字排开水槽、料理台和杵放瓦斯桶的坑洞,都是在坑洞中横行着斑蚊、蜘蛛以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昆虫。尽管早已有评论者指出童伟格是一个热衷于不断重新讲述既有母题的作家,但这种有意识的文本复制和粘贴,其意义似乎已经超越了“重述”的层面。他以一种最形而下的形式操作,追索着最为形而上的理念。
从这个一再出现的诡异场景中,我们其实可以概括出童伟格小说的几个既定主题:“鬼魂”“死亡”与“无伤”。在“黎明”这个“有光无光”、晨昏分割、阴阳相交的时刻,一群面目不清的老人做着一系列诡异的、常人做不出甚至都想不到的动作,这不免让人联想到“百鬼夜行”的魍魉世界。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没有人喊痛”——因为有“伤”,所以会“痛”;倘若“无伤”,“痛”也就不会存在了。然而,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有“无伤”的地方存在?如果有,那大概也只能是在超出我们实存体验的另一维空间之中。
在《无伤时代》中,除了黎明前那个鬼气森森的人工湖畔,童伟格还提到了另外一个“无痛无伤之地”,它具象地呈现为三色盲猫的骨灰坛,而抽象地指涉着生命消亡后的乐土。“在那样的地方生活,带点残缺,是自然的、是可以被原谅的。她可以视力不佳,那无伤。”而对于江这个从小到大伤痕累累的“废人”来说,这种痛彻心扉的感悟尤为刻骨铭心。自童年起,死亡事件便伴随着江,从祖父葬礼的风光,到父亲事故惨死的悲伤,再到祖母“以一丝气息,等待夕阳的召唤”的从容与澹然,当然其间还穿插着盲猫及“黑嘴”魔幻的死而复生、生而复死。凡此种种,都在他心里投下巨大的阴影。在《西北雨》中,童伟格在安排父亲给儿子讲完那个荒诞又不无凄凉意味的“战俘/开锁高手与狗笼”的故事之后,突然宕开一笔,煞有介事地用近千字的篇幅,转述“冷硬的教育学”原理,那是关于儿童心智发展在10岁左右由“具体运思期”向抽象的“形式运思期”转变的心理机制:“教育学说,倘若这小孩能牢牢记住一件自己并不理解的事,就像死背一则数学公式,那么在将来,他有可能突然明白这些事所代表的意义。这是说:肉身为度,一个人在内里包藏、护卫某种记忆,抵挡住时间摧枯拉朽的破坏力,终于和记忆一起,等到思维的转型期。在那之后,抽象回去寻获具体,事物向那些犹记得它的人,展示它自己。”江恰恰是在这一“心理转型期”连续遭遇了“死亡”这一对于儿童来说深奥难解的抽象事件,并一再加以强化;只是那个“突然明白”的瞬间迟迟不能到来,持续的创伤体验又对其心智的成长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干预和影响,以至于将其心灵塑造成“早发失智者”的状态。时空观念的倒错、纷乱芜杂的人称,以及阴阳两界的交融,共同建构了江怪诞的生存体验。他甚至将自己视为“一株蕨类植物”,“只会用浅浅的根,贴住坚硬的地表,把最新生的芽,牢牢藏在最内里的地方,然后自己推挤自己,纠结蜷曲成一团苍老的大圆球”。这种蜷曲的体态,同样也是江的心理样态和性格基础,其本质是胆怯、敏感、纠结、内敛的。处于思春期的江对收银员大姐萌生了朦胧的爱恋,却苦于示爱无门,因为他深知“谁会想跟一株蕨类植物,一同坐在黑暗的电影院里看电影”;只能异想天开地以“攒铜板”的方式,去换取同大姐搭讪的机会,但这个计划最终却轻易地被“白铁铸的圆缸,圆缸上附着一个白铁铸的圆钵”这样的简单装置所击溃,无非是在江创痕累累的心灵上再添一道伤疤。
试图逃离岛屿北端潮湿多雨的山村,同自己的背景与过往决绝地一刀两断,去“大城”和“北方大港”追逐与祖先、父执不同的生存体验,似乎是童伟格小说中人物普遍有过的雄心壮志。“我想,住在这样的地方,大概免不了是要离开的。”“我抬头对母亲说:‘没关系,我喜欢住在这里。’母亲对我笑,她拍拍我的背,她说:‘只怕你长大了以后,就不会这样想。’”而最具代表性的,还要数《无伤时代》中的舅舅、《躲》里的大伯,还有《驩虞》里那个“本事偌大地干遍各种职业——厨子、武士、道士、泥水匠、算命仙、教戏先生”的“他老爹”。但无一例外地,当他们在外面或风光或狼狈地挣扎了一辈子或半辈子,终究免不了返乡的命运,只不过,返回的或是疲惫的肉身,或是疯癫的灵魂。“大城”固然是好的,甚至连棉被都不需要,因为那里不会有故乡山村式的冷雨。但就像那首人人耳熟能详的歌曲里唱的那样,“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在钢筋水泥城市里四处碰壁的孤魂野鬼,最终还是咽下“今天又荒废了一天,明天应该好好努力”的苦水,踏上返乡之路。多雨的海边山村在空间上近乎封闭,只能靠一条马路和总是脱班的公车与外界交流;而乘着这公车、沿着这马路出走的山村儿郎们,只能是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画出一个半径更大的圈,就像表盘上的指针旋转一圈后又回到原点。
与空间相联系的,自然是时间。这显然不是一群在海上漂泊10年的奥德修斯,而只是一群不得不回头的浪子。他们曾经坚信“只有两件事人类可以自由操纵——第一,是‘时间’;第二,就是‘梦想’”,而他们所谓的“梦想”却不过是“用财富在土地上盖间有私人厕所的房子,把我的女人关在里头”。他们妄想将时间玩弄操纵于股掌之上,最终却被时间狠狠羞辱。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些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时间似乎是停滞的。例如《王考》中的祖父,任凭村人追逐时代潮流,卡拉OK也罢,有线电视也罢,于他都似乎是空气一般,丝毫无法动摇他于古籍中考据本乡本土历史隐秘的执念。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用毕生精力考据出的结果,居然是“本地越三四百年会有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一切会从头来过,人类重活,史书重写”。他对此深信不疑,也正因此,“祖父的逻辑像个圆,行动像个圆,信仰也像个完整的圆”。无独有偶,《驩虞》中的老者,面对视12年一度的大醮为娱乐的人群,提笔写下无人认得、因此也无人能解的“驩虞”二字。其实,这不过是“欢娱”的异写而已。《孟子·尽心上》有“霸者之民驩虞如也”一句,朱熹《集注》曰“驩虞,与欢娱同。”然而,又有谁能知道,这种看似迂腐的掉书袋行为,却与最高端前沿的宇宙理论暗中契合?“这满天星星,它们有的,在千百年前就已死了,爆炸了,熄掉了,完了,你现在看到的,是还在苍茫的宇宙中继续奔走出亡的余光。”今天看到的星光,是千百年前发出的,而在《无伤时代》里三岔口钟楼上像脉搏一样隐隐跳动的分针,永远指向两点四十五分,时间却仍旧无可羁绊地向前流逝。究竟怎样才是真实的时间?世界的复杂让这个问题无解。也许,对于山村里那些可以任意跨越阴阳两界的微雨魂魄,例如《活》里的树根、《叫魂》里的吴伟奇和“阴间观光团”来说,这个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在时空中自由跳跃,任意往来,终于抵达了“无伤”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