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记的鼎新之作——读薛瑞生著《晓风残月——柳永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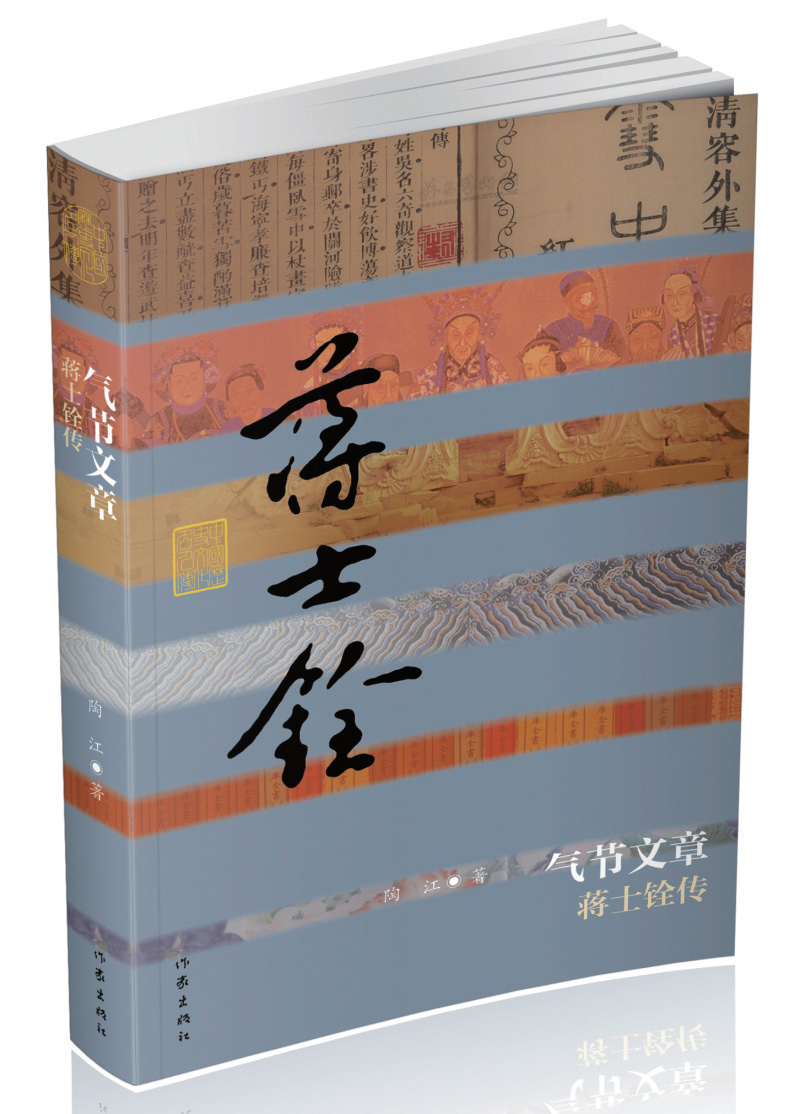
提到北宋词人柳永,相信大多数读者不会陌生,大概随口都能吟出他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或者“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之类的名篇佳句。对于柳永其人,除了稗史小说中几个风花雪月的传说故事,读者是否能说得清道得明呢?对于柳永的多数词作,读者是否能了解创作背景及其本事呢?不能知其人、论其世,而要读懂其词,可乎?看来,一本具有当代意识,能满足当代大众阅读趣味,又兼具学术性和史料性的柳永传记,不仅有必要,而且是读书界所期待的。
作家出版社最近推出柳永研究专家、西北大学薛瑞生的《晓风残月——柳永传》(作家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一书,便是在这一期待视野中出现的新著。
本书的“鼎新”首先体现在撰著体例上。柳永是北宋词坛名人,为宋词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其生平行实方面的资料却非常有限,诸如生卒年月、科举次数、及第时间、婚娶子嗣、仕宦历程等很多问题,都众说纷纭,争议颇多。为这样一位人物写传记,难度很大。试想一下,如果但凡遇到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作者都站出来发表见解,那么此书岂不成了柳永研究的学术专著?虽然这样做也是薛瑞生的强项,却与本书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之一种的人物文学传记的体例相悖。
读完全书,感到薛瑞生在撰著构思的处理上很智慧。为了解决史料性与可读性之间的矛盾,作者虚构“异史氏”和“词痴子”两位人物,通过他们和作者“(简)雪庵(薛瑞生笔名)”的一问一答,或者交代相关问题的学术研究动态,进行辩驳;或者叙述相关内容的背景因素,如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宋代的官制等,将其穿插在文学描写中,从而巧妙地解决了本书科学史料性和文学赏读性可能互相轩轾的问题。
比如,众所周知,宋代官僚机构庞大,冗官冗员问题严重,官制颇为复杂,又有元丰改制,更加剧了其复杂性。薛瑞生在研究宋代文学时,一向强调对官制的了解和重视,认为许多研究错谬都和研究者不了解宋代官制有关。具体到柳永,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对宋代官制的必要介绍,关系到对柳永仕宦历程的梳理厘清,应当是柳永传记的必然内容。本书中对此背景知识的交代,主要就是通过异史氏和词痴子与雪庵的问答对话实现的。诸如宋代官员携家眷赴任的问题、宋代官员磨勘转官制度以及官大差小、官小差大等问题的叙述,都是如此。
显然,异史氏和词痴子与雪庵主客问答形式的构思手法,是对汉大赋中“子虚”“乌有”和《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聊斋志异》中“异史氏曰”的书写传统的继承借鉴,但将其运用到文学传记中,却不能不说是薛瑞生的智慧和创新。巧妙的撰著体例和构思,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新鲜感受,也为此类历史人物的传记书写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书写范式。这一点,应是薛瑞生此书的大贡献所在。
其次,本书虽然是历史人物的文学传记,但是学术性非常强。说它呈现了柳永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名副其实的。薛瑞生是国内知名的柳永研究专家,早在1994年,中华书局就推出了他精心撰著的《乐章集校注》,此著后来多次重印、再版,是一部关于柳永词的可靠校注本。2008年,他又在三秦出版社推出了《柳永别传——柳永事迹新证》这本具有很强学术性的柳永传记。因此,《中华历史文化名人传》组委会约请薛瑞生担纲柳永传记的撰著工作,实在是慧眼识人。他在《晓风残月——柳永传》中,将学界有关柳永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自己研究柳永的最新所得也融入其间,从而使得这本传记具有很强的学术性。比如,关于“柳七郎风味”,众人皆知其出自苏轼的《与鲜于子骏三首》其二中。然而后人或对其词学批评价值重视不够,或以为这是苏轼对柳永词的贬抑。薛瑞生认为苏轼所谓的“柳七郎风味”,“正好代表了宋人对柳词的最高评价”(第48页)。接下来的行文中,本书结合具体作品,从大量创制慢词(第53页)、叙事性(第56页)、词的典雅文章(第74页)诸方面具体阐释了“柳七郎风味”。这样就以文学传记的形式,完成了对一个严肃的学术命题的探究。再如本书提出的“柳尾”一说,认为部分柳词的结尾往往“词语尘下”,是累及全篇的败笔(第85页)。另有一种“柳尾”则出现在赠人词里,“即在赠人词的结尾,总是说这人不久就可以大用、高升”(第188页)。“柳尾”之说,似乎为前人所未道,是薛瑞生首次概括出的柳词的特征,是具有学术前沿意识的创新命题。这方面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此不赘言。
再次,本书的行文语言也很有特点,文笔洗练老辣,苍劲隽永。第二章《婚娶、远游与发妻之死》中,在柳永的发妻瑶姬去世后,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这正是大宋景德二年(1005)十一月间,在开封府祥符县地面一块新墓地上,只见阴云密布,万物萧瑟,哀乐似泣,悲风如诉,封土新隆,纸灰飘坠,虽无攀柏之哭,却有荀倩之痛。送丧者无多,均显乎悲戚之容;观望者不少,俱发乎唏嘘之叹。有道是:亡者已矣,生者断肠。一缕香魂归天界,几分幽怨几分愁。”(第91页)此段文字之精练隽永,非深富旧学积淀者不能为也。全书中像这样的行文叙述俯拾皆是。
毋庸置疑,薛瑞生的《晓风残月——柳永传》是一部集学术性和阅读性为一体的高质量的人物传记,值得广大文史爱好者和青年学子认真阅读。然而,笔者仍想就与此书相关的某些学术理念与作者商榷。前文已述及,柳永生平行迹的可靠资料非常有限,故在柳永研究中,诚如作者所言,“前人包括唐圭璋、罗忼烈等学者在内,都采取了模糊法”(第254页)。而作者坚持认为:“但学者的责任就是不断探讨,如果一直跟着前人模糊下去,学术还能前进吗?论资料依据,的确是没有的。在没有资料依据的情况下,合理推断也就成了我们寻求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惟一途径了。”(第254页)又借异史氏之口说:“看来从模糊法到具体法,的确是一种进步。至于具体得对与不对,那就靠后来者再否定了。学术本来就是在否定与被否定中进步的。”(第255页)作者不仅秉持这样的学术研究理念,也在他的苏轼词、周邦彦词、柳永词、杨万里诗等的文本文献整理和研究中是这样做的,其提出的若干论断在学界引起很大关注,有的已逐渐为学界所接受(比如周邦彦与大晟府无关的论断),有的虽然未能获得公认,但却切实推进了相关研究(比如苏轼创作的诗词同步说)。笔者认同薛瑞生的这一学术理念,但认为,既然是推断性研究,就应当在行文表述语气的肯定性方面留有余地,不宜太坚决果断。另外,具体到本书,毕竟不是专门的柳永研究学术著作,这种推断性文字的分量和语气似乎应当更为弱化,毕竟这类著作面向的普罗大众,绝大多数不是柳永研究专家,不清楚柳永研究现状,他们很有可能“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所以,面向这一类读者的作品应当以传递确定性的知识信息为主。不知作者以为然否?
另外,本书也存在一些瑕疵之处。其一,个别表述值得再推敲。第219页第1段说:“但据现有资料,柳永也没有任过通判的记载。”后文(第224页)却提及柳永任职苏州通判一事始末。前后行文龃龉。第237页第2段写道:“(柳永)只顺便瞻仰了秦穆公墓与东湖。”这里提到“东湖”,恐不确。北宋永兴军路凤翔府的东湖是苏轼在凤翔府签判任上时,于嘉祐七年(1062年)秋主事整修的。柳永此行在庆历三年(1043年)。清修《凤翔县志》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商王文丁十二年,有凤集于岐山。凤凰飞经雍城(凤翔古称)时,于城东水池饮水,故其水被称为“古饮凤池”。柳永行经凤翔府时,彼时凤翔城东应只有“古饮凤池”的遗址。苏轼疏浚整修后,因其在城东,故名东湖。东湖之名的命名权应归属苏轼,和他那首《东湖》诗很有关系。其二,本书也存在校对不严的问题,导致书中有个别文字错误。如第2页第2段倒数第3行“辩驳期间”,应为“辩驳其间”;第30页第3段第6行“纤丽之敝”,应为“纤丽之弊”等等。希望本书重印或者再版时能予以纠正。
《晓风残月——柳永传》是作家出版社正在陆续推出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之一种。此书的写法很有特点,能给读者于文学欣赏之外的文化史和文学史的丰富获益,是一本可读性和学术性有机结合的佳作,值得阅读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