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埃唐·苏西《太爱火柴的女孩》:后“父亲”时代的“寻母”之旅

加埃唐·苏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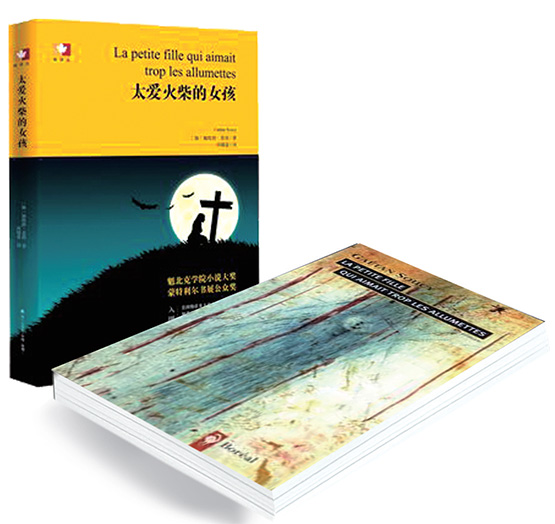
《太爱火柴的女孩》 中法文版
加拿大作家加埃唐·苏西的近作《太爱火柴的女孩》讲述的是一个由父亲之死引发的离奇故事。故事中有行为怪诞的人物、细思极恐的情节、丰富深刻的隐喻以及亟待解开的谜题:主人公是谁?父亲为什么自杀?母亲在哪里?他们的命运何去何从?这本福克纳风格的小说广泛涉及了宗教、神权、父权、女性等领域的新知,以故事的形式将西方文明在上帝被世俗生活“解构”后的挣扎与痛苦、迷失和希望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可以从很多角度予以解读。
后父亲时代
众所周知,建立在“上帝造人”神话体系之上的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这神话中伊甸园是人类的童年时代。上帝将亚当和夏娃安放在气候宜人、花草繁盛的伊甸园中,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亚当管理花草鱼虫、飞禽走兽,贡献着他的男性力量;夏娃帮助亚当管理,贡献着她的女性之美。男性力量与女性力量和谐互补,二人不分你我,彼此一体,成为理想的完满的人性。然而好景不长,狡猾的蛇引诱无知的夏娃吃禁果,夏娃把果子给了亚当,人类的堕落由此开始。为惩罚二人的犯错,上帝诅咒亚当必将终生忍受劳苦,而夏娃必受亚当管辖。
自此告别伊甸园时代进入父亲时代。完满的人性分裂成为男女对立,前者统辖后者。女性成为被囚禁的、沉默的“第二性”。这一时代在书中以女主人公的回忆为主,即父亲作为神甫(宗教神权)和公爵(世俗父权)统治的日子、母亲缺失的日子。父亲时代的特征之一是男性力量的失衡,产生暴虐(力量超出)和懦弱(力量不足)两种后果。在小说中体现在父亲用铁腕“统治”家庭,父亲的暴力和弟弟的懦弱就是这两种后果的代表。特征之二是女性力量的几近消失,即母亲的缺位,这种缺位造成的不仅是女性意识消失,也对男性力量造成伤害。在小说中体现的不只是女主人公和弟弟的“无爱”成长环境,还有看似强悍父亲的意外“软弱”。他偷偷去地下墓穴看望母亲和妹妹,常常拥抱亲吻不停流泪,与平日里强硬的形象相去甚远。终于有一天,父亲忍受不住痛苦的煎熬而自杀。
父亲之死标志着人类进入后父亲时代,宗教神权和世俗父权在人的理性和思考之下土崩瓦解后,传统伦理和规则不再具有约束力,人类只能以理性作为精神指导,然而理性最多带来“启蒙”。小说伊始,女主人公某天早上醒来后发现“父亲灵魂升天了”,她不得不学会独立思考。没有了父亲的《家教十二守则》,她只能以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作为行为的准则,然而《伦理学》晦涩难懂,也没有父亲般的约束力。在到村上为父亲买“棺材”时遇到督查保尔,主人公和保尔之间产生爱情,在他的启发下蒙生人的觉醒和女性的觉醒。保尔是第一个告诉主人公是“女孩”的人,并问她母亲在哪里,主人公这才懵懵懂懂地明白,她应该做的是寻找失落的母亲。
寻母之旅
主人公的寻母之旅先由寻妹开始。她终于明白在家中地下墓穴中,浑身缠满绷带的“受罚的义人”就是妹妹,二人是双胞胎、拥有“一模一样”的眼睛。这里暗示妹妹是主人公的第二自我,即真正的女性意识。小说中多次提到正是由于妹妹的沉默,主人公和弟弟才可以读书写字、开口说话,意指女性的“失语”给了男性以“话语权”。因此主人公下意识地寻找妹妹,其实是在寻找迷失的自己,而她不负所望找回了埋藏的自己和自己的名字“阿丽安与阿丽丝”。有个细节很值得注意,父亲还在的时候,弟弟几次提到他们还有个妹妹,跟她长得一模一样,主人公却想不起来。这说明在父权时代,男性敏锐地感觉到女性被埋藏的真正力量,而他害怕“受罚的义人”表示对这力量本能地惧怕。由此在神权/男权社会中,最恐怖的假想敌永远是变幻莫测的女妖。
妹妹已经找到,那么母亲在哪里呢?主人公发现一直以来躺在玻璃棺中的贵妇人就是那去世的母亲。母亲的形象模糊而遥远,只留存在主人公模糊的幼年印象和碎片式的记忆里。隐约记得她是公爵夫人,优雅娴静、美丽温柔、笑容满面,散发着温暖的气息。那时候是阳光明媚的,舞会是充满欢声笑语的。短暂而美好的童年对应的是伊甸园中的浪漫和完满。那时的夏娃还在,她的女性力量还在。主人公经历过父亲时代潮湿的天气、肮脏的生活和冷酷的规则,无比向往回到幼年的伊甸园,直到夏娃的失落导致母亲的缺位。
母亲之死是全书的一个关键点。书中借用父亲之口告诉读者,妹妹因为爱玩火柴烧伤了自己,烧死了母亲。书中还多次提到父亲“怕火”,并且时刻提醒妹妹不要忘记:火柴是危险的,不可以碰。父亲在文中的形象隐喻的是上帝。伊甸园中上帝吩咐亚当和夏娃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夏娃因为见那果子甜美,违背上帝旨意吃了禁果。导致亚当和夏娃受到诅咒,夏娃从此失声,亚当踽踽独行。妹妹偷玩火柴和夏娃偷吃禁果的形象就重叠在一起。火柴和禁果便具有多重内涵,在伊甸园中指触怒上帝的人之自主意志,在宗教神权中指的是解构神圣的理性启蒙,在当代社会指的是不受限制的工具理性。总之,火柴是危险的,因为夏娃的诅咒、母亲的消失都是玩火柴造成的不良后果。
母亲的消失是不可逆的,除了爱与温暖外没留下任何遗产。然而就是靠着这两种力量,怀有身孕的主人公作为未来的母亲,决定重建女性形象、恢复女性力量。她本能地选择与父亲不同的道路:她许诺要让女儿在爱与善良、美与关怀的环境下长大,并且吸取前辈经验教育她小心火柴。小说结尾,村民打败弟弟获得大宅的统治权,新的统治力量出现,主人公及其后代的命运也充满变数。对应到西方社会这一情节可能有两种理解:首先,随着女性/女权意识的兴起,女性逐渐开始建立不同于传统男权社会的全新话语体系。前辈女性几乎没有留下可继承的思想成果,她们必须“白手起家”,在波谲云诡的社会中这种话语的前途难以预测;其次,人性从神权/父权时代的异化中苏醒,重新寻找新的家园和方向,然而人如何把握工具理性、能否避免“引火烧身”还是未知数。主人公的寻母之旅还在路上,结局如何仍旧未知。
永恒的主题
《太爱火柴的女孩》是本沉重的、压抑的小说,然而在黑暗中也透出亮光,具体说就是作者对爱和对文学的歌颂。
小说伊始主人公缺乏女性意识认为自己是男性。即便如此也无法阻挡本性中爱的能力。女主人公对于母亲的记忆虽少的可怜,她还是本能地感到那不同于父亲的温柔母爱。即便成长环境冷酷严苛,她始终对弟弟残忍对待动物的行为不敢苟同,保持着自己的爱心和同情心。最重要的是她和保尔之间热烈而美好的爱情,面对爱人她本能地心动羞怯、不知所措、产生强烈的爱欲。爱情帮助她复苏人性和女性意识,两者并不矛盾,后者只有在前者的基础上才能产生,而前者又因为后者而丰富完整。因此女性意识的觉醒不是男性的对立面,而是整个人性走向完善的必经步骤。在这满目疮痍的家庭悲剧中,主人公未泯的爱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份令人振奋的礼物。回顾历史,爱与人性往往能在丑恶中开出无畏的美丽花朵。
作者多次通过女主人公之口强调文字的重要性。她与保尔一样不屑于争夺父亲留下的巨额财富,沉醉于文字、诗歌之中。正是这份对文字的热爱让二人都保有难得的人性。主人公经历父亲之死、爱人之死、村民来袭等波折,却在临产之际仍坚持将经历写下来。在时间的长河中惟有文学和故事永久——这正是作者通过小说试图表达的。文学根植于人的思想、人性之中,也会与人性之美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