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品荐特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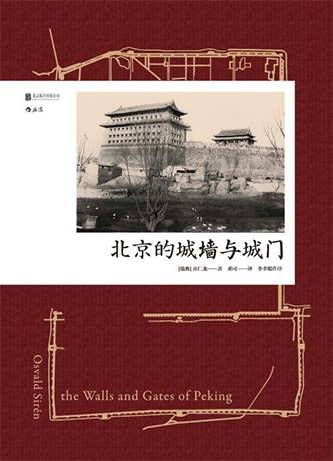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瑞典]喜仁龙著,邓可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3月出版
1920-1921年,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正激荡在古老的北京城。精神形态的老北京,经历着革故鼎新的剧变。物质形态的老北京,却满披沧桑衰朽之迹,肃穆依然:内外城轮廓齐全,一座座城门形制完整。置身其间的居民们,当时大概谁也没想到,将来的北京人还会有怀念这些老城墙和老城门的一天。可能正因此,对1920年代初期北京的老城墙和老城门的状况,做了详细记录和生动描述的这本《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不是出自中国人之手,而是出自一位专程来寻访中国都城建筑之美的外国人——瑞典艺术史学者喜仁龙(Osvald Sirén)。
北京古城的城门和与之相连的城墙,以及由这些城门和城墙延伸、分隔开来的街道和园林,构成了一个深深吸引作者的人文历史意义上的美的整体形态。为了详尽记录这种深切的美感,作者全面地调动了他身为艺术史研究者的各种专业素养。他反复细致勘察了北京城门和城墙的各处现场,尤其留意和分析嵌入城墙和城门墙体的碑铭砖刻,因为那上面留着明确的建筑信息。此外,为把有关北京城墙和城门修建、改造的历史沿革和构造形式变化彻底了解清楚,作者搜集、查阅了大量的地方志。这个过程中,作者请教和求助了许多中国师友。比如为他精心制作砖刻碑铭拓片的,是他的中文老师周谷城先生;为他翻译地方志的是培华女校的外教包哲洁女士。而穿插在书中的五十多幅城门和城墙的形态图和结构图,又是经国际友人介绍来的中国画师,遵照建筑师和作者的具体要求,按严格的比例和精准的尺度绘制成的。除了这些,作者还在书中附了他亲手拍摄的百余幅北京城门、城墙的清晰照片和少量作为参照的西安和山东青州的老城门和老城墙照片,留驻了难以再现的珍贵历史风貌。
全书八章,每一章都写得结结实实,并且优美流畅。第一章概述中国北方筑墙建城的历史;第二章回顾北京旧址上的早期城市;第三章综述北京内城城墙;第四、五章依东北西南之序,分别介绍北京内城城墙的内侧壁和外侧壁;第六章介绍北京外城城墙的内侧壁和外侧壁;第七章分四节,依次介绍内城四面的城门;第八章介绍外城城门。各章首尾都是优雅、洗练的散文笔致的场景刻画,隐含着趋近而又走远的行踪,和选准风光韵味最足的时刻或季节的独特视角。从容展开的建筑流变和艺术形式方面的梳理、讨论,一概放在各章中部。但即使是在交代这些很容易让读者觉得生冷铁硬的专业内容时,也常会跃出些灵动鲜活、诗意盎然的片段:“城门的魅力和个性,随着季节和光线不断变化,但夏季无疑是它最绚烂迷人的时节。高大的垂柳俯下身子,绿色帷幕般的枝条几乎贴到尘土飞扬的地面上,椿树的树叶则轻抚着城墙。孤独的行者骑着驴穿过这座城门,昏昏欲睡。这里的空气沉甸甸的,布满尘土的道路和石桥被太阳烤得炽热。人们都尽量避免走动,除了一群被晒得黝黑的顽童,他们在浑浊的护城河水中与白鸭一起扑腾、嬉闹。这是一幅北京夏天的缩影,因为有了这座古老的城门,衰落的城市和恬静的乡村被美妙地联系起来。”(引自第八章,见该书第17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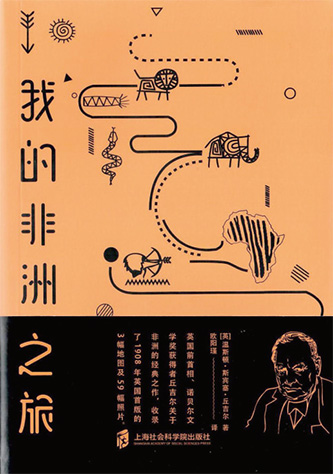
《我的非洲之旅》,[英]丘吉尔著,欧阳瑾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
79岁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早年就已展现出过人的写作和演讲才华。这本《我的非洲之旅》是他33岁担任英国殖民地事务部次长时,执行视察东非英殖民地的公务期间的旅程纪实。全书11章,最初曾在连载过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海滨杂志》上刊登过,1908年结集成书时内容又有所增添。
依作者在前言所说,书中各篇都是他在完成当天行程后,利用一个个漫长而炎热的午后写出来的。而通读全书,可以从诸多细节知道,丘吉尔的这趟非洲之旅,几乎时刻都面临疫病、蚊虫、暴晒、海拔等多方面威胁对身体健康和安全的考验。一路上,壮美的自然风景、奇特的种族风情,始终与作者隐隐的一种戒慎恐惧的心理提防相伴随。但很显然,这并没有影响作者书写这部旅行记的热情。遍布全书的各种画面感极强的描写,表明作者对他所到之处都有耐心的观察和全身心的投入。或许这只是因为职责所迫、使命在身。或许这正是作者化腐朽为神奇的一种写作能力的体现。
起于东非东南角的印度洋边的蒙巴萨岛,沿乌干达铁路向西北,经内罗毕至维多利亚湖,又到恩德培和坎帕拉,再顺白尼罗河而下,最终抵达东非北部的苏丹喀土穆,这趟几乎纵贯整个东非的长旅,仅看它标在地图上的线路,就够有气派。对此,丘吉尔用毫不吝啬笔墨的状物和写景,有力地呈现了它应有的分量。而行至内罗毕、恩德培、坎帕拉、喀土穆这几座政治中心城市之际,他也适时适地好像触景生情似的,探讨起了如何针对东非特殊的社会、人文和地缘条件,实行更有效、更合理,也更符合英国利益的殖民政策等严肃政治问题。
还是干脆利落而时带诙谐的文风,还是惯以具体的事例代替烦琐的思辨,坚定的政见主张、开阔的世界视野和顽固的帝国立场、狭隘的种族偏见,却明暗相间着,一股脑儿都流露了出来。这显见着时代、国族和文化的局限,同时也显见着写作者个人的坦率和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