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心灵忏悔及城市启示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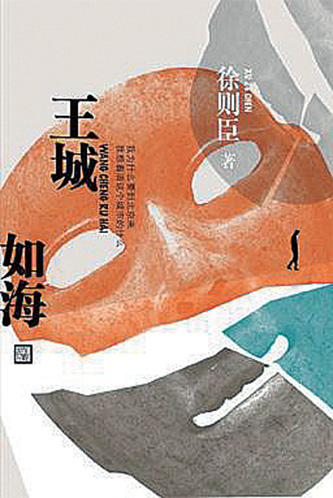
“70后”作家徐则臣一直经营着他的“进城文学”,他对城市中各色人等,特别是对底层小人物的刻画已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新作《王城如海》在延续以往平民意识的同时,更是聚焦于城市知识分子的心灵忏悔这一极具深度的主题,读来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的确,没有比惊心动魄一词更能形容我对这部小说的阅读体验。我们看到,靠着自身努力而成功“进城”的知识分子为此付出的代价竟是如此的令人发指,城市中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的背后原来蛰伏着无数罪恶的灵魂。不仅如此,《王城如海》还涵盖了不少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诸如阶层固化、贫富差距、伦理焦虑。这些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原本就令人触目惊心,而作家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当下火热的现实中去,以现实主义的风格完成了他对形形色色的城市风物的考究。
《王城如海》的主人公余松坡是一位留洋归来的先锋派戏剧导演。围绕余松坡的遭遇所牵连出的故事线是小说的重要线索之一。他的现实主义戏剧所引发的争议早已超出了他的想象。因为剧中涉及的蚁族问题,媒体们纷纷围绕着这部戏剧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口诛笔伐。此外,最令余松坡揪心的还是他的堂哥余佳山。他深知余佳山的悲剧是自己亲手写的检举信造成的。尽管真相无人知晓,但自己的那一关怎么也过不去,这几乎成了余松坡永远的隐痛。“也许如此无限地放大没有意义,但一想到我曾在浩大的历史中对一个人伸出卑劣的告密之手,我就惶惶不可终日。”也就是说,余松坡对自己当年的行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所悔恨的正是自己“将一个无辜者送进了监狱”,而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一直折磨着余松坡的身心,让他不得安宁。
不妨说,余松坡以一个忏悔者的形象出现,从而传达出一个知识分子精神内在的反省和批判,表现为道德的重负和自律。不过,作家之所以写余松坡显然不是为了做简单的道德评判。相反,作家倾注于主人公身上的,更多是同情,而非谴责。像余松坡这样一个出身农村的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成功”进入到城市已属不易。他一方面享受着“成功者”的待遇:住豪华别墅、开豪华汽车、有保姆伺候、衣食无忧;另一方面也承受着城市带给他的不安:戏剧引发的争议、无暇享受家庭的温暖等等;更重要的是作为告密者带给他的罪恶感。而这一切何尝不是一个“成功进城者”所要付出的代价呢?
小说的另一条线索要从余松坡家的保姆罗冬雨讲起。罗冬雨同样是农村出生的女孩,同样是来到北京打工,她一面与余松坡的家庭相连,一面和她的男友韩山和弟弟罗龙河相连。更重要的是,作家通过罗冬雨展现出的北京风物的另一面,也是更为广阔的一面,那就是底层民众真实的生存状态。
小说中的罗冬雨、罗龙河、韩山、卡卡、鹿茜等人同样是在北京打拼的异乡人。做保姆的罗冬雨、她的大学生弟弟罗龙河、她的送快递的男友韩山,以及由此牵连出的一连串的底层人物,包括送快递被汽车撞死的卡卡、主动献身的女大学生鹿茜。徐则臣不动声色地将一群走投无路的人呈现在小说中——和这些底层人物相连的是:雾霾、三轮快递车、“蚁族”们肮脏的租住房、快递物品、车祸,以及不牢固的爱情等等。这些蛰伏在北京城市底层的景观无疑是整部小说最为“现实”的地方。作家既写出了这些“北漂”底层小人物艰难的生存处境,更写出了他们内在的精神焦虑。他们为了能在城市立足,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鹿茜),还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卡卡),更有的因为愤怒而放手一搏乃至酿成了悲剧(罗龙河),不得不说,他们的悲惨命运在小说中着实达到了催人泪下的程度。他们因为惨痛的代价而愤怒,又注定因愤怒而付出更惨痛的代价。他们是一群因为走投无路而不得不走上绝路的人。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我们理解了《王城如海》的底层书写所呈现出的困境:如果说此前徐则臣小说表述了走投无路的人们的活的状态,那么《王城如海》则更清晰地将底层人物的宿命暴露无遗,这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们的死的注定。
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把小说的两条线索放到一起,做一个对照性的阅读,就不难发现,《王城如海》所描绘的北京风物是以余松坡为代表的“暂时成功进城者”和众多“想要进城而不得”的底层小人物这两个阶层组成的。以这两个阶层为核心所讲述的故事巧妙地构成了中国社会内在危机的四则寓言:乡村衰败的后果勾连着检举别人的快感(余松坡的告密);谋求上升机会的人只能以自轻自贱的方式生存(鹿茜的献身);肆无忌惮地抢占资本造就了底层的走投无路(卡卡的死亡);资源分配的不公最终演变为毫不留情的阶层对立(罗龙河的复仇)。
事实上,无论他们的“进城大战”是否成功,这些人物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无一不是作为异乡人的文化身份而存在,他们都是乡土社会的逃离者与背叛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城如海》通过城乡关系去窥探北京城市的风貌,进而揭示出城市人的生存状态。蛰伏于北京的底层人物,他们宁可忍受着城市的种种弊端(无论是环境的雾霾,还是精神的雾霾),也无怨无悔地希望扎根于此。就连“成功者”余松坡不也同样不愿坦诚面对自己的过去吗?也正因如此,《王城如海》对现实特别是城乡关系的理解止步于表象的暴露,而无法深入到对资本、权力等层面做出反思。它看似在探讨城乡对峙的紧张关系,但总是在紧要关合处悄然走笔。无论是对底层苦难命运的思考还是对城市知识分子心灵忏悔的反省,作家的态度都可谓如出一辙。无论是无法忍受城市规则的“蚁族”群体,还是长期有着在国外生活经历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身心都被现代城市所折磨、压抑,而摆脱这种折磨和压抑的途径,而且是惟一的途径,就是向隐喻着前现代的乡土中国妥协。
不妨说,徐则臣敏锐地捕捉到了人们内心深深的焦虑和不安,却也像每个人一样不知何以如此与怎样不如此。小说基于某种现实,将北京城市的各色人等、器物共同熔铸于一个内在性的趋于崩塌的“紧急时刻”。
(《王城如海》,徐则臣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