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体验与文本世界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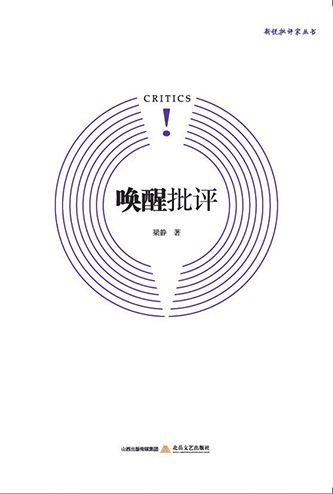
对于梁静来说,曾经从事小说与散文的创作经验、业余性地进行文学批评的身份体验,消费时代女性角色和社会处境的生命困惑等等,都化为她进行文学批评乃至文化批评的话语资源——话语场域的边缘、理想情怀的晦暗、自我走向的探索,这些共同形塑着她的文学批评路径,而她集中于思考女权主义、时代症候、文化跨界等领域的中国化、本土化、日常化的实践问题,由此确立和延续为她的批评话语基石,而在批评风格方面,梁静的文化批评呈现出鲜明的分析阐释趣味。
首先是强烈的分析冲动和言说趣味。梁静的文学批评兼及艺术批评,尽量逃避学科化的专业术语——那些或陌生或冗长或奇异的词汇总是让人望而生畏,更未事先设定理论框架,将艺术文本削足适履的作为印象式、模糊性乃至想象性论点的注脚;相反,她对文学文本、影视作品乃至文化现象的分析,总是循着观赏者——游历者——反刍者——超越者的心理思维逻辑,直至将批评效果编织为言说的黑洞——那种源于大众的生活思考和文化浸淫却又普遍难以自知的言说觉醒。无论是涉及文学文本还是影视文本,梁静的文学批评总是带着强烈质疑和问题意识,以反叛者的姿态遵着时代语境——个人经验——文本呈现——理性思考的思路全面涌入,这样的批评资源和方式,在保证了批评背景具有一定的时代广阔度和历史纵深度的同时,更实现了批评家—作家(作品)的“对话”。
其次是女权主义的价值实践。梁静的文学批评最鲜明的价值标准是女权主义——一种混合着性别民主、个体压抑、生命体验的文学标准。她的文学批评对象大量关注国内外的女性作家和女性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在批评言说当中同样将重心置于各类女性的命运挣扎和生命疼痛,甚至在一些批评判断中将主人公是否表现出女权主义和女权独立作为作品成败的标志。梁静自称对女权主义价值理论有着特殊的偏爱,同时她的这种将女权主义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在我看来也有可商榷之处,而“诗无达诂”某种意义上决定了给文学的高下优劣下一个绝对公认的标准是徒劳的,但是梁静这种对女性作家作品、女权主义批评实践的“偏执”背后,是她生命体验的一种投射——她是借用对女性作家和女权主义的批评表达着她的生活经验和心灵探寻,这是对女权主义生成根源的遥相呼应,而非将之仅仅作为一个批评理论武器。在看似倔强的批评姿态背后,是一位有着多重生活思考经验的女性批评家。
再次是批评文体的自由跨界。梁静批评文本的自由跨界,有着文化散文的理性与思索、史料与纵论,也有抒情散文的自白与宣言、感悟与情绪,既有着小说叙事的策略与技巧,也有着理论剖析的客观与冷酷。梁静是将批评文本作为一种独特的美学作品在进行创作,而她作为批评主体的在场,让其扮演着批评文本空间的引路人,让阅读者在自由漫行和驻足观望中,寻找着文学世界隐藏的密匙,打开一幅幅奇异诡谲的景观之门。无论这种文本景观的旅行是长途跋涉还是短途观光,“完整性”成为她进行文本批评的一种整体思维——批评文本的高度浓缩的信息、精湛明了的评论、贴切恰当的佐证、饱满充沛的激情,都使梁静的批评文本具有了散文的诗意和论辩的理性,在可读、深度、广度方面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深度融合,也成就了其独特的批评文体和风格,梁静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风格的批评空间,并且充满着无数的可能和方向,我们期待着她能将这条路走到极致的完美!
(《唤醒批评》,梁静著,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