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生活真实的歌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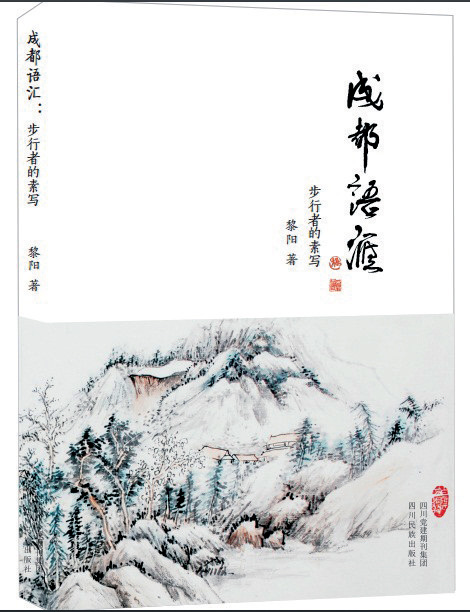
新诗百年纪念,刺激着诗坛热闹起来。而在多媒体智能化的时代,诗人们显得忙迫且有些焦虑。众声喧哗,炫目的光彩淹没了沉静的深入。当各种炒作与表演吸引着众多眼球的时候,潜心于经营诗歌文本的诗人,显得多么宝贵。
黎阳就是这样一个诗人。他汇集于《成都语汇》的200余首诗,篇篇都是真诚之作。正如他自己所言:他从来不写没有去过的地方,从来不写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出自生活,发乎真情,他以一个漂泊者的歌吟,共鸣着那些寻常的心声。
黎阳是黑龙江人,千里独行,最终来到成都。其间辗转各地,历经坎坷。他蹬过三轮车,卖过菜,做过工人、厨师、教师、经理人、职业歌手等。生活的艰辛与阅历的丰富,练就了他不服输的性格,也成就了他贴近生活的诗风。现在,他是《星星》诗刊的一名编辑,他在成都红星路上找到了人生的坐标。从这个高度望去,云卷云飞,满眼都是诗的风景。于是他扎根巴蜀大地,吸纳天府灵气,在这个已然超越了地域文化概念的诗的沃土上,耕耘并收获。
《成都语汇》其实不是成都的诗歌地图,尽管也展现了成都的一些地方文化标识。如天府广场、春熙路、宽窄巷子、金沙遗址及新建的高楼、地铁等等。作为一个外乡人,他的感受是:“盆地就是这么大,根本不在乎溢出的是得或失/从天府广场的肚脐上来回徜徉,汗水也滴成池堂”(引自《盆地》)。也许黎阳在这里想表达的,是四川盆地的广阔与包容,是生活其间的世事沧桑,是挥汗如雨汇集为池,是人杰地灵仰止于堂。这个“堂”,在诗人心里,具有庙堂的意义。对此,他是充满敬意的。但同时他又写道:“盆地还是个弧度,有些田野的味道/有些腐烂的味道,有些没有味道”(引自《盆地》)。新旧交替,不禁让人想起“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百味杂陈或淡而无味,也许是他曾经感受过的生活况味。
可贵的是,尽管千回百折,黎阳的人生态度始终是积极向上的。“习惯用一个方向,决定幸福/只有目标简单,生活才没有那么多的琐碎/当抉择的脚步不再摇摆,路边的草也就伸直了腰继续生长”。因之,他要“像一首好诗那样拨动心弦”,在生活与诗歌中,活得阳光,活得坚强。《步行者的素写》应是他的自画像:
都是同一条路,在时间的沿途
缓慢和艰难的只是目光深邃
他总是低着头,看着布鞋前面的石子
听风和车辆在身边越过
应该有的雨水一点也不会少
电闪雷鸣的时候,只能皱一下眉头
或许看到飞机的时候,也会大吼一声
不管它去哪了,都是一个尽头
挽起的袖口上,都是汗渍
裤子上有若干口子,每口子都有影子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奋斗者的形象。他正值中年,目光深邃,低头走路,仆仆风尘,行步艰难,一身汗渍。“布鞋”、“挽起袖口”,显示出人物身处底层而又活力四射的风采。这种来自真实生活与切身感受的诗,是无法“做”出来的。
再看:
看不得远了,就低下头走路
只要脊骨还能挺起骨髓里的正
那些血脉里的澎湃先抑制一段时间
头低下了,天空没有低
视野里的一切不会有太多的变化
呼啸的风 劈头盖脸的雨
是躲不过去的……
——(《低下头,路就越来越清晰》)
奋斗的人生显然是不容易的,只能目不斜视,走自己的路。面对重重阻隔,面对世事的复杂,他曾感叹:“我们都有最后一口气,都是这河水里被无视的一滴”。“我看不到笑容背后那口井有多深,只是惋惜那勾心斗角的眼神里满是悲哀”。在他看来,做人要正直,身处底层也有自尊。因之对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比较敏感。对现实社会中的阴影,他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写道:“我继续做一株荒郊里的野草,伸直自己的腰,抬起自己的头”。他本可以“中年停顿”,但是他没有停顿。因为“流浪的汉字终于在自己的词典里,/找到位置 阳光出现在合适的天空/九十九朵玫瑰的芬芳 充盈/一双泥泞的鞋子”。显然,这时候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他对自己的奋斗充满信心和感动。这种发自内心的抒情,具有最为朴实的感染力。
黎阳的诗真诚而自然。他写爱情、亲情和友情,都有确切的指向。比如写母亲:“这水是浮草今生惟一的命/千里的云和万里的路/抵不过母亲眼里的一滴泪水”。“一个人的时候,我从来不喝酒/只是点一支烟,泡一杯茶/坐在沙发上流泪/这时候我只会想起母亲”。比如他写朋友,便一一为他们画像,显得十分生动。他写人的正面反面,揭示人性的复杂。他写都市生活的场景,都很寻常和生活化。而烟和酒,其实更多是他思索与焦虑的象征,在诗中成为一种道具。
平凡而并非平实。黎阳诗的语言有流动之美。形象的跳转,通感的运用,抒情中的比拟,形成他的个性。“星光闪耀在每一株绿草额头/露水轻轻地延缓夜的愧色”,“悠悠弦乐低回的是散淡之念/藤椅上的正襟危坐,与风雅无关/酒是一缕故乡的米香/只有喉咙里的辛辣才能化开乡愁”,“把所有的旅途一饮而尽”,等等。作为一个诗歌编辑,他毎天会读到大量的诗。他“恐惧那些让我反胃的文字”,对低俗、粗鄙、矫情、造作不以为然。他以严谨的态度沙里淘金,并认真向好的诗歌学习,提升自己并抵制那些反抒情、反人性及以丑为美的伪作。内容与形式的和谐,语言与情绪的协调,使他的诗显得那么亲切可信,一如生活本身的丰富与美好。
对生命的终极追问,是使诗上升到哲理高度的必然。黎阳显然未刻意做这方面的努力。因为“活得勿忙,来不及感受”,他还没有更多形而上的富余。但生命何由而来,何往而去,我是谁的千古追问,总是深埋于每个诗人的心里。在《氲氤中的三星堆遗址》里,他写道:“在历史的氲氤里走几步都是艰难的跋涉/那些闪烁的金属后面总有一双眼睛/看着我们,感受不到任何表情只有阴冷”。他承认自己对文物有一种“莫名的抵触情绪”,“敬畏之中还有恐惧”。其实这就是一种生命意识。而在《偶遇孝泉,指尖都在流汗》中,他写道:“东汉的汉一直流到这棵树下/二十四孝,以及一门三孝/笑就不在虔诚的脸上开放了”。他对孝道的理解,更揭示了他对生命的敬畏。很多虔诚的脸上,袒露出所谓的虔诚,实则心灵是虚伪甚至是肮脏的。这里不仅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认知,也有对当今人性弱点的批评。而“指尖上冒汗”的写法,也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得更为充分,透露出黎阳的艺术表现能力。这类诗,在黎阳的作品中不是太多,但值得关注。
总之,黎阳是贴近生活、直面人生、书写真实、抒发真情的诗人。他的歌唱能应和普通人的心声。他平凡、积极,备尝甘苦,不舍岁月。他带给人们的,是实实在在而又健康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如诉家常的审美愉悦。
(《成都语汇:步行者的素写》,黎阳著,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