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作家师陀相遇

经典作家之师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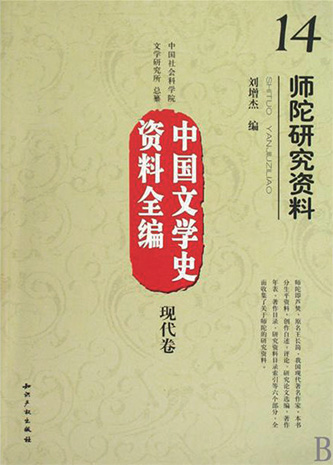
一
我和作家师陀先生的相遇带有某些偶然性。上个世纪70年代,高等学校对青年教师提出了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明确要求。当时,我对地域文学研究有兴趣,就跑到了开封市图书馆查阅河南现代作家的资料。在图书馆开辟的一个大型专栏里,工作人员向我介绍了河南作家师陀在上海出版的十几部作品的内容与学术价值。专栏中所介绍的《谷》《里门拾记》《黄花苔》以及《大马戏团》等一长串作品的名字,当时我还相当陌生。我兴致勃勃地在阅览室翻读着这些内容新鲜的作品留连忘返。图书馆的专栏还醒目地介绍;师陀原名王长简,开封杞县人,26岁在上海获得了《大公报》文艺奖金,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我在图书馆借了几部师陀的作品,后又在河南大学图书馆补借了几册市图书馆没有收藏的师陀著作。我翻来复去地抚摸着这一摞师陀作品,颇有一种满载而归的获得感。坐下来细心品读这些格调和谐醇美的作品,能够感受到作品情感的深沉,自己很快就被一种特异的引人入胜的气氛感染着。
事情往往会有不经意间的巧合。就在我用心阅读师陀作品的1979年秋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发起的讨论出版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丛书的学术会议在安徽黄山召开。到会的成员是高等学校的教师以及文学研究单位的研究人员。我应邀出席了这一盛会。到会人员就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出版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上还组成了负责丛书出版的编委会。第一批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目录,经会议推荐和到会人员自己的申请,很快就确定了下来。编委会宣布,《师陀研究资料》由我编选,书稿完成后交北京出版社出版。1984年1月,北京出版社按预定计划,出版了这部30万字的《师陀研究资料》。
《师陀研究资料》编选的过程,是我不断向师陀先生请教、学习的过程,我和师陀的友谊在不断的加深。师陀先生慈眉善目,说话慢声细语,有着中原人特有的质朴与诚恳。《师陀研究资料》的出版,激起了我进一步投身师陀研究的热情。自己当时暗下决心,将来要为出版《师陀全集》尽到自己微薄的力量。从1980年12月到1988年3月,我和师陀先生之间,书信来往不断。在现已出版的《师陀全集》和《师陀全集续编》里,收入了我们的来往信件近120封。我发表的研究师陀的文字也多达十几万字。在此之后,我和师陀先生的交往更日益密切:或我去上海向他请教问题,或他来河南讲学,重游故里,回杞县华寨村凭吊祖坟,等等,这些活动多由我以主人的身份安排、陪同。虽然师陀先生是前辈,我是晚生,我们会面时总能做到身心放松,无话不谈。连一起在我家里吃饭的时候,师陀先生对我妻子也总是以嫂夫人相称。他那小说家诙谐幽默的谈吐,顿时就使餐桌上的气氛轻松起来。
在与师陀先生长时间的接触中,我还能感受到,作家的生活经历,特别是那些刻骨铭心的经历,实际上是他储存于心中的创作内动力。其中的一些人物和事件,不时地会使作家产生宣泄的强烈欲望。当经过长期的酝酿,改造、构思,某些偶然事件的触发、刺激、联想,这些现实生活的信息就会复活,使师陀神思飞跃,心物契合,从而超越时空限制,在主体对外物感知基础上,实现主客体的相互交融,终于使他文思泉涌,创作出了优美华章。我从先生的不少作品里,总能品味出一种特有的人生滋味。闪现在他作品中深刻的思想感受,常常凝聚成具有幽默感的简短句子,内蕴极耐品味,使人心领神会。
二
师陀先生逝世后,首先向师陀夫人陈婉芬女士建议出版师陀遗著的,是美国学者夏志清教授。1988年11月9日,获知师陀先生逝世的消息后,夏志清在写给陈婉芬女士的慰问信中说:“刘增杰先生主编的,他亲自把《师陀研究资料》送给我了。此书对研究师陀极有用”。信中又说:“刘是开封市河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不知你同他有无信件来往。师陀尚未发表的遗稿,日记,书信,可由你同他合编出版。”其实,早在4年前,我和夏志清先生已经有过友好的会见。那时候,正是国内高校纷纷走出国门,扩大与国外高校进行学术交流的年代。建校已经百年的河南大学,毕业校友遍布世界各地。1985年,我随同河南大学访美代表团访问纽约时,旅美校友就特意安排我们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在夏志清先生书房与他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会见。我向夏志清先生赠送了出版不久的《师陀研究资料》,他也向我回赠了自己新近出版的著作。会见亲切融洽。夏志清给陈婉芬信中所述我向他赠送《师陀研究资料》事,指的就是这次我们在纽约的会见。
我和陈婉芬女士也相识较早。师陀先生逝世后,我去上海商讨出版《师陀全集》时,更得到了她全力的支持。当时,我由妻子潘国新陪同,专程到上海图书馆查找师陀先生的著作,同时也到师陀家里拜访了陈婉芬女士。陈婉芬女士和儿子王庆一,对我们十分热情友好,一见如故。当我向他们说明,出版《师驼全集》要做的工作,除我正在筹措资金外,还需要发掘那些虽然没有发表,但却有学术价值的师陀日记、未完成的手稿、以及读书札记,等等。听了我的介绍,陈婉芬女士和王庆一当即就行动起来。王庆一在母亲的指挥下,脱掉外衣,爬高上低,在屋子里翻箱倒柜,累得通身是汗。不到半天时间,就把师陀先生未发表的日记、手稿、笔记等,一摞一摞地放到了我们面前。现在出版的八册《师陀全集》中的日记、回忆录、备忘录等,都是从他们提供的材料中选录出来的。没有家属的通力合作,《师陀全集》的出版是不可能实现的。
研究者的相互合作同样也不可缺少。《师陀全集》2004年出版后,清华大学教授解志熙和他的研究生,也陆续发现了一批师陀具有学术价值的新材料。2013年出版的两册《师陀全集续编》,就收入了他们新发现的师陀的长篇小说《争斗》,以及连载于上海《学生月刊》后5期的长篇小说《雪原》的后9节,从而使《雪原》前9节和后9节完整地合到了一起。《师陀全集续编》还收录了大量友人致师陀的信件,以及一批研究师陀的新成果。我时常静夜沉思,没有研究者之间的密切合作,相互配合,要出版一位作家比较完整的全集是很难想象的。
在《师陀研究资料》出版后,除了出版《师陀全集》《师陀全集续编》外,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我于2011年还出版了《师陀作品新编》。以我粗浅的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新编丛书》的主旨,应该是要还给读者一个入选作家的全人。师陀是一位长于短篇和散文而兼备众体的作家。本此理念,我意识到,入选的师陀作品,既应有作者的名篇佳构,也要收录能够展示他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别类作品,像散文诗、学术论文以及作家所撰写的考证文字。《师陀作品新编》就收入了师陀关于《金瓶梅词话作者的考证》,以及关于《蒲松龄〈聊斋志异〉草稿的下落》等考证文字。师陀生前曾经坦率地告诉我,《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到底是谁,是“我没有做完的工作”,“作为这位伟大作家的同胞,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为世界文学史提供一些他的材料”。师陀一再惋惜地坦承:“我个人也许挨不上这个机会了”。他的话虽然是一种失望的自责,可话中所显现的探索精神,却是他含蓄地展现给后来研究者的旗帜,期盼新的一代研究者完成前辈的未竟之业。在《蒲松龄〈聊斋志异〉草稿的下落》一文中,直到1979年4月,师陀还郑重呼吁:对于“流传下的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惟一草稿,绝对不能听其湮没,或被虫蛀鼠啮,以致毁灭”。师陀的其他学术论文,如《我的风格》《“京派与海派”》,同样阐释了作者开放的文体观,以及他那不群不党,向往艺术独立天性的人生哲学。文学精神古今相通。师陀的古典文学修养,除了为他开拓出了新的创作领域,更潜移默化地使古代文学的精神血脉,渗透流动于他的作品中,看似了无痕迹,却又无所不在,自然天成。
三
师陀的生命历程充满着曲折。1941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前,有人就曾经在汉奸刊物《中华日报》上,盗用师陀的笔名芦焚发表文章,混淆视听,迫使师陀在《中华日报》上刊发声明,改名师陀。写作勤奋,靠版税生活的师陀,解放前却经常处于无法保障最低生活需要的困境里。多亏好友巴金的支持,他才渡过了难关。巴金写给师陀的几封短函,再现了师陀当时生活的窘迫无奈。巴金在信中说:“长简,信收到。开明版税单至今尚未送来。这次据我估计只有七八百元。今天在文化生活社为你借支了一千元,由交通银行汇上,请查收。开明版税取到后,即可汇上。一千元还不够买一条三砲台香烟。……”当时,巴金要动身飞香港,因为怕师陀的生活遇到新的困难,在写给师陀的另一封信中又说:“你每月的饷我已关照过,托文华会计直接交交通银行汇给你,希望不致出乱子。”师陀在后来写给我的信中说:“要说对我进入文坛帮助最大的人,那是巴金,他不但出过我许多书,对我私生活方面也很关心。”据我统计,从1936年5月到1948年6月,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就先后出版了师陀的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野鸟集》《无名氏》,散文集《上海手札》,长篇小说《马兰》,以及四幕话剧《大马戏团》。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很少有哪位作家得到过巴金如此的器重。师陀逝世后,在题为《怀念师陀》的文章中,巴金深情地说,“师陀是难得的文章家”。“难得”两字的分量很重,这是巴金从历史比较的视野做出的极为准确的判断。持这种看法的当然并非巴金一人。卞之琳干脆称师陀是天生的小说家,而楼适夷则在给师陀的信中说,“你的创作自有独自的风格,既不为一般俗流所注目,但在文学史上将永远是坚实的存在。”
刘西渭早在1937年6月1日《文学杂志》1卷2期就撰文:“我记得第一次芦焚先生抓住我的注意的,是他的小说的文章,一种奇特的风格,在拼凑,渲染,编织他的景色,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所。……诗是他的衣饰,讽刺是他的皮肉,而人类的同情者,这基本的基本,才是他的心。我们必须多读几遍那篇动人的杰作《过岭记》。”(收在《谷》里面)唐弢以文学史家的眼光评价芦焚(师陀)时说,“作者善于描摹世态,刻画风习,而时复带着揶揄的口气,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指出芦焚的《谷》,“以其糅合了纤细与简约的笔……创造了不少真挚确切的人性,获得了《大公报》的文艺奖金。”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师陀长篇小说《结婚》的评价极高,认为师陀的长篇小说《结婚》,是“真正值得我们珍视的作品”;还说,若纯就“叙述技巧与紧张刺激而论,《结婚》的成就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中是罕有其匹的”。
在评论师陀的文字里,我看重的还有署名亚蓝的《里门拾记》一文。1939年,在辅仁大学上学的亚兰(张秀亚),主持《辅仁文苑》,她在《里门拾记》一文中宣称:“真理是永远年轻的,看见真理的人,也永远是年轻的,这个青春不去的人,虽然是许多人心中的‘魔鬼’,却是作者崇拜的巨人。我们却不妨打开窗子,直截了当地说:这个巨人,也就是芦焚先生逼真的影子,自我雕塑。”文章还说:“提到作者的艺术手腕,说是小说家的,倒毋宁说是更近乎诗人。这也是由于他性格的使然。他多思虑,忧郁,伤感。性格是内倾的,因而 他富于内心的生活,所以,他的文句,是翻译自狡童般灵巧神经的小语,细致情感的箴言。作品有着朦胧淡远的韵味,篇篇像是和谐雅致的散文诗,不遇着个细心的读者去品味,其中的那巧妙,那美,便将隐没不彰。”师陀的内心世界,蕴藏着充沛的精神容量。亚蓝的话,准确地揭示出了师陀在创作上所具有的开路者的魂魄。
总体而论,师陀60年的创作生涯,虽然经历过风风雨雨,有过无奈与焦虑,但他总有一种看透真相后的平静与安详。师陀不慕虚名,低调善良,忘怀得失,随心随意随缘,自然洒脱的创作心态成全了他。心路相通是缘分。我与师陀先生的相遇,带给我的是灵魂的自省。阅读是一种文化修养。作为师陀作品的读者,我要像先生那样永远保持人生的平和与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