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乐之城》:你自己的梦想之城

《爱乐之城》导演达米恩·查泽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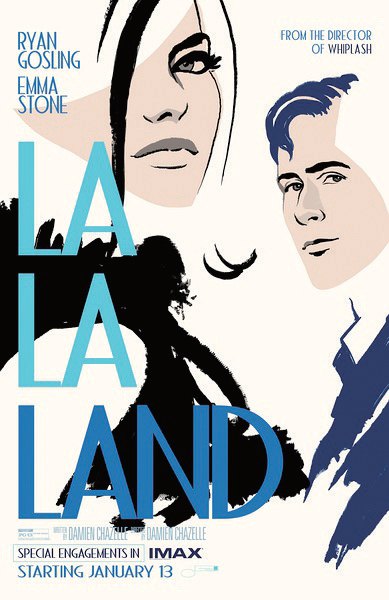
《爱乐之城》电影海报

《爱乐之城》电影剧照
2017年,奥斯卡奖又添笑话一则,主要倒不是因为台上乌龙发错了奖,而是因为十余年前没把最佳影片投给《断背山》的那帮人,今天出于看似相反、实则相同的原因把票投给了《月光男孩》,虽然它难以服众。
一些人批判《爱乐之城》太“白”了,说这又是白人女主角实现梦想,白人男主角拯救爵士乐——鉴于爵士乐与黑人文化的渊源,后者尤其让他们感到不舒服。有人说,这是好莱坞歌舞片的“传统”与“原罪”:种族偏见、粉饰太平,永远以白人明星为焦点。
活跃在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华裔女演员黄柳霜,留下了一句慨叹:“我在舞台上死了一千次”。这绝非虚言。以前(或许现在还是),恐怖片里团队中先死的往往是有色族裔,诸如傅满洲、“龙女”之类的“黄祸”一定活不到最后,而且不准留后,有后代也只能有女儿,女儿见了白人必定扑上去爱得死去活来不求回报,而白人的真爱还得是白人,为了白人男女主角之间的关系牢不可破,这个情敌通常要被设定成未婚妻。
凡此种种“爱与死的律法”,仅仅因为肤色,就判决一个角色人品低劣或者没有独立人格,不被爱,还必须惨死。如此富于攻击性的、精神和肉身的双重剥夺,可以称之为“罪”。可在《爱乐之城》里,我没看到有任何这样的主动攻击。
影片一开始,公路大塞车时路人甲乙丙丁合唱的一曲《又是一个艳阳天》,那个最先打开车门轻声领唱的姑娘、女主角的室友、老派的黑人爵士乐队、给女主角改变命运机会的那位圈内人,都不是白人,也都生活得好好的,甚至与主角一点现实冲突都没有。女主角演独幕剧时,多渴望有人支持啊,可是男主角为了不影响自己工作都狠下心没去,只说以后弥补她,而她的室友们可是去捧场了。
我想反问的是,在一个白人作者整出来的故事里,两个白人成功了,在没有贬损或者抹黑任何其他族裔的前提下,有什么问题吗?如果说,这些指责的声音,要的不仅仅是不攻击,而是心怀愧疚尽力弥补,比如在主要角色里搞配额,何尝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
《爱乐之城》显然不是一部难看的电影,话说得满一些,可以说是行云流水,风流蕴藉。评价低一些,也是俗套大串连,串得好自然。好玩的是,围绕着它产生了很多针尖对麦芒的争论,比如上文提到的,是否白人中心主义的问题。
再比如,片子在情人节上映时,一些人看过说根本不适合情侣看,因为演的是前任千般好;有人说的确不适合情侣看,因为它演的是感情再好也抵不过现实。这两种人里都有代入感强的,前一种人痛心蚊子血怎么给编排成了朱砂痣,而后一种人则痛斥男女主角为了向上爬放弃彼此,是亵渎爱情。
后来有人听了这两种说法,带着对言情片的期待去了,看完后大呼货不对板,这片子和爱情关系不大,占据舞台中心的难道不是“梦想”吗?从这个认识出发,有人对女主角百折不挠终于出人头地感动得稀里哗啦,有人反驳说宣称坚持梦想必成大事是成功学的“毒鸡汤”。
可以留意到,这些争论大多数都是围绕价值观评判展开的。也就是说,足够麻木的现代人,在面对《爱乐之城》时,很容易被激起瞄准某种价值观,批判一番的欲望。更好玩的是,甲说前任才是真爱,乙说这电影完全否定爱情,丙说梦想感人,丁说那不是梦想,是成功学的荼毒——同样在批判,可靶子不尽相同,分歧大到好像看的不是同一部电影。
最明显的例子,是观众如何看待梦幻的最后8分钟。这好像活在欢乐歌舞片里的8分钟,是男主的白日梦,还是女主的白日梦?抑或是音乐和默契造出来的,两个人心意相通的平行空间幻象?到这里,观众被《爱乐之城》映照出来的、自己本身的价值观,与他们理解的影片传递的价值观,两相冲撞之下,可能会让观众在同样的画面里,看到不同的东西。比如,斯拉沃热·齐泽克说,台下的米娅不安而懊悔,笔者是一分都没有看到。可按照笔者理解的影片逻辑,米娅那表情不是淡然里夹杂一丝怅惘吗?这条逐梦之路,她走得坚定而欢快,求仁得仁,既不可能后悔,也不可能不安。
其实,酒吧里这最后一场戏在开篇的合唱里就出现过了。作者的价值观,也没掖着藏着,大大方方地放在每一首歌、每一段舞里。
《又是一个艳阳天》就好比《欲望号街车》里白兰琪问路的那句经典台词。白兰琪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投奔妹妹,出场时她在问路,开口便是,“他们告诉我坐欲望号街车,再换乘公墓号,经过六个街区在天堂区下车”。她说这句台词时,观众并不知道她是走投无路的,而全知全能的作者已经将她来到此地的命运和整个舞台剧的故事核,全写在这句话里。
《爱乐之城》也是如此。虽然记得开场大合唱,唱的是小镇女孩离别男孩,追逐电影梦去了。我还是在第二次看的时候,才领悟到这首歌多么准确地“预演”了《爱乐之城》的故事。
歌中的“我”想起17岁时,在一座小镇的巴士站离别了少年时的恋人,尽管男孩非常可爱,但她还是得去做“她该做的事”,这是因为在夏日的周末,约会时他俩陷在影院的座位里,当所有的光都熄灭了,那个胶片上的多彩世界在召唤她,“到银幕上去,活在每个场景里”。所以,这个身无分文的女孩跳上巴士,来到这里(洛杉矶)。
“我们且看,她是勇敢还是疯狂”,歌中唱到,“因为也许有一天在那个沉寂的小镇上,他坐下来,灯灭后就看到了我的脸,想起他如何与我相识”。这不正是最后一场酒吧重逢吗?所以,在笔者眼中,这只是米娅一个人的白日梦。在这个梦里,男友塞巴斯蒂安在演奏他喜爱的爵士乐,但“翻越崇尚,行近巅峰,追逐每一处闪亮”,成了人生赢家的是米娅,是他追随拍戏的她到了巴黎,在巴黎演奏爵士乐,而不是她追随他和乐队去巡演。
在《又是一个艳阳天》里,尚未成名的女孩,在逐梦路上,激励她的美好希冀是有一天被留在家乡小镇的少时男友在银幕上认出来。以这支歌为映照,与塞巴斯蒂安的重逢,包括两人的微笑对视,就像她和以前羡慕过的女明星们一个范儿去曾经打工的咖啡厅,对她来说其实应该是一种享受,是梦想达成的一部分。
说到这里,再往前推一步就是批判女主角不配言爱了。这就又落入价值观批判了,批判的前提是预设了爱情的神圣不可侵犯。但这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一样的真理吗?至少在作者的价值观里不是这样。即使是那首得了奖的、爱情主题的主题曲《繁星之城》也是如此。它的曲调是那样温柔缱绻,开口第一句却依然是狂热的成功欲望:“繁星满天的城市,你是否只为我一个点亮?”
光,在《爱乐之城》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是银幕上的光,是镁光灯的亮度,是众人艳羡的目光,但从来不是爱情,或者一个不可或缺的他(她)。有人将《繁星之城》里“一个声音说,我在呢,你会好好的”翻译成“一个声音说我会等你,请你放心”,将“我不在乎我会去往何处,因为我需要的就是这疯狂的感觉,这是我内心的声音”中的“感觉”译成“爱意”,“内心的声音”译成“怦怦跳动的心”。
看到这译文,和看到齐泽克说米娅在酒吧里懊悔了一样,让笔者怀疑自己和他们看的不是同一部电影。其实,这首歌和另一首插曲《人群里的某个人》,都好像在写爱情,其实和《又是一个艳阳天》一样,写的是疯狂到不顾一切地追逐成功。
米娅和塞巴斯蒂安,只是向上爬的艰难旅途中结成的亲密战友,战场不重合了,自然就分开了,不需要谁牺牲谁,但是可以在不影响前程的前提下轻扶对方一把(“我在呢,你会好好的”),还能在分开时笑着祝福彼此。
理智上,笔者倾向于最后8分钟是米娅一个人的幻象,除了上文提到的,与开头直抒胸臆的呼应,还有幻想的细节是与她的生活一一对应。但是,对于两人共享的平行时空幻象,也不是不能接受。毕竟,在天文馆里看星星,按理说人是不会飞起来的。“爱乐之城(La La Land)”也许正如这个词在俚语里的意思一样,指向一个自我沉浸的、与现实世界脱节的幻想空间吧。
那些被一部虚构的电影激出来的热泪盈眶、愤愤不平与冷淡讥笑,不也都来自我们自己在心中暗自沉浸的“爱乐之城”吗?那里流淌的音乐是我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