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媒体批评之勃兴及其突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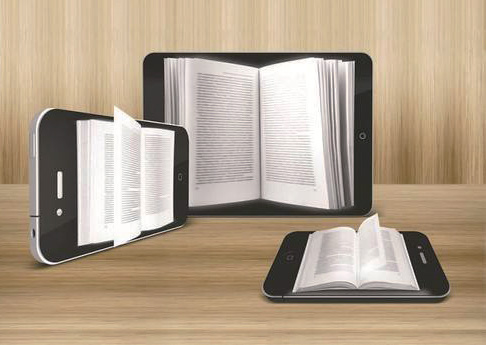
何谓文艺的媒体批评?我将之界定为以面向大众的报刊、互联网、自媒体等为媒介的文艺批评,它是与以学术期刊、专著等为载体的精英批评(或曰学院派批评)相对应的一种批评。广义的媒体包括学术期刊、专著等,因此这里所谓的“媒体”取其狭义,即更加突出文艺批评的大众性、通俗性、时效性的大众媒体。
一
精英批评讲求“常”,多关注经典作家作品,重学理与考据,文风持重,长于学术史的梳理及理论的深入挖掘,引文注释完备翔实;媒体批评讲求“新”,关注新人、新作、新事件、新气象,重论辩与辞章,强调文学批评对于社会现实的能动作用。从作者主体角度看,精英批评以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研究者为主体;媒体批评的主体更为多样,不仅有上述学人,还有大量媒体从业者、自由撰稿人、普通网民等。就读者群体来看,精英批评面向专业学术领域的较高层次研究者;媒体批评主要面向对文艺怀有兴趣并保持密切关注的大众。从篇幅考量,学术批评篇幅更厚重,尤其是在专业权威期刊、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以万字计的大块头文章;媒体批评则长短不一,报刊限于版面要求,讲求短平快,杂志和互联网批评篇幅比报刊更加灵活。
文艺的媒体批评往往在第一时间对文艺事件、文艺现象做出回应,语言简洁有力、直击要害、因受众广泛,也容易迅速获得影响力。中国文艺媒体批评的兴盛始于新式报刊大量涌现的20世纪前后,与晚清以来的社会变革关系密切。这一时期纸媒新闻传播事业不断壮大,媒体批评出于社会改良的需要而彰显其影响力。晚清维新派的办报活动为我国近代社会批评、文艺批评的发展起到了开拓性作用,其贡献之一就是创造了“报章体”这种不同于桐城派古文的通俗文体,影响了其时及后世文风。报章体反映了维新派要求变革的文化抱负以及对西方新思想、新观念、新名词大量涌入中国的回应。既为办报人又为撰稿者的梁启超等开风气之先,为倡导小说界革命写就大量明快畅达且带有一定政论性质的报刊批评文章,如《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小说丛话》等,起到了变革文艺观念、推动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近代化转型的重要作用。五四时期,文艺的媒体批评更加成熟。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在《新青年》等阵地发表了多篇文艺批评,将历史成绩与现实问题、理性思考与感性体悟相结合,对于文艺推陈出新、观念变革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这些文字经过历史洗礼,今日读来仍然富有鲜活的生命力。鲁迅的大量批评文章也多首发于《新青年》《晨报副刊》《莽原》等报刊杂志,短小犀利,具有直面现实的“战斗”精神,同时也不乏精深学问作为根底,对学术传统有总体性把握,对历史典故能够信手拈来,古今贯通、中西互照,传递了比较密集的学术信息量。
二
随着传播介质的变化,当代文艺媒体批评与百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多元的文化表征及丰富的表达策略。纸媒一统天下的时代一去不返,互联网媒体纷纷抢占批评高地,与纸媒分庭抗礼、各领风骚。当下,媒体批评对于精英批评构成了相当程度的挑战。尤以网媒对精英批评构成的“威胁力”为甚。
互联网时代文学网站、博客、微博、微信的普及使得文学批评话语权呈现出分裂割据局面。意见领袖、微博大V、粉丝型读者、雇佣水军等批评主体的复杂多元状态,左右了文学批评的舆论走向。网络批评具有较强的话题性,网民常围绕某一文坛热点问题展开议论争辩。近年活跃于网络的热门批评对象有“80后”现象及代表作家(如韩寒、郭敬明)、重大奖项及获奖作品(如诺贝尔文学奖、雨果奖)、文学评奖制度(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具有争议性的影视作品(如抗日“神剧”、后宫剧)等等。热门话题引发文学批评的话语狂欢,而乐于跟风的普通网民极易不加辨别地偏听一家之言,断章取义,剑走偏锋,水军的参与更容易加剧文艺批评走向偏颇,使文艺现象、作品被过度消费和肆意歪曲。
批评主体的分散性及人员构成的复杂使得批评活动的互动性大大增强,文学批评话语对峙交锋的力度也日趋加大。互联网如同一场不见鲜血却硝烟弥漫的战场。常见的情形是:从历时角度看,后来话语不断替代、压抑甚至否定旧有话语;从共时角度看,面对同一个批评对象,论辩双方针锋相对、各执一词,其各自背后还有无数跟帖力挺的普通网民,如此一来就促使某一具体的文学批评事件上升为具有广泛社会文化意义的网络舆论焦点。我们固然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批评生态,然而不加节制、未经反思的网络批评却容易成为脱缰之马,成为话语暴力、民粹思潮之渊薮,造成文艺批评之乱象。这一现象不仅之于文学批评需要纠正,之于文化批评、社会批评等任意一种批评形态而言都值得深刻反思。我们必须站在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立场上对于网络批评加以引导和规制。
在互联网媒体大行其道的当下,在文艺作品呈井喷态势涌现的今天,互联网批评必须强调态度立场,把握尺度方向,力求与文艺创作的蓬勃发展势头相适应并保持良性互动。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空间,用户处于一定程度的隐匿状态,但批评不应是虚无、虚伪、虚假的文辞,互联网不是批评者随意宣泄非理性情绪、释放不负责任观点的场域。批评者必须避免空洞无物、立场游移、语焉不详的模糊批评,避免缺乏凭据、暴戾粗鲁、伤害人格的意气批评,避免乱戴高帽、夸大成绩、回避问题的恭维批评。网络批评要谨守批评伦理,将中肯的评判与同情的理解相结合,减少人际关系、商业利益等非文艺内在因素的干扰,力求使批评话语更具理性和智性,不辜负创作者与受众的期待,更经得起现实与历史的考验。否定性的批评必须以不恶意伤害批评对象的尊严为前提,赞扬性的批评也必须建立在力避空脱溢美之辞的基础之上。棒杀或捧杀,均违背对批评主体话语的伦理要求,既直接或间接地伤害了批评对象,也对互联网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三
文艺的精英批评与媒体批评有所区别,但并非泾渭分明。精英批评固然长于文献搜集、逻辑架构、学理阐发,但也不应失去对社会现实的敏感和关切;媒体批评在关注当下、贴近前沿的同时,也不应放弃承担学术积累与文化传承的使命。
精英批评与媒体批评皆应掌控好当下性与历史性的平衡问题。有的批评家执著于“跟进式”“追踪式”“零距离”批评,批评家关注时新话题无可厚非,但是若仅仅拘泥于捕捉层出不穷的信息碎片则不可取。必须强调,文学的“当代”批评不等同于“当下性”批评,当代批评恰恰要对“当下”保持一定警惕与反思,须破除急功近利思想,走出浅表化、媚俗化批评的陷阱。当代文学批评要在迫近感与疏离感、在场感与历史感之间寻求合理支点,使批评话语既不忽视现实关切,又具有一定的历史深度和思想厚度。
想要加强文艺批评的阵地建设和队伍建设,我们就不能排斥任意一种积极健康的文艺批评媒介及批评主体。批评者既可以用精英批评的方式对积累已久的史料与史识条分缕析、严谨铺排,也可以用媒体批评的笔法捕捉思想火花、直击问题要害。两种方式宜在保持个性的同时相互取法,相得益彰,共同肯定成绩、查找问题,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与评论事业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