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世知己——陈歆耕《剑魂箫韵:龚自珍传》读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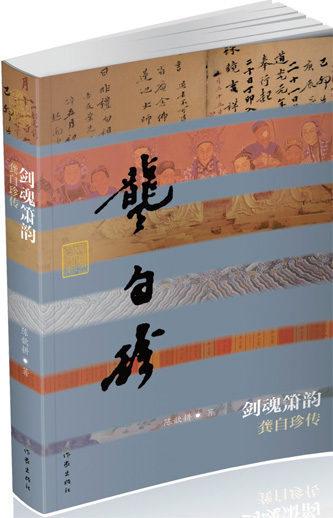
从拿到此作到一气读完,花了三四天时间。一本好的传记,能令读者通晓传主生平,再能从中觅得三五真言,想必是大多数读者读人物传记的目的之一。此传却使我在读之初就“有话要说”,越往后读,这种感觉越强烈。
读上部“巨匠”篇,感觉作者为“传主”精雕细镂了一张宝座,字字珠玑,行行真情。
开篇的大气以及对晚清社会背景的分析,虽精简省略,却入木三分。社会各阶层从官场到市井,若长卷徐徐展开,令读者对传主所处的时代有深切的了解,对其后的表现有心理准备,也是作者用情至深之处。深感时代的不幸,龚自珍那样的“奇珍异卉”在那样的时代里注定会失败,会碰壁,会受伤。
开篇的高度与恢弘,使得该传若朝霞灿烂,又似繁花千转。龚自珍唱尽了人生悲歌,又包含诸多无奈。可贵的是,作者并未对那时的社会背景作“血泪控诉”,而是冷静地叙述、客观地分析,不掺杂个人感情色彩。
著中“裂变”提到龚自珍的诗文对后世人的影响深远,甚至影响到中国近代文坛和政坛,可见作者在史料上下足了功夫。这恐怕是绝大多数人忽略了的,是作者为龚自珍理出这条“文脉渊源”,也为今人或后人们拨开迷雾。我们对龚自珍的影响力严重低估,更对龚自珍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的“无知”感到深深的歉意。
是将传主写成“雕版年画”中的模样,还是描绘成“狂士文生”,全在作者的能力和见识、良知和高度。在这一点上,龚自珍无疑是有福的,作者像一位雕刻大师,一点点搜集史料,一笔笔还原出他原来的样子。读者也是有福的,对于相隔百年的古人,我们不就是想要看到一个真实或相对真实的龚自珍吗。能做到这一点,再多的荣誉和再高超的写法,都不如此珍贵。
作者对龚自珍的生平冷静、客观、公正、不乏柔情与小幽默,说“龚自珍想挤独木桥,其结果用脚趾头也可以想象出来”。读者们知道,这不是作者在拿那时那刻的龚自珍“开涮”,而是对龚自珍深切同情,又含有几多叹息。
传中对龚自珍友人的描述,犹如垒珠缀玉,环佩有声。虽近白描手法讲述人物,却感觉那些人竟从纸上活了过来,好似亲眼看到的一样。如短命的塾师宋璠的一生让人看到了晚清民间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令人惋惜不止。对狂士“王昙”的描写更是令读者兴趣盎然,那黄沙漫天中,举臂拍门的落魄之人,竟然能得到龚自珍的善待,从另一个角度刻画了传主的性格和人格。
书中还写到龚自珍与魏源在扬州的交往,是本章重点,更令人倾慕。这两位大家竟然相处于同一片蓝天下,寝则同床,衣则同袍。结交扬州文士,遍访巷陌茶馆、名园歌姬……他们都心怀天下,挚爱苍生。相处期间彼此谈过什么,说过什么,议论过什么?魏源所著《海国图志》在龚自珍离世后,不知这想法有没有受到过龚自珍的赞许和建议?这一切,都随着当日云彩成了过去,今人不得而知。
作者并未用今人写法“写”当年的龚自珍,也没有用今人看法“看”当年的龚自珍,更没有用今天的“十进制”的衡器去“称”当年的十六进制时代的龚自珍!将龚自珍放在那一段时间背景下,如老放映机般转动,播放昔日胶卷呈现的历史片段。这样真诚的写法、虔敬的态度,非专业素养高深及写作态度诚恳之人所能达到。
大多作者在写人物传记时,喜欢将自己摆在全知全能全的位置,就像高高坐在传主面前的判官。可本传作者却不是,在写到古玩、诗词等章节时,作者多次用“不专业”“不太懂”“不精通”来形容自己。这样写不是作者在“示弱”,而是“示强”,因为传主足够强,作者自叹不如。这样反而给读者留有“气口”和延伸。作者不是“圣手”,也做不到“一手包办”,诸君还是去拜读、了解传主本人的著述吧。能做到如此,可见作者的大爱、大气、大义、大情怀。这恐怕是本传赠给读者的另一种惊喜,能看到作者高尚的人格和品行。
令人扼腕的是,龚自珍的生命凋零于夕阳壮美之时,幸无黑夜与生命只剩灰烬的落寞。作者的文笔也同龚自珍的生之活力一道戛然而止,但凭绕梁的生命之歌留在读者们的耳际。作者绝不赘言,也不肯多说,是想让读者在龚自珍的生命之河的两岸徘徊、叹息。追寻他远去的脚步,俯身闻一闻被先生扶植过的花草,看一看因先生离去而泣血的斜阳……
世间不止病了很久的梅花,以及像从天宫中倾倒而下的胭脂般的落花,连每一片云彩、每一个文字,都被龚自珍深深地爱过。他爱他的国家、他的人民、他的天空与大地。
可是,他走了。他的一生若一曲歌罢,散则散矣,恕不送客,留予后人唏嘘。
更为令人慨叹的是,大多传记作者会选择性地描写传主,更有加分、洗白之嫌,而作者对龚自珍的怪癖、毛病等不粉饰、不掩藏,力争让读者们全方位了解人物,感触到接近真实的龚自珍。如此不偏私、不盲信,是读者之幸,更是“非虚构”文体之幸。就像作者所说,历史的修饰与颠覆,无论是百年还是千年,总归要有面对真实的一天。这种率真、自信的写作态度,应为更多作者借鉴、学习。
当读到作者清明寻访传主墓地而不得,泪湿眼底……令人动容。我想告诉作者,龚自珍来自天上,若星辰璀璨。星星是不需要墓地与凭吊的。因为他们的人间之旅,是为了供世人仰望。正如作者所说,那些诗词、文章才是先生留给后世的金玉良言,才是他人生真正的丰碑。
龚自珍爱梅,爱到成“痴”。读书中文字如同看到作者和传主对坐于病梅馆中,那梅花正开。可寒气袭人,蜂蝶难来,春讯也不至。文人爱梅,爱它守得住岁月的寂寞,敬它苦寒的身世。北风再猛,雪花再飞,也阻止不了它们对着蓝天开成一张张笑脸。梅花的香气释放得那么彻底,爱这凡尘爱得那么纯粹!它们平日只长在墙角衰草间,却用生命蓄积四个季节的能量,为了能在寒冬绽放,勃发一次次幽香,斗这寒彻的人间世!
龚自珍爱梅,将梅花当作了知己,也当成了他自己。在那个千万般不得已的世界里,他病了,却要像病梅一样熬过花开的春季,炎热的骄阳和丰硕的秋天,因为它和他都在希冀能在冬日里芬芳。因为冬天和飞雪,大多事物都已沉睡而去,谁也不会和他们争抢。他和它要用笑意斗雪,用沁香散发在寒风中,让世人觉得,原来这寒冬中也有从天庭下降于不凡之物。这世界原来是美的,是值得留恋的。
这位民族守夜人,就这样走了,像一棵长期生病的梅花,终于倒在了暗夜里。他像星辰俯瞰着大地,深爱着人世,自己却只能苦沐于宇宙中挥之不去的寒冷里。
他害怕又爱慕的箫声,伴着梅花开放,当是最好的搭档。将声音和花香送进千家万户,送到读者的案头,心上。
因为作者的职业及文学素养,陈歆耕做到了不虚伪、不造作、不全知全觉、不指点江山、不自满、不自欺,谦虚务实。就像带着读者进入幽森花木之境,全景展现传主及他那个时代的背景,当属难得的诚意之作。
能做到对传主的感同身受,已属恰当,而能为传主锦上添花的作者更是难得,本传作者当属两者兼具。
作者希望读者“读不读龚自珍传不重要,一定要读一读他的作品集”,这是对传主的敬爱,也是对读者们的殷切良言。同时,相信作者的文字也会因为这本传记长久地进入阅读者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