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两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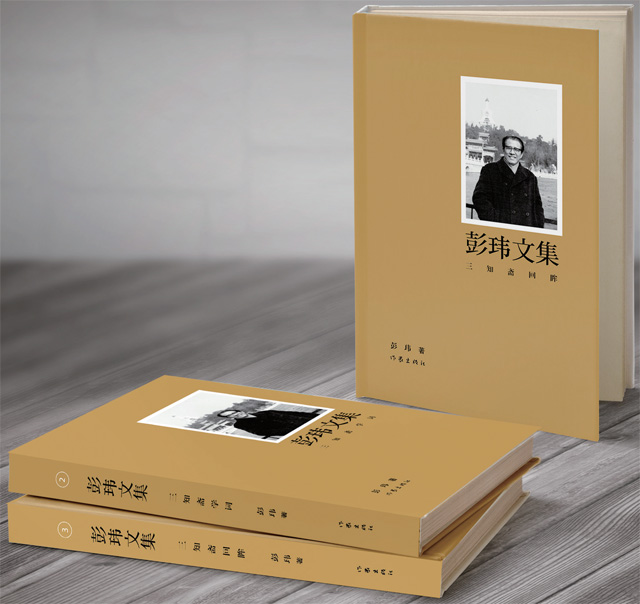
家在禹山脚下、茱萸河畔
我的家乡,是地处河南省西南边陲的邓州市彭桥镇龙潭河村。
那里,远离城市,土地脊薄,但却是一个有山有水、风光宜人的地方。
巍峨雄浑的伏牛山,绵延在我省的西部。它北与崤山、熊耳山相连,逶迤向东南方向发展,经卢氏、栾川、南召、镇平、内乡、西如峡、淅川等县,起伏回旋八百余里。在与邓州相临的境内,还有海拔千米以上的崇山峻岭,但到了邓州市的西南部、我的家乡一带,却已似“强弩之末”,只抛出了几个海拔二三百米相连的小山头——杏山、汤山、禹山。再向南去,就是一些遍布奇形怪状巨石的山峦和一道道遍是沙礓石的丘陵了。这里是伏牛山的末端。
茱萸河(亦名排子河),发源于汤山深处。据说汤山之名的由来,就是因为山内多泉,且不少是热度如汤的温泉。茱萸河从汤山出来,一路汇聚了无数泉眼流出的泉水和从山峦丘陵上排下来的雨水,形成了一条平时明澈、深邃,汛期波涛汹涌澎湃的河流,向东南方向流去,直到湖北襄樊注入汉水。
在北距禹山七八里的地方,茱萸河向东环绕了一个半圆,形成了一个马蹄状的大河湾。龙潭河村就在这个背靠山冈、面临茱萸河的大河湾里。大河湾的沿岸遍植柳树、杏树、桃树,还有一些柿树。河湾的中部是一个占地约30余亩的大竹园,万竿翠竹,郁郁葱葱。竹园后边,就是彭家地主的房舍了。
这是六座一排向东、规格相同,三进院子的百年老宅。一个宅院约有房屋30间,是彭家在长期剥削农民的基础上建造起来的。这些宅院,当年大概是堂而皇之的,经历了百年的风雨沧桑,那些房舍早已是一派破败的气象。院内道路凹凸不平,门窗油漆剥落。有的宅院甚至出现了残垣断壁。最早,我的曾祖父兄弟三人,祖父辈兄弟七人,对于这样的人口来说,这些房舍大概是十分宽绰的。但到了父辈20人,我这一辈五六十人,这些房舍就显得十分狭小了。每个宅院都分成了两家、三家、甚至四五家,他们各立门户,各起锅灶,把那些原本宽敞的院子分割得七零八落,支离破碎。
我从少年到青年,在这样的宅院里度过了10年。房屋宽敞与否、破旧与否,我都没有心思考虑过,只喜欢我家的后院有一棵桂花树,顶着圆圆的冠盖,亭亭玉立,年年开花;中院有核桃树粗壮高大、荫及满院,年年结果。它们带给我无限的温馨和欢乐。
龙潭河整个村庄,前后绿树成林,浓荫婆娑,是各种鸟类的乐园。每当黎明鸟儿醒来或黄昏时分群鸟归巢,就从竹园和树林中响起了百鸟齐鸣、嘈杂而和谐的乐曲,悦耳动听;在合奏中充当低音及和声角色的,是栖息在村后一排高大楸树上的白鹭,它们伸着长颈,“咯噜、咯噜”地叫着,深沉而悠长。
龙潭河向南走二三里,就是彭桥古镇。解放前是国民党的区政府、解放后是人民区、乡政府所在地。镇上原有一个方圆数里夯土建成的寨墙,四方有四个寨门。镇内有东西向和南北向两个街道,但并不繁华。有几个中药、杂货、铁器、酒、饭、茶一类的店铺。平时到镇上的人比较少,只有“逢双”赶集的日子,四乡的农民带着自己剩余的产品,到镇上进行交易,才显出熙熙攘攘的集市气氛。但这里很早就是陕西经商南县,进入河南西峡、淅川、邓县,再进入湖北老河口或襄樊、武汉的必经之路。我小时候还经常看到一些成群结队的挑夫和手推车,运送大漆、桐油、核桃、柿饼等山货进入彭桥镇。这是彭桥镇有着久远历史的原因。
我热爱我的家乡。家乡的山、水和土地哺育了我,陶冶了我。古镇、陵园、村庄,横亘于村北的山,从家门前流过的河,在我的记忆里,都是那么完美、那么和谐。
家乡,一年四季都有巨大的魅力。
春天,当禹山的积雪慢慢融化,露出一片淡淡葱绿的时候,茱萸河边的草也发了芽,柳树舞动着嫩绿的枝条开始吐絮。接着,杏花、桃花、梨花、相继开放。竹园里,也从地下冒出尖尖的新笋来,人们稍不注意,它们就蹿也似的往上长,很快脱掉身上的箨叶,展示出墨绿色的躯干,嫩得像要滴出水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春耕开始了。丁丁当当的牛铃声,在四野震响起来,人们开始了一年辛勤的劳动。
夏天,麦子熟了,遍地金黄。人们挥汗如雨,既抢收又抢种,碾场打麦,种晚秋作物,锄早秋作物,忙极了。中午,太阳像火一样,当大人们在树荫下休息的时候,村北茱萸河的龙潭里,却成了孩子们戏水、纳凉的好去处。一群光屁股小孩说说笑笑、吵吵闹闹,从高高的河岸上,一个“冰棍”跳进了潭窝里。浮出水面以后,再一阵“狗刨”朝远处游去。游累了就躺在岸上晒太阳,把皮肤晒得黑明发亮。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对孩子们来说,也是充满诱惑的季节,树上的枣子红了,柿子黄了,核桃也熟了,引得他们垂涎欲滴。等到初霜以后,柿树的叶子红了,禹山上的枫叶也红了,遍地的高粱也顶着红红的穗子,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大自然成了一幅斑驳多彩的图画。
入冬以后,场光地净,进入了冬闲。有人在村南茱萸河较窄的河段上,筑起了一条土坝,把河水聚起来,再从坝上一个窄窄的口子里流出去,转动水车,带动轧花机,帮助乡亲们把籽棉轧成皮棉。这时的茱萸河变成一个长长的、深邃的、绿色的湖泊,美丽极了。不知道哪一天,北风呼啸中的大雪,一夜给山岗、大地披上了银装,天地变得更加苍茫、寥阔。柏树群像披上了铠甲的武士,巍然挺立在茫茫雪野中。丛丛绿竹勇敢地抖落压弯了身子的雪,在风中萧萧吟唱。寒冷把人们赶进了屋内,手里捧起火罐取暖,火罐里散发出柏果燃烧的淡淡的幽香。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家乡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发展了,文明进步了,人们的生活比过去大大富裕起来。但由于发展集镇、大炼钢铁、建造水库的需要,家乡的山水地貌已经不是过去的样子了。原来的宅院、陵园都已不复存在。但家乡在我的心中,那种感性的、最原初接触所留下的记忆,依然十分美好,并引起我无限眷恋的情愫。
婉约、豪放与刚柔相济
把词分为婉约、豪放两体,始于明人张綎。他在《诗余图谱·凡例》中说:“词体大约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以婉约为正。”东坡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从此,以婉约、豪放两体评论词作、词人,撰写词论、词史,就成了一种传统,其影响直到今天。
一、如何看待对词体的如此二分
有的学者是赞成的。他们认为,如此二分,便于从总体上把握两种体式、风格的大致分野,比较两种词体的特点和各自的优长,便于从纵向寻找词体发展的脉络及其流变。因此,张綎所肇之端,有着历史的和现实的合理性。
但大多数学者不赞成对词的如此二分。他们认为,从晚唐五代经北宋、南宋到张綎生活的明代,已是上千年了。其间词人辈出,词的风格也是异彩纷呈。用婉约、豪放两端来划分众多词人风格的归属,并进而论其价值的高低,似有简单武断、削足适履、背离实际之弊。
况且,公认为豪放词体的代表人物,也不乏婉约之作。如苏轼悼亡之《江城子·记梦》《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辛弃疾的《祝英台近·晚春》《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等,都可以并列于婉约体的代表作,而毫不逊色。公认为婉约词体的代表人物,也不乏近于豪放之作。如李清照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等。
笔者认为,既然有此流传已久的二分之说,就把它当作一家之言,供后人阅读历代词作、或创作新词的参考。在研究和评论当代词人词作的时候,要从实际出发,不宜用二分法简单地比、套了事。词是作者心灵意绪外化的产物。对一个作者的词作,要分析其中的各种意象,揭示它们背后的思绪和寓意,以形象化的要求,考察其语言的特点,以及作品在气、韵方面的状况。在分析多篇作品的基础上,再概括出作品的体式。
二、如何看待其“崇正抑变”的观点
张綎“崇正抑变”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
“正”和“变”,是古人对文学的发展变化、风格或流派的出现,作出的总体性评判。“正”是正宗,“变”是变体、别体。从词的发展来说,从晚唐到北宋初期,一直是婉约词的天下。其风格表现为一种委婉缠绵、含蓄蕴藉、细致入微的阴柔之美。其内容多是男欢女爱、离愁别绪、宴会游乐等,同“言志”的诗相比较,人们称作“诗庄词媚”。这是词的本来面目,是词之“正”。到了苏轼,婉约词的一统天下突然被打破了。苏轼“以诗为词”,摆脱了“词为艳科”的束缚,诸如言志抒怀、吊古伤今、身世感慨、社会风貌、山川景物等,凡诗之可言者,词亦可言,甚至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极大地扩展了词的题材。在风格上则是激情澎湃、逸怀豪气,表现出“海潮东来,气吞江湖”“千里万里,山奔雷驱”(郭麟语)那样一股纵横跌宕、不尽豪放的气势,呈现出一种阳刚之美。到了南宋的辛弃疾,终于使豪放词与婉约词形成了双峰相峙、双分天下的局面。相对于“正”来说,豪放词是“变”。
词之从“正”到“变”,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那么“正”和“变”孰优孰劣,何为本色?虽然有许多词论家拥护张綎的观点,但在明代,就有异于张綎的通达之论。如俞彦,就对苏词作了高度的赞扬。他说:“子瞻词无一语着人间烟火,此自太罗天上一种,不必与少游、易安辈较量体裁也。”东坡词是由“万顷波涛,来自万里,吞天浴日”这样一种涵容天地的胸襟,以及超迈的人格所决定的。对当时不被看好的辛、刘(克庄)的豪放词,他也深表钦佩,加以维护。还有一位词论家孟称舜,基于词的抒情特征,对豪放、婉约二体不强分优劣。他说:“盖词与诗曲,体格虽异,而本于作者之情。”“作者极情尽态,而听者洞心耸耳,如是者皆为当行,皆为本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苏辛词的评价,也是持平之见。其《苏东坡词提要》说:“词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约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为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今日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对辛弃疾词评论道:“弃疾之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翠刻红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
笔者认为,婉约也好,豪放也好,发展到今天,都脱离了对音乐的依赖性,而成为一种书面的文学文本,两种体式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不应强分优劣,应当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填词最要紧的是,要有真言语真性情。不论何种体式,只要有真情、能感人,都是本色。
三、应当提倡刚柔相济的词风
上面提到的孟称舜还说:婉约与豪放“两家各有其美,亦各有其病”。他说的“病”是:或失之于“俗而腻”,或失之于“莽而俚”。两家确都有一些作者的作品,或婉媚无骨、阴气太重;或粗犷无韵、阳气太盛。最理想的状况,是把两者糅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
刚柔相济的思想,在《易传》中就有论述。《系辞》说:“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意思是说,刚和柔不是绝然分开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在中国古典美学中,也贯穿着这样的思想。如画论之“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婉媚之内”;书论之“要兼备阴阳之气”;词论之“壮语要有韵,秀语要有骨”,等等。
清代文论家姚鼐在论及文章之道时说:“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暗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十分强调刚柔相济才是为文之道。
词论家指出,在宋代,有许多著名词人在创作中都注意到了刚柔相济的问题。像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岳飞的《小重山》、辛弃疾的《摸鱼儿》以及贺铸的一些篇章,都是兼具阳刚壮美和阴柔优美的作品。这样的风格,值得我们学习。
《彭玮文集》文集共分三卷,分别为《三知斋吟稿》《三知斋学词》《三知斋回眸》。“三知斋”为彭玮先生的书斋名,所谓“三知”,乃“知不足、知艰难、知是非”之意,作者长期以此三端自勉。其中第一卷《三知斋吟稿》甄选了作者半个世纪以来的诗词作品二百余首,时而激昂,时而婉约,寄寓深情,描摹时代,佳句迭出,精彩纷呈。第二卷《三知斋学词》收录了作者关于诗词学习与创作的心得和评论文章,书中对柳永、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中国古代经典词人词作都有透辟论述,充分显示出作者的深厚学养。第三卷《三知斋回眸》是作者的回忆录,记述了一个出身于旧知识分子家庭的老共产党员坎坷曲折、追求进步、坚持真理、辛勤奉献的人生经历,尽显一位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的家国情怀、精神操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