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散文:不断与传统观念抗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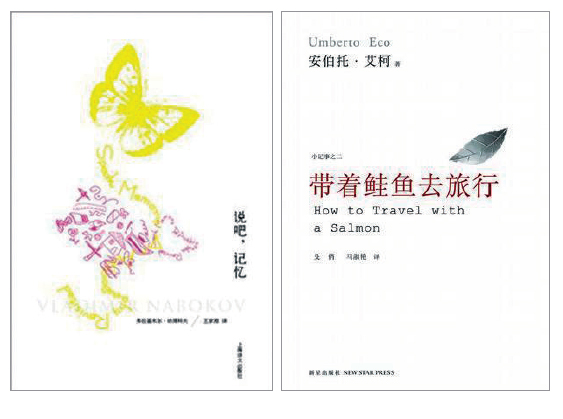
学界普遍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泛文化现象,是一种后现代氛围,几乎触及到文学、艺术等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耳熟能详的有德里达、福柯等人的理论;罗兰·巴特、苏珊·桑塔格等人的批评;金斯堡、普拉斯等人的诗歌,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人的小说;贝克特、尤奈斯库等人的戏剧。后现代主义与传统的所谓流派不同,它更多地集中呈现的是一种思维的独特性。生存于这股“后”浪潮之中的散文创作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
世界散文,自蒙田、培根以降,经由帕斯卡尔、卢梭、卡夫卡、劳伦斯、纪德、帕斯、博尔赫斯、罗兰·巴特,虽然题材范围有所不同,叙述方式也有诸多变化,但是作为一种言说方式的体裁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不仅如此,笔者认为在世界散文创作的庞大作家队伍当中,还涌现出了像罗兰·巴特、博尔赫斯、艾柯等这样的大师级人物。
作为一种观察和认识世界的观念,后现代主义意在打破“一体化的世界”这一神话,以一个多元世界取而代之。后现代主义散文则具体表现为意义中心的消解,且代之以碎片化。没有中心,或者说去中心,是解构或消解的根本策略。因为追求“无中心”,所以传统观念中的标题与正文的呼应也在本雅明的《单行道》中屡屡被打破。在中心消解的同时,过去被传统观念所持守的情感元素也同时淡出,理性思维占据主导。《恋人絮语》里并非传统的“叙述恋情”,而是对“恋人”之间可能出现的种种细节的理性梳理,关注细节、关注细节的“形式”,成为作品的主要内容。
后现代主义精神内核的最终指向艺术的创新,这一特征在后现代主义散文里的呈现极为突出。比如艾柯的《误读》《带着鲑鱼去旅行》在文章的运思、布局安排方面集中体现了作者对于旧有思维的强势突围,给读者带来的阅读刺激绝不亚于观看好莱坞大片,在结构形式上彻底颠覆了传统。《很遗憾,退还你的……(审稿报告)》在文章构思上极具创新意识,对多部世界名著名典,以审稿报告的形式加以肯定或否定,滑稽、谐谑,对这些名著名典的分析,貌似漫不经心,实则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给儿子的信》用信的形式,游刃有余地批判社会的丑恶,具有辛辣的讽刺意味。文章里时而正说,时而反语,表明现实社会充斥着战争的阴霾,枪支等武器泛滥,连儿童玩具都不得幸免。《发现美洲》又以剧本的形式布局谋篇。艾柯对于书信、审稿报告、剧本等一切文章形式几乎都做了尝试。作者简直就像一位神秘的魔术大师,完全出乎观者的预期,不停地变换出无尽的文章形式。
从叙述话语或风格的角度看,后现代主义散文的突出特征是叙述过程的发散性与跳跃性;对历史的表现也成为某种“再现”甚至“戏拟”。就“发散性”而言,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中叙述他对蝴蝶的热爱,有这样一段描绘:“一只具有斯堪的纳维亚女神这样名字的微黑的小豹纹蝶低低的掠过长有朦胧的幽蓝色果实的沼地越橘丛、掠过棕色的死水圈、掠过苔藓和泥潭,掠过芬芳的沼地兰花(俄国诗人笔下的夜的紫罗兰)的穗状花序。漂亮的Cordigera,一种宝石般的飞蛾,嗡嗡地飞遍它用做食物的湿地植物。我追逐有玫瑰红边缘的粉蝶,灰色大理石花纹的眼蝶。”完全没有传统语言的架构,只有“掠过”、“掠过”,这样的描写动感十足,就像电影画面一般,在读者面前一一呈现。依然是纳博科夫:“然而雪是真实的,当我弯身捧起一把雪的时候,六十年的岁月在我的手指间碎成了闪光的霜尘。”完全就是用文字构筑的电影画面。关于对历史的某种“再现”,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中第九节“瓜那巴拉湾”的一段描述,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特点。这一节开头从第89页至第94页,都在叙述一个378年前的故事,这种叙述故事的思路,直到94页故事叙述完成,才在起承转合之中顺带做出交代,这段内容铸就了这篇作品的一种特殊叙述方式,在同一篇文章里采用了不同的叙述方式。值得一提的是,就这一节的内容而言,不仅是穿越古今、而且还穿越欧洲与美洲、穿越旅行与哲学,文字所呈现的画面更是在动感与静谧之中穿行,完成了对传统文章形式的彻底超越与颠覆。另外,让·波德里亚的《冷记忆》则充满极强的跳跃性,常人大多无法理解。
后现代主义理论已在西方盛行了半个多世纪,中国大陆虽然与西方社会存在诸多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但是其中的影响就像流动的空气一样无法回避。而且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双向的。艾柯不仅了解李白、杜甫,他还了解鲁迅甚至知晓毛主席语录。艾柯不断翻新的文章架构,在鲁迅的《野草》那里似曾相识;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先解构审视对象,之后再从批评的角度写表扬,表面批评实际表扬,与朱自清《背影》等传统思维的直接阐释完全两样。钱锺书的《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在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中也有重现。仅就“西风东进”而言,中国福建的南帆则以《守护还是复制》《叩访感觉》《舌尖上的安慰》等作品,向罗兰·巴特遥相致意。《舌尖上的安慰》中,南帆梳理了有关“吃”的一切:当然不是单纯的食物,而是分析其背后可能想到的一切机制:人的躯体感觉(“饿与馋”、“嘴的三种功能”)、社会化的表现形态(“饭局”、“小吃零食”)、文化视域下的分类(“麦当劳”、“故乡的食物”)等,一篇文章分为若干零碎片段,作者把所能想到的带有社会文化思考的碎片囊括在“吃”的话题下,阐述带给人身体与心理安慰的美食,其背后的文化编码是社交场合、文化侵略下的经济远征以及带有人格象征的心理羁绊。除了南帆之外,值得关注的还有钟鸣,字典式的文章结构以及跳跃性极强的语言,都将读者引向了后现代主义散文的殿堂,《畜界·人界》《涂鸦手记》等虽有讲故事的痕迹,但其思维的跳跃性、信息容量的广博性、思想的深刻性,都令读者刮目相看;其随笔的信息容量,还颇有梁实秋的遗风。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台湾英年早逝的作家林耀德,在他临谢世前两年分别发表的《铜梦》《尸体》是完全成熟的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散文作品,《尸体》记叙了在祖母的灵柩旁的冥思,与其他有关尸体和死亡的陈述被放置在同一个平台上,剪裁、拼接在一起,是情感的零度介入,更是情感的破碎形态。林耀德的笔触充斥着反讽、佯谬、诡异和悖论,有学者称林耀德是使中国当代散文创作与后现代主义接轨的第一人。
阅读后现代主义散文,要不断与传统观念抗衡,传统观念不断站出来“嘲笑”“后” ,而“后”又在执拗地、理直气壮地“炮轰”传统。传统散文呈现的是感觉,后现代散文呈现的则是以错觉写感觉,是正视错觉!后现代直接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法,与开放、包容、多元、求新紧密相连;让人们逐渐远离单弦思维、固定模式,以一种更加富有创新性的朝气去面对各种全新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