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与展望——第二届两岸文学评论工作会议台湾学者发言摘编

第二届两岸文学评论工作会议2016年12月17日在厦门召开,会议围绕期刊《桥》创刊5期以来刊载文章的整体回顾与价值评估、两岸青年创作现状的整体观照与前景展望、两岸文学评论工作的深入与拓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现将部分两岸学者的发言摘编如下:

对两岸青年在文学创作上的一点建议
□张万康
中国台湾青年的毛病大致是这样:文字上是一种文青体,与世俗百姓的隔阂感太大,过于雕琢文字,显得小家子气。内容上则是不知所云,无病呻吟。尽管青年们除了接触文艺,亦想展示年轻人的活泼俏皮,或说展示自己高来低去、涉猎多元的能力,但多半流于卖弄,轻佻猥琐;自认思想新颖前进,但要命的是基调仍是“文青体”。所谓文青体,其文体气质看似深沉、内敛、忧郁、节制,却不免是兜圈圈又装可怜,弄巧过多,假假的,惺惺作态。老是努力提醒读者他懂得蛮多的、很有思想,可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思想家的哲学质量,于是就只剩下阴暗的幼稚了。有的人写久了颇有文笔,看似简练、简洁,甚至可说老练,但其实是硬砌的,不成熟。而且越年轻越想写出金句,想装大人。说到弄巧,有的青年在笔头上想做出“大巧若拙”的效果,这照理来说很容易看穿、看透,但风气所及许多人就是看不透,且模仿起这种路子,好像这样才叫写作,太怕别人认为他不懂写作。这就好比台湾的书封设计,流行留白、简约、清简、朴雅、玩弄字体的风格,非常浅表,但假装这是艺术品味上的功底。
整个脉络上来看,青年学的是前辈,有样学样。40岁以上的作家也有这种毛病,有的人很卖弄,有的只是诚恳、认真与讲究(或可能仍是卖弄;不自觉的),总之十分在乎文学形式、写法的求新。在我来看,新不见得鲜,所谓“新鲜”,关键是在鲜。清新不是太难,抓个模式去套即可,难的是新鲜、清鲜。且又,光有这个清、图的是个清,泰半空洞,想清高却成清而不高,想清醒又成清而不醒,套句歌名“明明白白我的心”,要做个明白人才能写出好东西。好的作品是晶莹剔透、自然而然充满灵妙,释出神韵,故此让人眼睛一亮、精神一振,心想文学原来可以这样写、事情竟然可以这样看……诚然,能做到这一层次的作者毕竟是极少数。我的意思是说,四五十岁的作家们的作品大多也是值得商榷的,可是40岁以下的作者、文青们却又承袭或吸收于他们,于是搞得更是不伦不类。也可以说,四五十岁,甚至60岁以下的作家所隐藏的问题,在其之后的世代身上整个显影,龟裂。
我发现中国台湾文青体的那种文字、气息,在中国大陆的文青所写的东西上头也看到了。至少一部分大陆文青是这样。基本上一个人在当作家以前,都是先当文青。所以我觉得观念的打底是要紧的,你长歪了,以后很难矫正。文青体是一种“人不说人话”的文体。它是硬充学术腔、精英品味的文体。我常鼓励台湾文青和青年作者在创作时能有一个想法或说态度或心境:“我要写出的是我父母能看得懂的文章”。除非父母是文盲,但文盲也可以听声音,重点是在于一种沟通的能力与胸怀。这并非刻意为之。存心要写得多浅显、直白,那也极可能是种浅陋与作态;或是成了一种“乡民体”,这种质感也是不行的。在中国台湾,中文能力比较差又爱上网爬文(读文章、找文章资讯)的年轻人,他们写与读的是一种乡民体,通常它不光是流俗的问题,而是没脑但装得很有看法或高见,搞笑能力也不灵但自认很好笑。让父母也读得懂,我觉这不是啥了不起的口号,而是对中文有一定的认识,自然而然就会这么做。中文是一种大俗大雅的东西,基本上它还偏俗。若它雅了起来,注意,也通常是短句。中文文法的特性很难拖出一个老长的句子。有的名作家擅长稠密的长句,但也不能泛滥,否则我个人来看就有点可怕了。它可以是技巧,即文笔中的一种适时的技巧或实验,但不宜成为一种路数。
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在台湾地区的发展
□洪士惠
受限于两岸的空间文化距离,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在中国台湾的发展情况,除了莫言、苏童、余华、王安忆等已被普遍知晓的资深作家外,其他的中生代或新生代作家,似乎未受到太多关注,主要原因除了是多元化社会“稀释”文学的影响力、中国台湾政治的本土化影响外,两岸作家趋近相似的现代议题,似乎已无法吸引台湾出版市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青睐。尤其过去如文化大革命般的政治题材已是“老哏”,虽然在资深作家的笔下,仍因题材的特殊性,具有一定的讨论度,但气势已不若往常;中生代或新生代的作家作品,也因缺少热门议题的讨论度,而显现疲弱不振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藉由影视传播的力量拉抬声势的情况愈趋显著。通俗文学如郭敬明小说改编的电影《小时代》,或是顾漫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何以笙箫默》《微微一笑很倾城》等,皆是藉由影视传播后,中国台湾观众才知晓作者身份与背景。纯文学的作品,如前几年获得台湾金马奖关注的毕飞宇小说改编电影《推拿》,以及今年甫获奖的刘震云小说改编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等,也是在受到媒体关注后,小说家与原著作品方才被读者看见。这种跨文化力量的影响,成为中国台湾引介中国大陆当代小说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势之所趋。撇开通俗文学的情爱主题不论,在纯文学范畴中,从《推拿》盲人主题与《我不是潘金莲》上访主题,题材的特殊性在电影或出版市场上,成为重要的“利器”。说到底,这两部作品皆是讲述了“底层”的声音而受到瞩目,引起观众的好奇与兴趣。纯文学领域里,在文字构筑而成的想象空间,以及永恒的人性思考议题的优势外,外在文化或环境的特殊性,具有一定的阅读吸引力。
当前,学术界精英化的讨论议题,明显划开了其与文人圈的距离。这种距离,对于大陆当代文学在台湾的传播情况势必产生影响。即使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讲述“反对阐释”的论点,认为作品的意义应是让读者自行发现与思考,评论的“中介”工作只是其一、而非惟一,然而在引介中国台湾文坛相对陌生的文学作品时,也只能先藉由基础化的学术视野,观看/阅读文学作品,拓展作品的能见度。今年的台湾师范大学“全球华文写作中心”主办第三届华文作家论坛时,不再如前两届一样邀请学者撰写正式论文,转而以作家短评作家的方式呈现;或是人间出版社创办的《桥》刊物,直接以短篇论文方式评论青年作家作品,皆是显现了“引介”华文文学或两岸文学的实质需求。在媒体曝光率不高的情况下,这种有别于以往台湾正规学术论文的方式,拓展了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在台湾的影响范围,也缩短了学术圈与文人圈的差距。然而,就如同始终在第一线做文学引介工作的《文讯》封德屏社长所说的,目前中国台湾学术圈的研讨会或论文,在专业领域上虽不乏真知灼见,但是能够影响的范围真的有限,尤其在极需学者作专业文化或文学导引的中国大陆当代文学里,第一线的“引介”工作显得格外重要,因此相关学者专家若能结合媒体传播力量,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写短评或论文,将会引起读者的阅读与讨论兴趣。
文学工作者的修炼
□苏敏逸
一个可以通过历史考验,继续流传下去的作品,必定有可以层层挖掘的深度,而这样的深度得以被挖掘,必须依靠细读的功夫,以及随着年岁慢慢增长的生命经验和知识积累。但这一切必须要有一个重要的基础,叫作“耐心”。
“急躁”和“喧嚣”是我对现代生活的整体感受,它们表现在没耐心、沉不住气、急功近利、追赶潮流,也表现在凡事讲求业绩、效率和投资报酬率,更表现在对事件、问题的探究、思考和反应都强调即时与快速,轻易地发议论、下结论,却如同浮光掠影。我以为一个生活还过得去的文学工作者应该与现代社会风气拔河,文学工作者最重要的修炼是“沉得住气”,在“慢”与“静”中,认真“读书”和“生活”。
在“慢”与“静”中,才能不追求效率,不在意得失,把个人缩小,以沉静、平静的心绪面对和反省生命的课题、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诸多问题,也才能沉淀杂质,廓清本质;也只有把个人缩小,人才能看到他人、看到社会。我始终觉得,我在当代作家的作品中,很难看到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品中的某种“整体性”(这里的“整体性”,指的是清晰的社会观、世界观)。或许,暧昧不清原本就是当代作家所追求的效果;也或许,是我自己读得不够全面、仔细。当然,当代作家所面对的社会变动过于快速而剧烈,让作家更加难以把握,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始终认为,在鲁迅等人的那个年代,他们所面对的也同样是一个混乱复杂、看不清前景、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他们掌握各种社会讯息的方式和能力更是远远比不上我们现代人。如果当代作家能够把个人缩小,把眼光往外投注,同时放慢写作速度,在平静的心情中,用更长的时间观察和思考,沉淀和琢磨,也许也能够慢慢建立作家个人的“整体性”。
“读书”对文学工作者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文学工作者本来就应当怀有旺盛的求知欲,对“人”的一切知识感到好奇。但我更想强调“细读”古今中外各种伟大经典作品的重要性。透过细读,让伟大作家的情怀、胸襟浸透自我的生命,因为我始终觉得,伟大作家不论如何复杂,他们都有同样的特质,就是对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与“爱”。这样的阅读熏陶能增加文学工作者生命的深度与广度,即使不从事文学工作,对一个“人”的培养,都是有益处的。
“社会主义”与日常书写的再辩证
□黄文倩
在考察茹志鹃晚期的各种材料时,我注意到,其实她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教条化非常自觉,也因此才能在新时期初期立刻创作出具有现代派意识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同时,茹志鹃其实自觉地意识到,如何处理早年“社会主义”和日常叙事的矛盾与断裂,是推进后来具有公共品格与进步意义的文学的重要生产条件,尽管她对此问题的清理,在20世纪80年代以自由主义和西化现代性为主导的历史条件下,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但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重要资源,还是值得我们妥善清理、归纳并引为今日借镜。
首先,从经验与现实取材的意义上来说,她充分意识到即使是下乡、驻点,各式的所谓向底层学习的理想实践中,对作家而言,其滋养并非简单线性的生产。其次,茹志鹃在晚期的创作观中,在许多篇幅里,均非常自觉强调作家跟知识、思想、历史、修养、敏感、激情与想象力等“艺术民主”的关系。她语重心长地反省“社会主义”文学在重视生活之外,与其他面向与环节的“综合视野与能力”的缺漏。第三,结合前两项的视野与观念,茹志鹃既然体认到要在一己的具体生活中,以“人”为题材的核心,同时在情感上,作家要忠于或维持自身的主观性,并自觉要求思想和艺术上的种种经营,对一个女性作家来说,她晚期在理论上的整合回应与落实的方法,就是将“社会主义”与日常叙事再一次辩证式地重新联系在一起,具体来说,就是不避家务事、儿女情的题材与叙述。第四,茹志鹃晚期创作观的特殊性中,还有一点亦接续了“社会主义”文学对光明的信任与突出美的倾向。
茹志鹃所理解的日常叙事(包含家常、儿女情、人的命运、个人感情、想象力、生活中的光明与美等等),不可孤立与作普遍性看待。它不仅仅是一种作者用来扩充与补充早年“社会主义”在题材选择、人物发展、忠于自我情感特殊性的文学方法,亦是建构饱满而非框架化的文学思想内涵的一个个具体环节。是对美与艺术之于“社会主义”应有其独立与特殊性的综合尊重与强调,是她晚年对“社会主义”文学所形成的教条限制的一种美学责任的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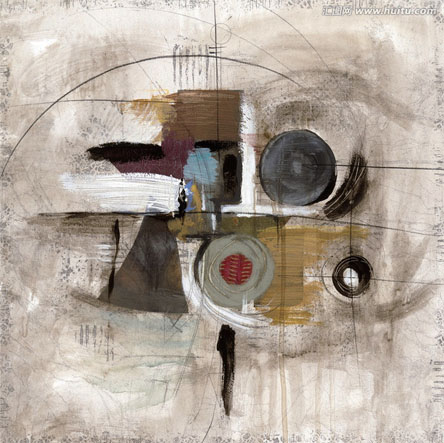
记忆(欲望)如何面向(回避)历史?
□彭明伟
我们常听到对当前两岸作家的作品越来越趋向个人化有所微词有所批评,他们的作品其实正反映了后现代社会的处境或精神困境。除了过度自恋、不可自拔的写作者,还是有不少作家清楚意识到这种没有稳固价值体系支撑的精神困境,面对这样的惶惑不安,他们的创作努力便是要走出自我个人中心的生活,重新确认自我与世界的关联。我们从近年两岸20世纪70年代生人的作家作品中普遍可以看到这种焦虑与化解焦虑的尝试努力。他们化解精神空镜的方式是透过写作,书写的题材则是记忆,通过记忆、想象,希望通向社会历史,把作家个人与他所生活的世界的过去与现在重新连结起来。
记忆与历史不是相通的,而是相克的。打个比方来说,个人记忆与社会历史像是两块磁铁,许多作家透过书写个人记忆、家族史来通向社会历史,但往往个人记忆与社会历史之间有看不见的相斥力,个人记忆越想向社会历史靠近,却将社会历史排斥越远。应该反思个人记忆的叙事威权,质疑记忆的无限扩张和繁衍。只有翻转磁铁的正负极,重新认识到个人的不自由、个人记忆被历史形塑、个人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个人记忆自然与社会历史产生相互吸引力,个人记忆才能通向社会历史。
由《桥》看两岸“70后”小说创作
□高维宏
两岸“70后”的当代作家可能面临两个困难,一是自我与大众的距离,这个问题包含着自我反省的面向。另一是要抵抗的事物越来越模糊,这个问题包含着对于自身以及当下社会问题的思考。这两个问题看似对外,但都与自我连结在一起。要改变自己的习性,走近他人。又要认识其中的异化之物像是鲁迅说的无物之阵。换言之写作并非只单靠自然以及突显个人的天才,而是需要有意地考虑他人的。
近年中国台湾流行“走出‘舒适圈’”这个说法,一般用以指人需要脱离自己熟悉的环境才能够成长。或许写作也有“舒适圈”,走出“舒适圈”的真意应该是要走出自己的世界去理解他者,是要抵抗渗入血肉之中的资本主义的消费与竞争逻辑,反复地辨别自我之中的异己之物。希望中国台湾“70后”写作能够从前贤作家的创作中提炼出抵抗现实的武器,以中国大陆的文学作品作为窗口,补充台湾文学长期以来缺少的左翼现实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