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故事与文学启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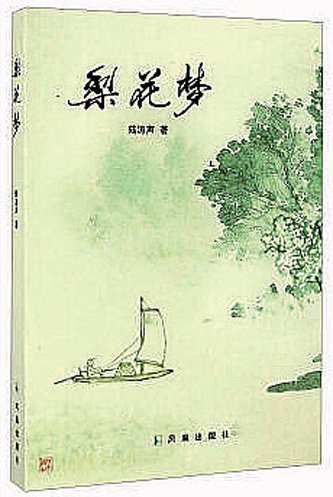
“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新文化的启蒙运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为公众开启了一道希望之门。五四文学用新文化的人生观价值观感受、理解、思考衡量、评价历史、社会和人生,批判旧生活,憧憬新生活。鲁迅的《阿Q正传》开启了乡土文学对农民悲惨命运和愚昧精神的透视,随之便是茅盾的《蚀》三部曲、叶圣陶的《倪焕之》等多位作家作品,对现实作了细密描绘、深入剖析,催人觉醒。文学启蒙的传统浸润了一代又一代有良知的作家。而不久前,一位佛门高僧却对一位作家感慨说:“这30多年,因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流进和文学的名利化、商业化的蔓延,文学的启蒙品质渐被消解,许多作家的迷惘也纵容了人生迷惘……”这显然是深怀忧患的醒世之言。
然而,我们惊喜地发现,江苏作家陆涛声继承鲁迅精神,长期倾情农村,甘守寂寞,关注现实人生,坚持创作反映农民生活的小说,从文化角度对农民劣根性——即小农意识当代性表现作审视与解析,痴心地担当着呼唤觉醒开启民智的责任。归根结底,当前各种腐败现象和社会不良风气几乎都与小农意识有关,是改革前行的阻力。而陆涛声的长篇小说《梨花梦》,通过男主人公柯正华之口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大农民”。这显然是对小农意识的革命。
长期以来,小农意识的短视、狭隘、虚荣、好走极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产生了无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小农意识,不仅仅是现实中农民身份的人有,各社会阶层甚至号称精英的人也有。《梨花梦》描写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一批农村年轻人走出高中、大学校门又回到农村。他们有一定文化知识也有新的视野,但又或多或少带有小农意识,面对商品经济大潮带来的多种观念撞击,选择了不同的人生目标,也经历了不同爱情婚姻的悲喜剧,展示了不同的品性和灵魂:李亚娟是村支书的女儿、柯正华的高中同学,一直明恋柯正华却遭父母反对,她能抗争,却又有权力的优越感,怀有用父亲权力佑护柯正华创业的心愿,然而这恰恰犯了柯正华反感权力干预的大忌;她最终被父母安排嫁给乡里首富之子,满足于逛商店购物的享受,安于依附而放弃自我价值实现。柯正华同学蒋惠东,学了钣金冷作技术在工程队当技工,收入并不低,却羨慕工头轻松赚大钱、高消费、有情妇,弃工“经商”,臆想依赖权力赚钱而讨好官员,为维持当“老板”的虚荣面子,盲目追逐时髦,然则屡经营屡失败,最终陷入困境。乡副业办副主任杨志远,利用经济改革规范的不完善,大搞权钱交易;还通过欺骗、陷害等手段,掠得了陈玉姝的“爱情”;行事大胆疯狂,有流氓无产者习气。树苗供销商吕荣坤,性格豪爽率直,但要面子好做老大且易轻信,遭暗算而损失惨重。当民办教师的玉姝爹,因工资低,见邻居赚钱而心里不平衡,为另寻财路一度不专心于教学。没文化没技能而贫穷的土根,当过兵在首长身边服务过,意外得到老首长关照,“采购”煤炭轻松发了家,便觉得有了地位有面子,许愿帮玉姝爹找干部说情,安排树苗销路。土根的马脸老婆,因暴富而得意忘形,无知、刻薄,竟对当教师的玉姝爹一家颐指气使……这些人表现了不同的人性弱点,根源都脱不开小农意识。
然而,小说中更着力刻画的,是陈玉姝和柯正华两个艺术形象。
男主人公柯正华从小受到“右派”父亲和大学教授舅舅的熏陶,读中学时受民族资本家沈九如先生资助家乡办学的情怀感染,读大学时又被爱国华侨陈嘉庚爱国事迹感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畜禽研究所,因遭遇不公而辞职回乡养鸡。对于大农民,他的理解是“有文化,有见识,有气度,有教养,有担当,眼光能看大局,视野能及世界”。他以当“大农民”自勉,他按市场需求规划发展,培育新品。曾几次遇到刁难,在屡经挫折中不断发展;他还计划把养鸡场改建为科研、饲养、营销中心,探索出一条农村养殖产业化、现代化发展的新路,以让农户代养方式帮助周围贫困农民致富,从一家到30多户,计划达到上千户。他也有认识的局限性,也造成失误,然而事后总能严格自我反省,“能勇于否定自己该否定的方面,重新找回公正”。他坚持实事求是,宁可不评劳模,也不肯虚报数字。他认为“跟风,永远找不到正道。“退一万步说,即使政策有变,所创造的一旦不属于我个人,终究还是社会客观存在,抹杀不了,我的脚印终究留着。”这就是大农民的境界。他不断探索真理、觉悟人生,是农民队伍里对自身阶级局限的自审者、叛逆者,把农村改革当作一次人生的洗礼。
女主人公陈玉姝与柯正华本是青梅竹马,相知相惜。她当民办老师的父亲求财心切,遇危急时受到了杨志远的“救助”,迫使她陷入杨志远结下的蛛网,被他掳进怀抱。她性格软弱,有依附性,易轻信,也一度迷失于富有生活,酿成了婚姻悲剧;经历生死之劫、剐心之痛后,她从教训中觉醒,重新认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人格走向独立,并再次经受了感情纠葛与权力优越的考验,一步一个脚印地创出自己的事业,觉悟到“幸福只是行动的热情与创造的满足”,努力创造机会帮助更多人就业脱困,最终也成长为“大农民”。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名著《怎么办?》中女主人公薇拉这个艺术形象,是沙皇独裁统治没落与俄国解放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的转型时期孕育出来的,小说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薇拉是个“新人”。《梨花梦》中“大农民”产生的时间,也是改革开放带来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观念撞击与交糅时期,即历史性变革的转型时期。柯正华与陈玉姝脱颖而出,是新一代农民中的觉悟者,眼光从乡村放远到都市、海外。反映了新一代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的自我批判、自我觉醒,完成了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转变与境界升华,是凤凰涅槃,也是破茧成蝶,是中国农民中的“新人”。这支农民队伍内部产生的自我觉醒与升华,比来自外部的批判珍贵十倍百倍。虽然在当时的农民中还不是多数,但代表了农民跟上现代文明的脚彻底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
陆涛声是第一个描写“大农民”的作家,突破了传统的农民题材的创作。小说情节人物命运由人物性格决定,合情合理,真实感人,由主要情节派生衍发的情节,出乎意料之外,入于情理之中。无论是刻画“新人”成长,还是小农意识的现实表现,都极其用心地描写他们各自复杂的内心世界,展示了他们矛盾的心路历程,特别细腻特别精微,可读性很强。人物所作抉择,无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能唤起读者与小说人物一同进入心理体验,甚至读者也会自身试作假设性抉择,总结经验、教训,获得启迪,产生觉悟。这正体现着新文学的启蒙精神。小说中多处诗意地描写了梨花。梨花梦,是柯正华和陈玉姝的创业梦,更是灵魂自我更新的梦;其实也是涛声希望传统农民成为新人“大农民”、改善民族整体素质的梦。笔者以为,面对当代人信仰、道德、价值观的现状,当代文学应当回归启蒙传统。
(《梨花梦》,陆涛声著,凤凰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