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索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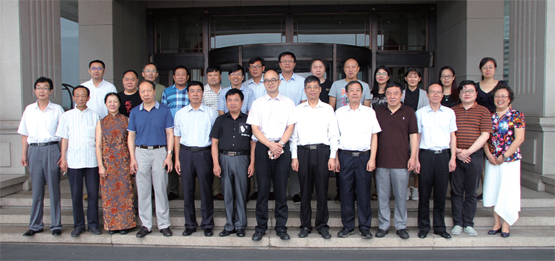
9月10日,“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三辑专家座谈会在山东威海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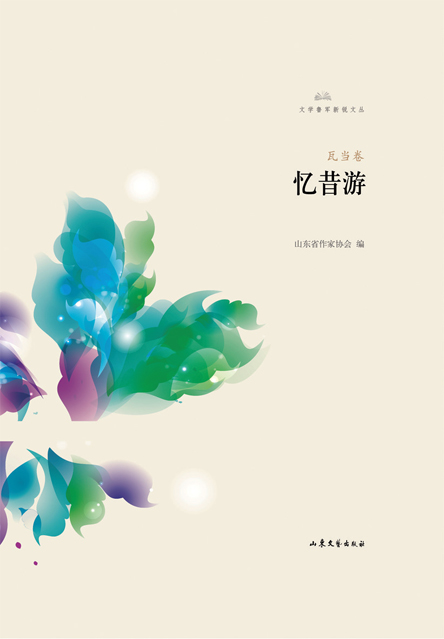
《忆昔游》共收录了瓦当的9部中短篇小说,从题材和内容上看,大都以第一人称写成长历程中的亲情、友情和青春的躁动,写自己的生活和情感,可称之为成长小说。
从创作风格和表现手法上看,《在人世的忧伤》《织女牛郎》《时间到,该变回瓦当了》这3篇,明显受到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影响。虽有故事、情节和人物,但大都是变形了的:荒诞、极端、真假难辨甚至不符合生活逻辑,基调也大都消极、灰暗。
《在人世的忧伤》中,写“我”坐车回家途中,车子抛锚,在帮同车女人找走失孩子时遇上流氓,女人受侮辱,我被打的遭遇。故事荒诞极端,基调消极灰暗。作者通过这个极端故事,表达了悲观厌世的情绪,读来令人绝望。
《织女牛郎》写我被骗,又被三个旧时伙伴戏弄祸害——拖入水中。故事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也不乏戏谑、幽默、俏皮,故事很无聊,却似乎也不乏严肃主题:朋友间看似亲热的背后,、却也暗藏虚伪与背叛。故事的语言比《在人世的忧伤》稍显干净、流畅。
《时间到,该变回瓦当了》写几个年轻伙伴为打发时间进行的游戏,“我”甚至时常神经质、莫名其妙地在深夜敲门呼喊自己的名字,丑女伴蓝盛衣则在“我”和华英雄两个男人之间来回穿梭,玩情感游戏。结尾处,“我”在雨中大声呼喊自己的名字:时间到,该变回瓦当了——小说写出了“我”和年轻伙伴们生活的极度无聊,精神的极度空虚和痛苦,结尾处那声“时间到,该变回瓦当了”的呐喊,是“我”痛苦中觉醒的自我呐喊和自我救赎。
上述3篇小说的作者试图写“现代派小说”,而最后一篇喊出的“时间到,该变回瓦当了”,既是小说中人物痛苦中精神的自我觉醒和自我救赎,同时也是作者小说写法上觉醒与转变的开始。从第4篇到第6篇小说,无论中短篇,都开始有比较完整的故事、人物、情节,都比较符合生活逻辑。相比而言,我赞赏作者写法上的这种回归。
《北京果脯》描写一个名叫树人的男人不安于现状,某一天和妻儿不辞而别,到北京后噩梦般的经历。小说好看,尤其是题目与结尾的呼应,与残酷沉重的故事相比,有举重若轻之妙。但这篇小说故事灰暗低俗,尤其是对性事自然主义(或原生态)的描写,太过直露放纵,不仅毫无美感,且有把玩和猎奇之嫌。小说所写人物经历太过极端、阴暗,令人难以置信,因此树人这个人物的经历似乎也缺乏普遍意义。
《揭谛揭谛,波罗揭谛……》这篇小说关注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郑成是“我”的少年玩伴、没妈的孩子,在学校时因一次以《母爱》为主题的故事班会受到刺激,离家出走,其父外出寻找却找回一个假郑成,其间假郑成与同龄伙伴王大勇恋爱,因太爱对方而将其杀死,被警方判刑坐牢后越狱。真郑成这时失而复得回到家中,却已经变成整天坐在校门口的痴子,因被宝子嘲弄引发一场打斗,宝子和王小勇被开除,“我”则被留校察看。结尾处,小说这样写:我在学校广播体操的乐曲声中感到无处不在的荒芜。小说的故事和人物虽也不乏荒诞,但内容、内蕴比较严肃,值得提倡。小说题目同样很巧妙,与内容很切合,题目其实是引用和尚念的一句经文,“揭谛揭谛”的大概意思是“去呀,去呀”,“波罗揭谛”的意思是“走过所有的道路到彼岸去啊”。这个题目,明显是对小说中呈现的问题少年既无奈、忧虑和呼救,又有祈祷的成分,很有意味。
然而,就综合质量而言,我认为《欢乐颂》是这部小说集中较为出色的作品。《欢乐颂》讲述的是:林水因与村长儿子、流氓孟强恋爱,遭父亲阻挠,父亲被孟强用硫酸袭击致死,孟强逃离家乡,案子多年未破。林家老太太一直怀恨在心,漫长的岁月里每天几乎不忘教育、动员林家老少报仇雪恨,闹得全家鸡犬不宁。直到多年以后,林水出嫁,林老太太肺癌而死,林水孩子出生,新年来临,全家才如释重负,回归正常生活和新年的欢乐之中。这篇小说采用白描手法,语言简洁且富有张力。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对复仇这个古老话题换了另一个视角,赋予了新意,虽然其中的情节编排、人物性格发展是否符合生活逻辑,个别地方亦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整体构思、立意都值得肯定。
余下3篇均为中篇小说,作者叙事采用的都是第一人称。
《忆昔游》写的是作者的青春经历和记忆。小说以回忆为线索,描写“我”与同学或工友的青春躁动,生活、工作、友谊与爱情,当中也不乏对理想的追求与坚守。运用了传统写实手法,色彩丰富(当然也包括暗色和亮色),有青春生活气息,故事、情节、细节和人物塑造相对完整,也比较符合生活逻辑,读来让人感觉轻松亲切。
《我的父亲母亲》和《我的故事》这两篇,从题目看近乎朴拙,我理解作者大概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作者确实是写自己的经历和熟悉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刻意要增强故事的可信度和作品的亲切感。
《我的父亲母亲》,题目与张艺谋的一部电影相同,乍看毫无新意,但小说的内容却有着作者自己的发现和思考。小说以“我”——一个孩子的视角观察父亲与母亲的关系,父亲是像个木头人一样的搬运工,母亲经过一次外遇后与父亲同床异梦,直到有一次父亲被误抓进拘留所,母亲才顿悟:原来自己的命是与这个木头般的男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那场风花雪月的爱情到头来只是一场噩梦。这样的思考很接地气,也很有人情味。
《我的故事》我以为也是本小说集中另一篇出色的作品。作者关注的是一个拆迁钉子户的家庭,作者在结构这篇小说时颇具匠心,先不交代写的是拆迁钉子户,而以“我”的视角潜入并置身于小说的人物和事件当中,写这个家庭过去几十年的悲惨遭遇、恩爱情仇和离愁别恨。结尾处才借助一则报纸新闻,交代出这个家庭是拆迁钉子户。小说叙述时是以这个家庭中不同人物的身份,不断变换叙述视角,既丰富了结构层次,也使小说整体显得错落有致、风姿绰约。更可贵的是,作者通过这种颇具匠心的结构安排和叙事方式,对这个底层拆迁钉子户生活的不幸,寄予了深深的理解与同情,显示出作家应有的平民意识和悲悯情怀。
读了瓦当《忆昔游》这部小说集,我对瓦当小说创作的总体印象是:作者有很不错的潜质,创作时也不乏机智,比如小说的题目(像《北京果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也比如个别小说的结构(像《我的故事》);小说大都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写的多数是自己的经历和熟悉的生活,与大多数年轻作者一样绕不开“成长”的经历和视角;表现手法、创作风格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行,作品也在不断进步、成熟。但如果以更高的标准衡量,我以为作者还存在不足:首先是小说的构思和题材的选择上,要么太过依赖自己的生活阅历和生活经验,要么太过依赖极端想象和荒诞的臆造,生活视野和对人生的认识都存在一定局限,从他的小说中看不到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其次是小说总体上仍停留在对生活表层的呈现,缺少深度的挖掘和思考,因而未能真正写出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是小说还未能成功塑造出鲜活、生动、立体,因而也让读者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当然,这三点不足,其实也是当下大多数小说作者的普遍不足,非瓦当一人独有。好在瓦当还年轻,只要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更高的追求,我相信他一定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