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森·怀特海《地下铁路》:美国奴隶叙事的暗黑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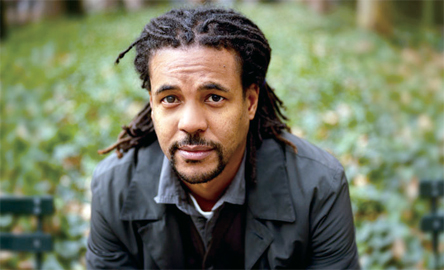
科尔森·怀特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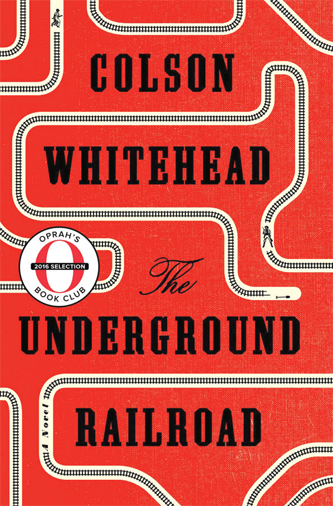
《地下铁路》英文版
有两样东西我有权利获得:自由或死亡。如果我不能拥有一样,我就要拥有另一样。没人可以活捉我,只要我还存有一口气,我都会为自由而战。
——哈丽特·塔布曼
以虚构的方式重审剖析奴隶制,似乎成了近年来美国作家写作和影视传媒的热点:小说有詹姆·斯麦克布莱德《上帝鸟》、保罗·比蒂《叛贼》、凯斯·雅阿《归去来》、詹姆斯·汉娜汉姆《美味佳肴》;影视剧则有重拍剧《根》、新剧《来自地下》、电影《为奴十二年》《被解救的姜戈》《捉拿》等。它们大都不是纯粹的历史作品,有些干脆就是寓言性的,充斥着“怪力乱神”与荒诞的情节设置,因种族关系的紧张而有意无意地介入到现实焦虑的情感状况,获得了某种程度上可称之为“一部很重要的作品,讨论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们当重点关注”的文化资本,进而成为观看/阅读的热点和传媒/文学大奖的常客。2016年8月,在美国文化史上时隐时现的奴隶叙事链又添新丁:奥巴马和奥普拉力荐的《地下铁路》正式出版;11月,科尔森·怀特海的这部作品获得2016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奖。
一
《地下铁路》是一部考验作者/读者精神强度的残酷戏剧,充满血腥、暴行、死亡与绝望。它将饱受奴隶制和种族歧视戕害与摧残的黑人身体和心灵历史,编入黑人少女科拉穿越时空、寻找活路/母亲的“奥德赛”之旅。在行程中,科拉见证了内战前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是如何被奴隶制所形塑,美国人蓄奴与废奴之战是何等残酷和一步步走向激化的。
小说的主线设置在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整个国家日趋分裂,南部进入棉花资本主义的黄金发展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席卷整个美国北部,西部大开发也初见曙光。美国政府出台《逃奴追缉法案》,黑奴逃亡和保护逃奴的行为都成了罪行;大量关于黑人是上帝单独的造物、低等的人种,奴隶制是对黑人的保护,逃亡是他们漫游躁狂症发作的结果等奇谈怪论以解剖学、人种学和神学的面貌到处流传。
科拉生而为奴,是个弃儿。小说的主线是仿自托尼·莫里森《宠儿》的三代黑奴女性叙事。当祖母阿佳瑞还是非洲内陆的乡村小姑娘时,父母就已经被绑架了。她第一次看见大海是在被送上运奴船的时候。在船上经历两次不成功的自杀后,祖母放弃了努力。一次次地被贩卖、拍卖和转让,不断被估价、再估价的经历,让她很快发现了奴隶制背后的资本主义逻辑——马克思在稍后时代集中思考的物化/异化问题:黑人就像物品一样,都是有价值的,其价格总是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摇摆不定。她最终来到位于佐治亚州的兰德尔种植园,先后有了3个男人,在棚屋木板上生了6个小孩,只有科拉的母亲梅布尔活过了10岁。最终阿佳瑞因中风死于棉田。梅布尔不像阿佳瑞这样认命。怀上科拉时她的丈夫因发烧死去,在绝望中度过10年后,她又遇上最好的朋友投缳自尽,终于将熟睡的女儿从身边轻轻推开,选择了逃亡。当自由就在眼前之时,她想起被抛弃的女儿,又决定回到种植园,在回来的路上被沼泽吞噬。梅布尔是《宠儿》里塞丝那样的形象,一个充满歉意、试图救赎对女儿遗弃之罪而终不得的母亲。
科拉继承了祖母的坚韧、睿智和母亲的安静、执拗,身体结实,沉默寡言,没有受过教育却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敏锐的判断力,是天生的倾听者和观察者。她的人生观主要来自口口相传(“奶奶说”和“妈妈说”),秉承绝大多数黑人女奴的“活下去”哲学。“定量配给”的苦难生活和母亲的抛弃,更让她成为早熟的犬儒主义者,对听到、看到的一切都充满怀疑。母亲走后,她在奴隶主的虐待、对母亲的怨恨和周围奴隶的白眼中,像野草般野蛮生长,惟一的“财产”是传自祖母的不到3平方米的菜地。当她的菜地被人侵占时,她挥起斧头捍卫继承权,迎来了被玷污、被捆绑、被殴打的少女时代。这时,种植园购入了一个黑人男性奴隶凯撒。他受过教育,鼓动科拉和自己一起寻找传说中的地下铁路,逃往象征黑人自由和幸福的北方。科拉断然拒绝:“白人总是试图慢慢杀掉你,有时他们想着快点杀掉你。为什么要让他变得轻松?这是一种你可以说不的工作。”后来,为保护同是弃儿的切斯特(其父母被卖)而遭受暴虐成性的奴隶主特伦斯的野蛮毒打,并目睹针对逃奴的残忍火刑后,科拉终于明白“逃或者死”的道理,在凯撒的再度相邀下,带上一包自种的甘蓝,踏上了寻找“奶与蜜之地”“迦南”的“出埃及”之路。
二
在科拉杀掉前来追捕的白人少年后,他们来到了地下铁路的“站点”——一个谷仓,跳上了第一班列车,开启了神秘的地下铁路之旅:“……铁轨或南来或北往,自不可知地来,往应许之地去。”
“地下铁路”早在18世纪就以帮助南方蓄奴州奴隶逃跑的组织形式而存在,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它被定名为“地下铁路”。逃跑者落脚或找到食物的房子被称为“火车站”,由负责人(“火车站站长”)和干事(“经理”)组织、维持。向导(“乘务员”)负责带领队伍在两条路线(从中西部直奔加拿大,或沿东海岸一直向北)前进。到内战爆发为止,由白人废奴主义者、同情者、自由黑人和前逃奴(之前是逃奴,后来过上自由人生活,但身上仍有种植园烙印)构成的队伍,已帮助数万奴隶获得自由。小说用地下铁路网络取代一个松散的、事实上存在于地上的拯救黑奴联盟。地下铁路从喻体变成了本体,从所指移动到能指,成为一条实际存在的“地下的铁路”:建在南方蓄奴州地下,有车站,有火车,有枢纽,有乘客,有隧道,秘密运行。火车何时来何时走,自何处来开往何处,上车后才可能知道。
地下铁路是典型的蒸汽朋克叙事装置。蒸汽朋克是发端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亚文化科幻题材。它以19世纪工业革命时代为背景,将蒸汽动力机械“神话化”,通过大量蒸汽机械元素的运用,构筑出幻想与怀旧交织、过去与当代打通的超现实科技世界乌托邦。蒸汽朋克最基本的设定是科技对于历史的反叛,当超越时代的科技出现时,时代必将被其改变。小说中,地下铁路、流水线作业、摩天大楼、电梯等给人以科幻的“乱入”氛围。与一般蒸汽朋克相比,小说提出的问题:当地下铁路从个人行为变成乌托邦式的地下铁路网之后,历史会随之而发生巨变吗?
小说大量描写了监狱、疯人院、运奴船、阁楼、沼泽、墓园、绞刑架、种植园木屋、猎奴人马车这些 “非正常人类”活动的不正常空间。它们是福柯所定义的异托邦空间,是既受主导性社会秩序规约又在组织逻辑上出离其外的另类空间,是美国这一想象共同体中的异质因素,如小说中用词:“它的缺陷”。地下铁路正是由隐姓埋名的站长、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乘务员、长期穿行于地下隧道的司机以及亡命奔逃的黑奴等“化外之民”共同活动其中的异托邦空间。它不构成乌托邦,也无法改变美国,而只能改变科拉。
地下铁路开启了科拉“格列佛”式的美国之旅。在白人的排斥、法律的阴影以及猎奴人里奇韦的追踪下,科拉只能如荆棘鸟一般逃亡,落地就意味着被抓捕、驱离甚或死亡。在逃亡之旅中,科拉遭遇了一个由不同风格的州组成的“复数”的美国,“出埃及”后发现到处都是新埃及,寻找迦南却发现自己背上了“迦南的诅咒”:“逃出来了,短暂地站在阳光里,然后转身,再度成为奴隶。”自由充满不确定性,安全仅仅是暂时的,“然后”没有“然后”,只有逃亡似乎没有尽头。首站她来到南卡罗莱纳州,换了假名,成了美国政府的财产,当上保姆,进入专门的黑人学校;生平第一次进商店买衣服;被要求做生育能力和智商测试,甚至差点被做了绝育手术,旁观了1930年代臭名昭著的黑人“坏血”实验;成为自然奇观博物馆的雇员,装扮回奴隶成为主题为“进步时代”的玻璃窗布景展里的“活道具”。为躲避追捕,她又回到站点,在黑暗中经历漫长等待后逃到北卡罗来纳州。然而那里不仅废除了奴隶制,同时还想“废除”黑人;“自由之路”两旁的树上挂满了黑人和白人同情者的尸体;在阁楼上幽禁数月,从墙洞里窥探到白人恐怖分子夜骑的私刑场面,终于被里奇韦抓住。由于里奇韦“生意”上的需要,他们来到田纳西州,她被救下,前往印第安纳州,被安置在瓦伦丁种植园——一个墙上写着“留下·贡献”标语,共同劳动、生活,有诗歌有戏剧有学校有布克·华盛顿与杜波伊斯同台辩论的黑人自治社区——地下铁路中转站。这个黑人“黄金国”很快也被白人暴徒焚毁,里奇韦再次抓住了科拉,逼她带路前往本地的车站。她带他来到“鬼站”——一个从未启用也不和其他线路互通的站点。抱着里奇韦一起滚下深不见底的台阶,杀死了他,逃出生天。她在前往西部的车队中选择了一位前逃奴,一起踏上了西进之路。科拉和地下铁路的故事结束了。在这一刻,科拉又回到了历史的主线之中,向美国刚从墨西哥手中战取的加利福尼亚州而去。
三
作者科尔森·怀特海是美国“60后”知识分子作家中的一员。这一代作家在风云激荡的上世纪60年代不过是孩童;成长于日趋保守的70年代,只能在B级片的暴力与惊悚中寻找父辈“举世皆敌”的血性与荣光;当他们80年代在学院接受了精致训练转而登入文化场域之时,整个场面都是意义模糊的各种“后”(如后垮掉派)在苦苦维持。和前代人被定位为“文字一代”相比,他们被认为是“视听一代”,在卫星电视、电脑游戏、类型电影、漫威漫画、摇滚乐的大众文化氛围里成长,对民权运动没有切肤之痛,对毒品、性解放和各种朋克或习以为常或深陷其中。怀特海是一位学者型的精英小说家,毕业于最重原典的哈佛大学英文系,曾在《村声》杂志社工作,写了大量电视、书籍和音乐评论,后辗转于多家常春藤名校讲授创意写作课程。他是一个摇滚乐、蒸汽朋克、恐怖小说和僵尸电影的爱好者;独自读书、独立研究、擅用网络手段的超级宅男;纽约大都市生活经验的书写者以及黑人畅销书作家。从1999年长篇小说《直觉主义者》开始,他出版了《萨格港》《约翰·亨利的日常生活》《第一区》等8部小说,一部美国扑克大赛的纪实文学作品以及一部散文集。
早期奴隶叙事为了迎合白人读者预期,形成了模式化的自由乌托邦修辞:奴隶在暴戾的种植园园主的阴影下成长,被鞭打被侮辱,开始努力认字,寻找机会逃亡,然后失败,但历经波折之后终于成功到达北方,获得自由。科拉的遭遇和性格,让人想起同时代的传奇人物哈丽特·塔布曼,一个前逃奴、地下铁路的传奇乘务员、逃奴的摩西、即将登上美国20元钞票票面的黑人女性。科拉不是奴隶叙事中常见的、因受奴役而通过战斗或抵抗来争取自由、并与命运血战到底的塔布曼式的英雄形象。她的屡败屡战、挣扎与杀戮,都不过是被动消极的,来自对“活下去”的渴望和刻骨的私人仇恨。对于地下铁路这一带有童话色彩的史诗性人类造物、“不可能之海上的岛屿”,科拉很淡然:“不知道它为什么在那儿,它的意义是什么,所有我想知道的,就是我想停下来,不用再逃了。”在阁楼里,她开始思考并重新认识自由:“所谓自由是这样一个东西,当你注视它,它就不知道偏到哪里去了。就像一片表面上看似茂密的树林,实则内部只是空空如也的草甸子,你总是可以发现它的真实局限。”在逃亡中,她既没有真正到达“北方”,也没有进过大城,更没有形成自己的全美印象:“窗外有且只有无尽的黑暗。”科拉的成长在于她识字后通过阅读和观察,终于获得了关于这个世界最为残酷的自然主义认知,醒悟到美国黑人的“宿命”:新的压迫机制取代旧有奴隶制,这是一个他们在其中生活但又不允许他们拥有的国家。
《地下铁路》堪称叙事技法的样本之作。文本中充满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写实批判、现代主义的心理描写与陌生化/神秘化效果、魔幻现实主义场景的营造,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文类混合、拼贴与戏仿。小说中,这些“主义”不再是递进的、螺旋上升的进化关系,而是一种平行、掺杂的对话关系。同时,小说还混杂着盗墓、奇幻、恐怖等“类型小说”元素。怀特海在其想象/现实、清醒/梦幻左右互搏的写作实践中,以一种实用主义者的姿态自由表达,由此带来了此类小说技法的文学史命名困境,只能像雷蒙·莎迪瓦尔那样从实在论里借来一个术语,将其归类为充满悖论色彩的“奇思现实主义”(speculative realism)。在阅读小说时,我们也许还要听着大卫·博威的70年代英伦摇滚,及到小说的终章,则要调出《紫雨》和《白日梦国家》等80年代经典专辑,它们共同构成了怀特海写作时某种文本内在节奏的共鸣之物。
就主题而言,《地下铁路》是一部关于逃亡、成长、奴隶制拆解、黑人身份认同的复调小说,延续了他在《直觉主义者》里对于历史、种族和机械技术之间关系的想象,用现代场景、真实人物、真实事件切入历史场景,以碎片化的场景、跳跃性的情节处理,切断正史叙述虚幻的线性与统一。其回到历史、架空历史的写法、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对历史文献的考古挖掘和美国黑人史研究的编织使用密不可分。怀特海以史入文,对于历史文献信手拈来的运用,让人想起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以及法国作家洛朗·比内《谁杀死了罗兰·巴特:语言的第七功能》。
就语言而论,《地下铁路》是一部非典型的黑人小说。它既不“饶舌”也不“爵士”,反倒是用语简洁、考究,句子简练、明晰,行文简省、朴素,举重若轻,有些段落读来宛若诗歌。绘人写物则颇类中国传统白描手法,伏笔、渲染均具匠心。一定程度上,这种雅韵从容的文风抚平了小说内容的戾气与粗粝。同时,它也是笔者所见黑人文学中对话最少的作品。“话痨”只有一个,就是那个时而木然时而愤懑时而嘲讽的“不靠谱”(而非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者。为了冲淡文本中弥漫的血腥气味,他以有瑕疵的心理分析、有硬伤的情节设置、破坏读者阅读紧张感的“剧透”、时空错乱的细节,以“七实三虚惑乱观者”的演义手法,刻意制造出阅读上的间离效果。科拉惊险的逃亡、复杂的内心以及凌乱的文本叙事之间构成了“争吵”关系,使得三者之间本应有的完美交流和相互牵制变得无比混乱。通过自由间接引语这一延续自《直觉主义者》的,类似于电影剧本的闪回、旁白与定格技法,他用科拉近乎冷漠的自我保护视角讲述了血淋淋的场景,肆无忌惮地介入科拉的所思所念所梦,让自由、混血、资本主义、种族歧视、美国国家理念、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独立宣言》中人的定义、黑格尔式的主奴辩证、知识/科学的暴力性等等哲思议题在其内心里一拥而上。
小说的节奏时快时慢,焦点摇摆不定,内部存有一个多声部叙事的喧哗结构,不断在“科拉快跑”的间隙插入次要人物的番外章节,宛如长篇小说的大纲碎片,除了作者所偏爱的里奇韦之外,其他人在讲述完毕后就再也不会在后续章节出现,删掉对整篇小说的文气也没有任何影响,读来如同观看一部快进的默片(朱利安·鲁克斯语)。对于这种“任性”讲述次要人物的短章,怀特海解释说:“我想把读者关到现实的小黑屋里,然后再放他‘出站’。我试图真实描写种植园的惨状,为那些虐死的奴隶提供证言,写出他们的生之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