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乌特金《环舞》:当代俄罗斯文学的魅力“环舞”

安东·乌特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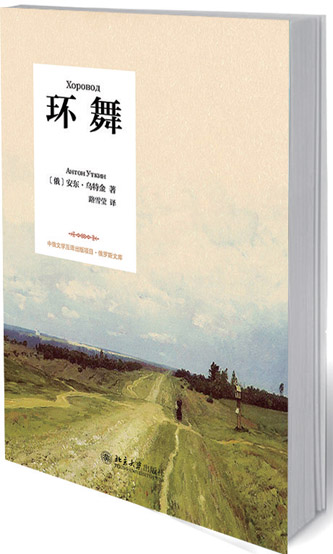
俄罗斯当代作家安东·乌特金的处女作《环舞》于1996年在《新世界》上连载刊出。1997年小说单行本出版,1998年法文版在巴黎出版,2015年中文版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今年8月7日北京书展上,乌特金与中国读者见面,讲述了《环舞》的创作。
这部“异样”的长篇小说甫一问世,立即引起了评论界的强烈反响。大名鼎鼎的文学评论家巴维尔·巴辛斯基坦言:“安东·乌特金突然间闯入了《新世界》,毫无预兆。他太……‘出人意料’了!”时年29岁的安东·乌特金因此一举成名,1996年获《新世界》杂志奖,1997年被提名“布克奖”,2004年斩获雅斯纳亚·波良纳文学奖。
《环舞》采用第一人称“我”,围绕19世纪一个近卫军青年军官的生活史展开叙事。作者的视角始于1836年20岁的自己被大学开除后由舅舅安排,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服役,“事事从身历处中写来”:“我”的公爵舅舅出征欧洲返俄途中与回绝了拿破仑的女人、波兰的拉多夫斯卡娅伯爵小姐的爱情悲剧;“我”的军中友人、生活拮据的涅夫列夫中尉爱上了将军的女儿叶莲娜·苏尔涅娃的悲剧故事;“我”与叶莲娜·苏尔涅娃因为舅舅私生子引发的婚姻悲剧;两次决斗、只剩下空壳的书中之书……同时,“话语从心坎中抉出”,似为小说隐含主线的自省独白。小说的叙事构思、背景节点纷繁芜杂——19世纪俄国的新旧都城(彼得堡和莫斯科)、乡村、波兰、巴黎沙龙;俄国贵族、沙皇军官、十二月党人、异族人、异教徒,直至最终患忧郁症的“我”;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征服、波兰反抗俄国占领的起义、霍乱、冬宫失火……情节(素材)与内省、个人故事与历史事件巧妙地环环相扣,成为一个整体。
“‘故事结束了。’你也许会这样说,也许不会。”安东·乌特金将卡拉姆辛《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中这段话作为小说开篇。紧随其后的就是那个“曾以几个大胆的预言震动欧洲”的小老头星象家悦耳的讲述:“预言有双重含义……”“世界就是靠荒诞的东西支撑的……”此时,“身穿有着金色肩饰的近卫军军服”的“我”却在思虑,“要是把那不遗余力地照亮这个小老头、这个大师的微弱烛光哪怕分出一点点给我……说不定我就会忽然看到这张五官端正的脸上显露出命运的奇异征兆,看到他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软椅脚下那一团白色的薄纱裙子。”
作者就是这样开始了独有的叙事构建:将叙述者与小说人物合为一体,使得凭借“讲述”这一动作完成的数不清的荒诞真实与自省独白成为了小说的中心。用作品中人物的话说:“讲述者是裁缝,而语言是量尺……”小说的结尾仍然是:“于是,我把酒一口喝干,讲了起来……”
作者在小说叙事结构上的独具匠心也体现在书名“环舞”上。
环舞是人们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圈跳的舞蹈。安东·乌特金在北京的创作见面会上曾谈到,小说就像建筑一样,其结构是最为重要的。环舞这种舞蹈的表现形式与外部特征恰恰契合了这部小说的叙事结构。小说的名称直接来源于情节的自身发展。小说里人物的命运仿佛手拉手的人群,一环扣着一环,一个命运引发另一个命运,一个事件紧紧接着另一个事件,最后形成一个巨大的圆环,也可以说是运动着的轮子。“我已经明白无误地感觉到我那平淡无奇的命运以某种说不清的方式被锁定在与其他人的命运的交接处,有时那是完全不认识的人,但他们却使我成为他们的事的参与者和接续者。”
这种环环相扣的“铺叙”,行动和人物沿着第一人称“我”的叙事发展时间线索建构开来。莫斯科大学历史专业毕业的乌特金一方面将故事置于19世纪上半叶俄国的现实语境中,试图以历史叙事代替文学的虚构,以大量的史料创造出逼真的想象,达到感染读者、增强小说真实感的目的。难怪小说问世后,文学评论家诺维科夫等都反对将小说归入后现代主义之列,坚称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另一方面,作者又从叙事结构着眼,醉心于彼时和此间人生、宗教、哲学、伦理、时代、社会等一切精神物质层面的内省式独白,亦是对传统的主题叙事、全知叙事的突破。也因此有学者指出,直至乌特金的出现,俄罗斯的独特的文学形式才得以创建,获得了自己的表现形式。在跳跃般、生涩的间或断裂、貌似客观的自叙写实中,自省独白成为小说内涵不可或缺的支撑,成为小说至关重要的中心,因此,无论是否“后现代”,我们都有理由将其称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的魅力‘环舞’”。
“蛾子在我的卧房飞来飞去,诚心诚意地(若有所思)跳着环舞,而那些不经意间闪现的思绪就像南方之夜的星星那样在头脑中闪烁几下,给我带来抚慰,随即熄灭,没有一点遗憾。”这是全书中惟一一次具象的“环舞”,有趣的是,完成环舞的不是人而是蛾子,与之相伴的是闪烁的思绪。而“环舞”典型的表征形式——“圆”却在书中出现了许多次。
“至于说到历史倒退,”亚历山大不情愿地继续说,“你说得完全正确,因为历史是循环的,一种恶走了,另一种恶就赶忙到来。所以我们只能看到变化的表象聊以自慰,其实它们都是幻想的。”“虽然我还没有完成我生命的循环……”
关于命运的论说则贯穿小说始终。“为什么?老实说我很喜欢听故事。了解别人的各种各样的命运是很有趣的。自己只有一个命运。”“人们总是循着不自觉的意愿自己选择了命运呢?”“我成了别人的生活、命运,透明记忆和衰退的故事的莫名其妙的汇聚点,那些人命运的片段就像随风飘荡的浮云,而他们的记忆像不安宁的梦境,他们的故事则产生于传说的阴郁怀抱,它们好像故意传到我的耳朵里,又好像无意中渗透到我的意识中,要求连接起来,就像恋人们颤抖的手在祭坛前握在一起。”小说甚至因此被称为关于平凡与复杂世界的宗教哲学论著。
环舞也是一种古老的斯拉夫民间舞蹈,一种大规模的祭祀仪式,是斯拉夫民族精神的象征、斯拉夫人审美和思想的表达形式、俄罗斯文化的具体体现。安东·乌特金值得关注的另一点正是他对打破经典与传统继承的探索。
安东·乌特金从不掩饰他对俄罗斯经典作家的追随。尽管《环舞》的创作本意是以19世纪历史人物的口吻创作一部回忆录。但在写作回忆录的过程中,许多新的想法在作者的头脑中慢慢成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创作虚构,并衍生发展为一部长篇小说。无论是小说中的人物、风情,事件题材,还是创作风格笔调,都可以见出俄罗斯古典作家,特别是莱蒙托夫对乌特金创作的深刻影响。对于“我”爱上的叶莲娜·苏尔涅娃,乌特金直接就通过“我”的同时代人——莱蒙托夫完成了自己的赞美。“我不觉得她有多么美艳,但在她的五官和举止中一下子就能感受到诗人莱蒙托夫在他著名的小说中称之为‘血统纯正’的东西。”乌特金最初还曾希望自己能像莱蒙托夫一样,在创作出《当代英雄》的年龄(28岁)完成一部优秀作品——虽然最终他的处女作比生日晚了4个月完成。
有评论家称:“若要确定安东·乌特金小说属何种流派,我们可以将之戏称为‘现实主义的后现代派’……将这两种潮流(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自然融于一体的作品,迟早总会出现的:既追求戏谑,也追求严肃,既有鲜活的文学语言,也有对真实性的偏好……以及‘文语’‘卖弄辞藻’‘掉书袋’。类似的作品或许只能创作于当代文学苑囿之外,真的就是这样……”
无论叙事建构,还是笔法言语;无论现实主义,还是后现代,安东·乌特金都值得我们更多地去探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