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娜·加西亚《猎猴》:古巴流散作家笔下华裔群体的同化与异化

克里斯蒂娜·加西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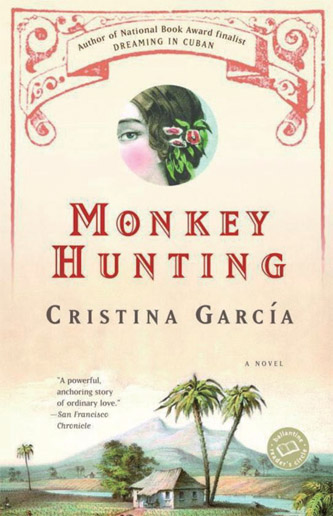
《猎猴》英文版
早在拉丁美洲国家独立革命时期,美国就成为拉美移民的暂居地。古巴就有很多作家曾长期定居美国,他们真实而深刻地记录下少数族裔在美国所受到的文化冲击,传达着流散群体在异域实现身份认同的艰辛。上世纪90年代初,当代古巴移民中涌现出一批活跃于美国文坛的古巴裔美籍作者,克里斯蒂娜·加西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她1958年生于哈瓦那,两岁时同父母移民到纽约定居。加西亚的作品总是以古巴-美国的二元文化身份为起点,讲述跨文化个体为融入主流社会、实现自我认同所做的努力。
近年来,古巴国内对于中国移民的研究日渐兴盛,出现了一系列以中国移民为主角的流散文学。克里斯蒂娜·加西亚于2003年出版的小说《猎猴》(Monkey hunting)就是代表作之一:主人公陈攀1857年离开故乡厦门作为苦力在种植园扎根,而后与黑奴结婚,塑造了四世同堂,横跨中、古、美三国的华裔家庭。陈攀的孙子比伯·陈和重孙多明戈·陈在古巴导弹危机后由关塔那摩移民美国。当多明戈迅速适应了纽约的大都市生活,开始追求同龄人的爱好时,父亲比伯却在思乡和寂寞的双重折磨下卧轨自尽。加西亚对于华裔群体在纽约奋斗过程的展现体现了她作为流散主体的思考。
多明戈和父亲的住处距离唐人街几个街区,位于城市中心忙碌而污秽的唐人街、肮脏而满是社会边缘人群的居所、弥漫的负向情绪,定义了加西亚眼中的华人移民处境。多明戈与同时代的美国年轻人一样,将所有钱花在音乐会和服饰上;与父亲相比,他融入美国的意识是强烈而自发的:“他每周在公立高中上两次ESL课程(非母语英语课程)”。对于多明戈来说,习得英语象征着新身份的诞生:“后天学习的语言……不会像母语一样给他带来充满回忆的打击”。
古巴性与美国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新一代移民面临的一系列身份认同危机跃然纸上。但由于作者的流散身份,华裔群体的形象并没有得到如实表现:一方面,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进行自我观照,对“他者”进行同化,在华裔群体的遭遇中寻找共鸣;另一方面,作者依照自己的阅历和愿望将华人群体的现实处境进行扭曲改写,使得“他者”异化,成为了作者想象中的、具有东方主义倾向、与历史现实不符的二元存在。
比伯与多明戈对于作者而言都属于“他者”,在对于华裔群体的记写中,作家融入了对自身处境的观照,传达了她对自己移民经历的思考以及自我认知的转变过程。童年时期的加西亚随着父母在爱尔兰、意大利、犹太移民的聚居区辗转停留。移民过程中自我身份和群体身份确立的困难成为成年后加西亚最常思考的问题。在《猎猴》中,加西亚尝试了对“多层次归化”的个体刻画,展现了全然不同的流散个体身份设定:或是在流散过程中选择抛弃自身文化属性,极力融入主流文化;或是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尝试中经历多次痛苦而困惑的自省;抑或固守回忆,拒绝文化融合。
加西亚通过多明戈之口发问:“他们现在的世界是怎样的?什么是属于他们的?‘是否有可能’——多明戈想——‘在得到拯救的同时被摧毁?’”最令人痛心的是老一辈移民的“被摧毁”:在纽约陌生的土地上,比伯失去了半生为之奋斗而引以为傲的工作,靠搬运冰块做苦力劳动度日,这是他不愿、也不能理解的。在绝望情绪的纠缠中,自我解脱是最便捷的途径,比伯最终卧轨自尽成为必然:“在纽约,多明戈知道,想要杀掉什么总比留住它便宜得多”。
作家对华裔群体的塑造难以摆脱萨义德《东方学》的话语体系:“他者”往往被塑造成单一属性、片面的群像,而作家对“他者”的历史性和其内部的特殊性往往不加以观照。另一方面,古巴文学传统中的中国形象也对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隐性影响。例如,作家在将中国男性女性化的尝试中,赋予了其情欲旺盛的标签。在《猎猴》中,对于多明戈的描写中充满具有挑逗意味的细节:他静跪于圣母像前,却产生了舔舐其脚趾的冲动;接着多明戈又回忆起幼年时期被同父异母的姐姐抚摸的情景。在东方主义的潜在影响下,加西亚笔下的华裔形象也与华裔群体的实际形象发生偏移。
读罢《猎猴》,读者能够体察到多明戈与比伯作为流散个体试图融入纽约都市生活的无力感,然而却无法确切捕捉到其作为华裔移民的特殊性。这也体现了加西亚在“他者”刻画中的另一个问题:母系话语体系的过于强势。
母系家族的传统首先体现在多明戈的宗教信仰上:萨泰里阿教的信仰连结着对母亲的记忆,这一特有的古巴性让他找到了移民生活中永恒的、可以依靠的文化根源。母系家族的又一影响体现在音乐上。多明戈母亲的家庭中,大部分人祖上都是康加鼓手。而纽约人崇尚的瓦图西音乐与以康加音乐为代表的古巴性相撞击,构成了他在新身份确立中必将面临的阻碍。
另一方面,父系家族的投射在多明戈身上是微弱黯淡的。惟一提到其中国性的片段在于多明戈向茶水里加糖时,忆起父亲向他讲述的家族历史。对于多明戈而言,百年前华人祖先的历史只是模糊而遥远的存在。由于缺乏相关文化传统与记忆的支持,这一微弱的“中国性”并未对多明戈的身份认同造成显著的障碍:“多明戈想要说自己的血统是复杂的。但他应该怎么决定自己是哪里人呢?‘古巴,’他最后回答说,‘我来自古巴。’”
读者也许会问:作为第四代华侨,多明戈自我认同中的中国性是否理应消失殆尽?研究显示,流散主体的中国性并未随时间推移而削减,相反,血统上的多样性令许多美籍古巴裔华人开始重拾家族历史,企图填补移民过程中历史和文化的空白。古巴裔华人摄影师玛丽亚·刘深入哈瓦那唐人街寻找家族迷失的历史;古巴裔华人作家艾米丽·罗的祖父自1949年返回中国后就再无音讯,这促使她重返古巴:“美籍古巴裔华人,不能被任何现存的模型解释”。由此可见,在《猎猴》中,华裔个体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尚可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