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南高原插上翅膀——评普驰达岭诗集《石头的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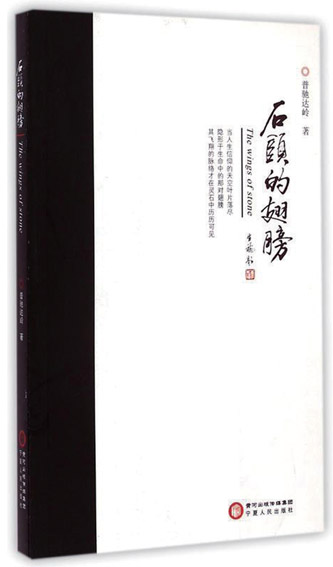
几年前,我读到了彝族诗人普驰达岭的诗集《临水的翅膀》。“突入都市,我们就像一支迁徙的部落无以着陆。”这样的题记让我无法平静。从那时起,我反复研读《临水的翅膀》和其他彝族诗人的佳作,在个性迥异的群体中分辨每一张面容。后来,我读到了普驰达岭的新作《石头的翅膀》,依旧震撼了我。
在《石头的翅膀》中,一个彝族诗人试图为他心中的无边巨石——南高原——插上翅膀。普驰达岭的长句像一块磁铁,吸满历史的碎屑,让历史在诗歌中复活。他令历史缓缓升温,用想象赋予其血肉灵魂,他的想象以独白、追问、对答等手法,在一种清晰的奇幻效果中达成了历史的“在场”。通过“我”,将历史与现实接通,让历史还魂于“我”之身,让生命的质感饱满真实,如针尖扎手,疼痛以无语的震颤波流荡及周身每个细胞。只有在这种深不可测的历史替身的角色体验中,“我”成为孤独的语者与行者,霸占着南高原庞大的地域和繁杂的呓语,与它心有灵犀,生死相许。最倔强的野心终化为最深邃的叹息,展现的是替身的渺小与渺小背后不甘的初衷。
祭祀的语言托着石头升空飞翔,这种新神话的情节用肉眼看不到,完全凭借主体内心力量的抬举来实现。客体的圣化迫使主体成为抵押的人质,主体必然取仰视或跪拜的姿态,说出在谎言和誓言之间无法得到证实的诺言。因而这个主体是忧伤的,忧伤深过了一道伤口的深度,这个主体只有像醉鬼一样被摊开平放在南高原父亲无边的胸怀之上,他的疼痛才有片刻减轻。
客体的圣化——正是要在现实世界找出信仰的物化凭证,或者是信物。谁能说“一只流浪的猎狗,在火塘边蜷伏”不是人类家园理想的真实写照呢?生命需要崇高伟大的事物,名山大川往往作为这种精神寄托品成为当地的信仰对象,它们正是被拔高了的客体,作为对主体的陪衬与拯救,实现对有限世界的超越。主体需要仰视,需要将自身与一个更大的能量场接通,有限的主体不能在有限的自身中得到拯救,他只能在无限的客体中自我夸大,甚至神化。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就是这样创建出来的,并代代相传地维系着民间信仰体系。
与部落的迁徙不同的是,少数民族精英进入主流社会占一席之地,凭借的是个人超常的智能、体能与生存技巧。他们就像卧底的间谍,或者远居他乡的大使,一种无根的生存和空前清晰的眺望与洞察放大了故土的每个细节,成为他们无数静夜里必然袭来的相思。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超人与凡人的双重角色和两极游走,只有植根于绝对的孤独中,一个身影才会显形。只有在无止境的酷刑的冶炼下,爱才得以提纯结晶。石质的呼吸,石块与石片在风中的摩擦声,“我”与历史和祖先的交谈像泪水滴落石上,瞬间就被正午的骄阳烘干。除了当事人,这种对话无人听得懂。巨大废墟空旷而又令人窒息,渺小的个体面对这庞大的遗骸,有时会生出生不如死的绝望。此时诗已经抵达了问题的核心,诗和哲学一起撞入了极限之渊。
反过来,在描绘现实遭遇的时候,作者完全变了个人,谨慎得叫人心悸。除了回忆与眺望,他几乎没有欢乐。提前知晓了谜底,这就是智者生涯的尴尬。即使被族群簇拥,扮演着一部电影的主角,他仍然知道自己只是个观众。献身于历史,意味着在现实中永远扮演旁观者。一个欲望与血肉的自我至今没有打开,所以也未能被塑造,这是致命的缺憾。他主动压抑了有声有色的现实体验,或者灰烬一样过滤并私藏了它们。言说真理的时候,诗人看起来像个幽灵。他的笔下看不出狂热的笑意、裸露的爱意、剜骨的泪意、痛快淋漓的酒意。这就是无法撒谎的智者的失意。代表彝人说话和自己说话是两回事,一个诗人必须更多地言说自己。当他怀着宗教情怀去触碰他的现实时,他是无力的,甚至不忍迈入。
到了卷四的散文诗部分,他终于舒展开来。在舒坦的民俗与淳朴的民风里,不管生身之母是否安在,母语乡音就像母亲的双臂拥抱着你。但从选材的角度看,他还需要提炼点石成金的本领。端庄之美和庞大意象群会使人眼花缭乱,议论抒情也需要有令人过目不忘的语言魔法,深层民族基因与现代审美心理的接轨需要开辟新路径,这些都是我对普驰达岭的期待与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