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文版到日文版——读北冈正子先生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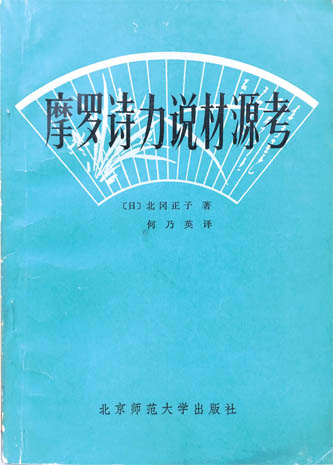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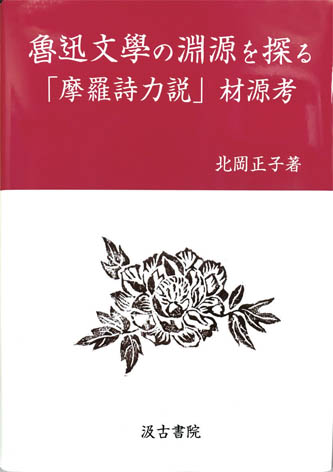
一
提到北冈正子先生,首先会想到她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因这项研究成果很早就被介绍,故已广为中国学界所知。当然这里指的是何乃英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的中文版(以下简称“中文版”)。在中文版出版以前,“材源考”没有日文版成书,只是连载于《野草》(中国文艺研究会会刊)上的“笔记”。首篇《〈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笔记》(以下简称“笔记”)刊载于《野草》第9号,时间是1972年10月。中文版收录了截止到1981年的前15回连载和部分尚未进入笔记的新发现的资料。这便是学界通常所说的“北冈正子的材源考”。
中文版之后,时间过去了32年,“材源考”又出了新版本,这便是日文版『魯迅文學の淵源を探る 「摩羅詩力說」材源考』(汉译名“探索鲁迅文学之渊源 《摩罗诗力说》材源考”,汲古書院,2015年6月30日。以下简称“新版”)。和中文版相比,新版最明显的变化是“体积”的增大。由前者的小32开本233页,变为大32开本的650页。不仅如此,新版还是作者对此前笔记的大幅度扩充和改写——继中文版之后,作者的笔记在《野草》上间以“短休长休”又续载8回,到《野草》第58号(1995年8月)为止,共载24回——因此,即使从笔记停止连载的1985年计算,距新版也有了20年的间隔,出现如此“全面升级”也在情理之中。
诚如作者所言,在此后的20年间,“通过新出版的书籍和连载时未能找到的书籍,获得了可资参考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其中,我有幸得以阅读旧稿写作时没能读到的诗人们的几多诗篇,有幸得以阅读有关历史文化环境的参考文献——历史文化环境对诗人们的人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改稿之际,我补入了新获得的知识,在将其作为一个论考去归纳的想法下,又再次做了全面修改,其结果是大幅度的增补。其中第一章有关拜伦的那一章,因旧稿弄错了材源,几乎是重写的”。(新版后记)因此,就作者的工作而言,新版堪称作者历时43年(1972-2015)“材源考”之集大成,是完结之作。
二
那么,从中文版到新版,作者到底完成了哪些工作呢?由于这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研究成果,考虑到一般读者,这里有必要首先对《摩罗诗力说》(以下简称《摩》)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大家知道,鲁迅1902年4月至1909年8月在日本留学。先是进东京弘文学院学日语,1904年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大约一年半后的1906年3月从仙台医专退学,回到东京,一边在独逸语专修学校学德语,一边筹划他所说的“文艺运动”。读过《藤野先生》或《〈呐喊〉自序》等文的读者会知道,鲁迅“弃医从文”的选择发生在仙台医专,他回到东京后“从文”的具体行动是筹划出版《新生》杂志。为此,除了和周作人合作翻译了芬兰、美国、法国、波斯尼亚、波兰、俄国等国的16篇小说外,鲁迅还写了若干篇长文。《新生》计划失败,兄弟合译的16篇小说结集《域外小说集》两册出版(1909年3月、7月),鲁迅的文章则陆续发表在当时的留学生杂志《河南》上。其发表顺序为《人间之历史》(第一号,1907年12月)、《摩》(第二、三号,1908年2月、3月)、《科学史教篇》(第五号,1908年6月)、《文化偏至论》(第七号,1908年8月)、《裴彖飞诗论》(第七号,1908年8月)、《破恶声论》(第八号,1908年12月)。由此可知,《摩》是这些文章当中的一篇,分两期连载。该文发表时,鲁迅不满27周岁,是在结束留学的前一年。当然,那时还没有后来的文学家“鲁迅”这个名字,而只是留学生周树人。发表《摩》时,署名令飞。
《摩》的主题是“诗”,也就是文学,旨在阐述什么才是“诗”(文学)。也是上述六篇当中惟一论述文学的一篇。既然周树人要从事“文艺运动”,那么他所设想的这场运动的核心意向是否就包含在这篇文章当中?这是作者要详考《摩》的动机,也是书名里出现“探索鲁迅文学之渊源”的缘由之所在。
“摩罗”即“恶魔”之意,来自西语中的Satanic school即“恶魔派”一词,专指以拜伦和雪莱等人为代表攻击社会道德的诗人。顾名思义,“摩罗诗力说”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拿恶魔派的诗歌之力来说事。所谓“说”,即论述、阐述之意。《摩》在内容上分9个部分,第1-3为总论,第4-9之前半为关于各个诗人的个论,第9之后半为全篇结论。这是《摩》文内容上的总体构成。作者发现,《摩》在写作上的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运用各种材源来塑造“恶魔派诗人”们的形象,这种情形遍布《摩》文于诗人论述的核心部分。而这里所说的“材源”(即比较文学术语所称source),系指《摩》中行文之所据的明白无误的“他者的文章”。各章所取材源各不相同,文章种类也不一样,使用语言包括日语、英语和德语,大部分来自《摩》写作当时出版的单行本,也有杂志上登载的短文。因此,新版在学术成果上的首要贡献便是坐实了《摩》关于诗人论述的核心材源。兹列如下(原材源信息后括号内附中文译名):
1.木村鷹太郎『バイロン 文界之大魔王』,大學館,373頁,1902年(《拜伦 文界之大魔王》)
2.バイロン 木村鷹太郎訳『海賊』,尚友館,285頁,1905年(拜伦著《海盗》日译本)
3.濱田佳澄『シェレー』,民友社,173頁,1900年 (《雪莱》)
4.八杉貞利『詩宗プーシキン』,時代思潮社,280頁,1906年(《诗宗普希金》)
5.Kropotkin, Peter. Ideals and Realities in Russian Literature. 出版社不详,347pp. 1905.(克鲁泡特金《俄国文学的理想与现实》)
6.昇曙夢「レールモントフの遺墨」(集入『露西亜文学研究』,隆文館,1907年),原刊『太陽』12巻12号,1906年(《莱蒙托夫之遗墨》)
7.昇曙夢「露國詩人と其詩 六 レールモントフ」(集入『露西亜文学研究』,隆文館,1907年),原刊杂志不详。(《俄国诗人与其诗 六 莱蒙托夫》)
8.Brandes, Georg. Impression of Russia. (translated from the Danish by Samuel C.Eastman)London. Walter Scott. undated.(Preface 1889.)353pp.(勃兰兑斯《俄国印象记》)
9.Brandes, Georg. Poland. —a study of the land people and literature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310pp. 1903.(勃兰兑斯《波兰》)
10.Riedle, Frederick. A History of Hungarian Literature.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undated.(Preface 1906)293pp.(李德尔《匈牙利文学史》)
11.Petöfi, Alexander. Der Strick des Henkers. aus dem Ungarischen von Johann Kömödy. Leipzig. undated.127pp.(裴多菲《绞吏之绳》)
就材源关系而言,作者的结论很明确:上述材源“覆盖了《摩罗诗力说》各章的核心部分”(新版序言)。
在此基础上,作者在新版中完成的另一项工作是通过《摩》文本和材源的对照、验证,坐实了当年周树人对这些材源的使用方法,即,并非消化吸收了材源旨趣之后再将其用于自己的文章,而是以近乎引用的方式剪取材源,直接贴入自己的文章。而作者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探讨材源的运用方式,明确《摩》是以怎样的意图,塑造了怎样的诗人形象。除结论部分外,全书从第1章到第5章详细呈现了“意图”和材源构筑的“诗人形象”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这也正是全书的主体部分——其直接涉及并揭示当年周树人之文学观形成的渊源部分。
第三,作者在新版中还进一步调查并提供了各种材源背后的“文学上、历史上、政治上的事实与状况”,通过把《摩》这一“微观的记述位置”,摆在“材源以及材源背后的广袤的文学的、历史的、政治的宏观记述”这一坐标轴上加以确认,明确地把握到了《摩》记述当中潜在的“偏差与错位”。读者从中可知,那些“偏差与错位”有些是来自当时周树人的知识局限,有些则是他有意所为。
总之,作者通过旷日持久的繁杂作业,通过网罗材源,比较检对,去伪存真,追踪发掘以及广博而深入的背景调查,以新版材源考客观呈现出了写作《摩》时的周树人,不仅展现了他的写作方式、他的诗人心像和他的文学观,更深入地揭示了他与一个时代精神背景的密切关联。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置身于那个历史现场的等身大的周树人。
三
在材源考的中文版和新版之间,作者还有两部关于鲁迅的专著,一部是《鲁迅:在日本这一异文化环境中——从弘文学院入学到“退学”事件》(以下简称“异”。原题『魯迅 日本という異文化なかで――弘文学院入学から「退学」事件まで』,関西大学出版部,平成13〔2001〕年),另一部是《鲁迅 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以下简称“梦”。拙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11月。原题『魯迅 救亡の夢のゆくえ——悪魔派詩人論から「狂人日記」まで』,関西大学出版部,平成18〔2006〕年)。可以说,这两部专著都与作者的材源考工程密切相关。前者呈现的是刚到日本留学第一年的周树人,是对写作《摩》以前的作者成长史的追溯性调查;后者呈现的是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从事文艺运动的周树人,是在《摩》材源考及其各种延伸调查(例如德语、天演论、狂人、《希望》材源等)的基础上描述出来的作者“所得以理解的鲁迅”(《梦·致中国读者》)。这些著作的时间跨度和内容都鲜明地呈现着作者北冈正子的鲁迅研究特点。
首先,作者的鲁迅研究伴随着长期的鲁迅阅读史和思考史,是堪称为“鲁迅伴我行”的漫长人生经历当中的学术结果。据自述,作者出生于鲁迅逝世的那一年,1954年刚入大学中国文学科不久就在学习汉语的课堂上读到了鲁迅作品,同时参加了一个由社会各界青年自发组织的“鲁迅研究会”,从此便与鲁迅结下不解之缘,并左右了“此后的人生”(参见《鲁迅伴我行》《文艺报》,2011年9月16日第16版)。1960年代初,开始写作硕士论文,选题是《留学日本时代的鲁迅》,该论文首次涉及《摩罗诗力说》当中作为材源的“雪莱”问题,从此走上了前面谈到的“材源考”之路。就作者的鲁迅研究特征而言,或许从其阅读史和思考史当中不难窥知到一种更为潜在的东西,那就是真心以研究对象为师以及伴行始终的对师者的挚爱。
其次,是“问题意识”的清晰和独特。说到对鲁迅挚爱这一点,也许并非作者一人的特征,而是继竹内好之后日本战后一代有代表性的鲁迅研究者的共同特征。然而即便在时代所赋予的共性当中,作者的“问题意识”仍显得清晰和独特。作者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留学日本时代的鲁迅”。选择这个题目,或许与“原鲁迅”(片山智行语)的发现和共识有关。研究者们在鲁迅留学时代所做的一系列文章里看到了后来鲁迅的原型,而这显然又是个关系到“鲁迅从哪里来”的重大问题。然而,作者发现,对于这个“成为鲁迅之前”的“周树人”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成为鲁迅之后”的作品和文章乃至被阐释的“鲁迅形象”来构建的,并非出自对“周树人”史实的客观调查结果。于是,问题来了:是否可以暂时先放下后来的鲁迅,而只看留学时代的周树人到底是怎样的?这是一个“在作家鲁迅诞生以前的、还属于周树人文学活动的时期”(《梦·后记》)的研究对象的明确设定。
不论在哪本书中,作者都不忘记提醒,虽然使用“鲁迅”的名字展开记述和论述,但谈的还是“周树人”。可以说,明确将“周树人”区别于“鲁迅”(并非割裂)的问题意识和严谨的处理方式在作者是一贯的。而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以成为作家之后的“鲁迅”这一滤镜来看待此前的“周树人”,从而有效地确保了对处于成长期的“周树人”的客观对象化处理。仅以《异》的处理为例。这是“周树人在成为鲁迅之前、还尚未看到学医之路时期的传记,描述的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与日本这样一种异文化相遇,在茫茫之中逐渐坚定自己决心留学的最初一年的轨迹,是一个怀抱民族主义的青年周树人诞生之前的故事。其中既没有装点青春时日的恋爱出现,也没有冒险登场,既没有学医的周树人,也没有作家鲁迅。而这些都是他在很久以后的经历。这个时期,通过日本这一异文化的触媒,连续不断地诞生出了大批‘爱国青年’,而他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异·前言》)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周树人,作者又是怎样处理的呢?
这就是接下来要谈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所采取的实证研究的方法。实证研究重调查,靠材料说话,在实证的基础上构筑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这显然不同于以某种现成的鲁迅观为前提,省却史实的调查与验证,而仅仅去加以重新阐释的方法。相比之下,后一种方法在自说自话的当中似乎更容易“自圆其说”,或许不失为一条“捷径”,然而作者却拒绝了这种来自现成的“方便”。前有竹内好、周围有伊藤虎丸、丸山升那样的令人尊敬的学长与朋友,中国也更有关于鲁迅的定评,面对这些环绕着自己的诸多“鲁迅观”,作者坚持以实证科学为前提的鲁迅探索。这一探索决定了其必然要涉及的三个层面的工作,即对既往的鲁迅观加以验证,还原出那个存在于历史现场的“鲁迅”,揭示并具体呈现出“鲁迅”所具有的复杂而深广的思想文化背景。关于弘文学院时期的周树人,作者拒绝了在论据不清的情况下仅仅凭借想象的随意书写,而是“以资料重新构筑的状况和环境,将会不断呈现暗示隐身其中的主人公存在形态的场面”(《异·前言》);关于回到东京从事 “文艺运动”的周树人,作者“采取的方法是,并非只从鲁迅所留下的‘文艺运动’主张的言说中去读取,而是将其摆在一个综合的视野下,即在他所置身并形成思想的时间和空间以及他所接触到的异文化言说的状况中,对其内容加以考察”(《梦·前言》);而如上所述,材源考通过《摩》文本与材源对照,彻底还原了通过恶魔派诗人来建构自己文学观的处在历史现场的周树人。
很显然,在方法论上,这是一条不易“出成果”的困难的路径,作者数十年的调查经历,也足以说明了这一点。之所以会这样坚持,诚如作者在《梦·致中国读者》中所言:“我尽自己的可能调查相关史料,仔细筛选证据,强化论据,描述出了一个在此基础上我所得以理解的鲁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证研究就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更是研究者的一种态度。求真、求实的根本态度,才是实证研究的神髓。作者的鲁迅研究体现了这一点。
四
在材源考从中文版到新版的32年间,中日两国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鲁迅研究方面已经有了相当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互动,资料的发掘与共享,研究方法的借鉴和“问题意识”的沟通与共有都正在成为两国学界不断变化着的新常态。在这种状况下,材源考新版无疑会为两国学界在鲁迅研究和近代思想文化史的交流方面增添新的内容,带来新的互动契机。因此,最后还想再谈一下新版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我以为不妨从三个方面来看,即知识、方法和态度。
鲁迅留学日本从开始到结束,距今已相隔114年和107年。年代的久远,资料的匮乏,语际的障碍,对他国文化和历史的陌生,再加上研究对象传记资料的不充分,这些就构成了那个“留学日本时期的鲁迅”与今天的我们之间的距离。例如,这种隔膜首先在知识层面上就体现得最为明显。和30多年前相比,对鲁迅早期史实的了解和认知虽有了较大的改观,但至少以新版材源考所提供的知识为参照,便会轻易发现,现有的汉语圈当中关于“鲁迅”的知识储备还不足以相应地支撑理解留学时期的鲁迅所面对的知识环境,或者说,可以帮助人们去体察鲁迅当时所面对的那个“异文化”的知识平台还没有建立起来。最为直接的证明是在目前出版的包括《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6卷本;2005年18卷本)、《鲁迅年谱(1-4)》(北京鲁迅博物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以及后来的修订版)、《鲁迅年谱长编1881-1921(第1卷)》(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鲁迅大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等在内的鲁迅研究基本资料当中,新版材源考所涉及的那些文本事实、诗人传记、相关事项以及广泛的背景知识等,其绝大部分还都并未被收纳——同样的情形也体现在作者的另外两部著作中。然而,惟其如此,也就正是作者的贡献所在。包括材源考在内,作者的鲁迅研究,大大缩短了那个处于100多年前的历史场域里的“鲁迅”与今天的距离,为从现在接近那个时代清除了不少障碍。因此,首先在知识层面上,就很值得汉语圈的鲁迅研究参考和吸收。不过反过来说,新版材源考也的确不是面向一般读者,而是面向专业研究者的专著,没有一定程度的预备知识,恐怕是很难读下来的。
关于方法问题,前面已经谈过,在此不再赘言。可以说,作为实证研究的一个范例,新版材源考在方法上非常值得学习。有这样一项出色的成果摆在面前,再来讨论“实证”作为一种方法是否有效已经没什么意义。需要讨论的倒应该是如何看待通过严谨的实证过程所获得的结果,尤其当这种结果与某种既成印象、观念发生龃龉时,应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是否定结果,还是调整观念?例如出现在材源考当中的“鲁迅”,显然不是某些人观念当中的那个全知全能的“高大全”,而实则还是正处在学习过程和人格形成过程中的周树人,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学习、借鉴、模仿和吸收都是这一成长过程当中抹不掉的足迹,而后来的那个伟大的鲁迅便是这样一步步地内在形成的。正是当年的留学生周树人付出他人所未付出的努力,才有了《摩》,才有了后来的鲁迅。当然,实证研究的结果虽然是假说经过实证过程所获,但不会是完美或绝对,出现被质疑甚至被否定也完全正常。不过,对实证结果的质疑或否定,是要靠同样经过实证过程的结果来说话,否则便只是止于“评论”,等于说说而已。事实上,北冈先生的材源考当初也正经历过这样的所谓“试行错误”的过程。
当她写作拜伦那一章时,由于对关于拜伦的一个材源不了解,也由于不加过滤地引用了岩波版《鲁迅选集》的误译,受到中岛长文先生的严厉批评。但后者在批评的同时公布了自己调查清楚了的有关拜伦、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日语材源,这使北冈先生获益匪浅,欢呼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援军”,不仅收纳了“援军”提供的资料,也使此后的材源考做得更加严谨。这是很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实证研究方面的良性互动,也是鲁迅研究史上的一段佳话。有这样的互动,真正的实证研究才会发展起来。
然而,最后还想再重复一遍,归根结底,实证研究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态度。研究者的求真、求实的根本态度,才是实证研究的神髓。我以为,这或许是材源考带给学界的最大启示。
(作者系日本佛教大学教授、日本著名鲁迅研究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