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冈正子鲁迅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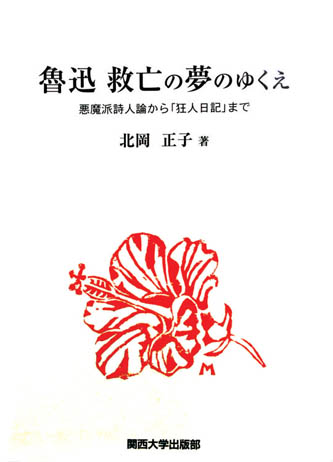
救亡之梦的去向 日文版

救亡之梦的去向 中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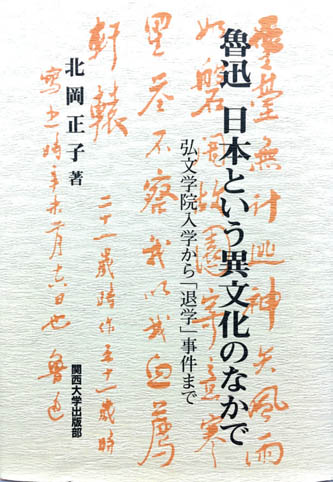
异文化环境 日文版
北冈正子的研究方法是:“将材料来源的文章脉络和鲁迅的文章脉络加以比较检查,弄清鲁迅文章的构成情况”,“从中领会鲁迅的意图”。她认为,如果仅把《摩罗诗力说》看作鲁迅的独创,反倒不能真正发现其独特性,关键是在考释鲁迅所依据的文献材料并施以实证研究之后,要细细分辨有所取和有所舍弃的情况,于这种取舍选择之中发现鲁迅的立场、视野和思想精神之根本。我们不能说北冈正子的这种研究方法已经臻于完善或穷尽其详了,但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的优秀范本,其许多结论和观点至今依然有其说服力和学术价值。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当年丸山升针对竹内好鲁迅论的“文学主义倾向”而提出的“假说→实证”方法,即依据第一手史料尽可能切近中国近现代史的事实并进行慎重细致之实证分析的科学方法。实际上,北冈正子也确实很好地传承了其受业导师东京大学中国文学专家小野忍、乃至丸山升等战后一代日本学人严谨的实证分析传统。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一般认为北冈正子的方法主要在于材料的考证,即文本事实和鲁迅文章与参考材料之间的事实关系,其实并不尽然。文献资料的挖掘和考辨固然是北冈正子的工作重心,但并没有仅仅止于此,她同时更注重材料考证辨析基础之上的文化比较、关系史分析和对鲁迅思想独特性的判断。换言之,材料考证和比较研究的有机结合才是北冈正子鲁迅研究的真正魅力所在。而如上所述,《摩罗诗力说》至少参考了日、英、德三种文字的著作文献,这一发现本身已然展示出下面这样一个事实∶鲁迅当时是处在多语言文本多文化关系的结构之中的。因此,如何在这个关系结构中确定鲁迅自身的位置和思想文化取向,就成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的关键所在。北冈正子有关鲁迅对拜伦、雪莱的认识与木村鹰太郎、滨田佳澄等的著译文本之间关系的分析,就达到了材料考证与比较研究有机结合的境界。
《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第五章讨论鲁迅与裴多菲的关系,这是北冈正子长期积累多方调查而最见其实证考据和比较研究功力的题目。《摩罗诗力说》第九节讨论裴多菲其人其诗,鲁迅当时主要参考了赖希和利特耳分别出版于1898年和1906年的《匈牙利文学史》,这从周作人的《旧书回想记》里可以找到线索。而北冈正子经过仔细比照鉴定,排除了当时鲁迅可能参照的多种文学史著作,最后确定是利特耳的《匈牙利文学史》成为鲁迅讨论裴多菲时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来源。该书第十四章论述裴多菲,前半部分叙述爱国诗人的一生,后半部分论述其诗歌和世界观。北冈正子注意到,鲁迅对此多有参照和引用,但并没有沿袭利特耳透过诗歌从有机联系中呈现诗人裴多菲整体形象的手法,而是“把几乎所有介绍裴多菲的篇幅让给裴多菲生活的顶点和不能不失败的革命重合的戏剧性场面”,舍弃掉诗人“以民间民谣为基础,在诗歌中开拓出独特境界的其他侧面,鲁迅笔下的裴多菲仅仅是个民族战士的形象”。经过这样一种仔细的甄别和比照程序之后,北冈正子得出如下结论:“从利特耳的《匈牙利文学史》,鲁迅了解到和革命兴衰密切联系的裴多菲戏剧性的一生,他那民族战士的方面。再有,继波兰诗人之后,从裴多菲身上吸取的精华是坚定不移的复仇心,这可以从《摩罗诗力说》对材料来源的处理方法上推论出来。”那么,鲁迅在讨论诗人裴多菲的时候,何以会对材料来源有如此这般的取舍选择呢?这种选择背后是否有更为深远的属于鲁迅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呢?对此,北冈正子最后给出深层文化思想上的思考:“鲁迅这时不在奴隶及其主人关系的主从位置转换中寻求救国之道,而在以人类精神进化为基调的新价值体系的创造中寻找出路,这种特异思想所光照的世界,与西欧以及追随西欧的后进国家的图式完全不同。……而且,鲁迅不只看到波兰(或匈牙利)和中国都是欧洲或亚洲的被压迫民族,还进而把东欧各被压迫民族所创立的文化和思想,与似乎领导世界的西欧所创立的东西视为不同的价值体系,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此说来,鲁迅思想的先驱意义也就变得更加清晰了。(《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第213页,何乃英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青年鲁迅立志走异路、别求新声于异域,但他留学7年所寻求到的并非日本一般所谓的富国强兵“脱亚入欧”式的现代化之路,也非清末“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式的洋务之途,而是在19世纪帝国主义时代受霸权欺凌的被压迫民族摩罗诗人的反抗思想中寻求到别样的解放道路,这无疑是理解后来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之鲁迅独特性的一个关键所在。而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当时历史状况的复杂,青年鲁迅这种特异的思想走向还远远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也因此,北冈正子的业绩和所提出的课题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和价值。当然,要完全揭开留日时期鲁迅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在结构,还要涉及到许多更复杂的方面,如鲁迅是在怎样一种历史语境下创作《摩罗诗力说》的,从最初的东京弘文学院、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到后来的东京德语专修学校,鲁迅如何在日本接受了近代教育并进而影响和推动了他立志从事“文艺运动”这一思想志向的产生,又与后来以《狂人日记》为发端的文学实践构成怎样一种关联,鲁迅早期的“立人”观念与进化论思想有何种关系?等等。这些也正是北冈正子大半生持之以恒不懈追寻的课题。
《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是北冈正子集1970年代中期以来的研究成果而编辑成书的论文集,旨在通过“材料来源”考证,探讨鲁迅留学时期从事“文艺运动”的情况,以及这场“失败”的运动与后来以《狂人日记》为发端的新文学实践之间内在的关联。讨论的方式依然是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可以视为作者大半生鲁迅研究的代表作。全书由四个章节和一个“补论”构成,其中第一章“有助于其‘文艺运动’的德语学习” 是考察鲁迅在弘文学院日语学习情况的《鲁迅——寄身于日本这一异文化之中》一书的续篇,沿用实证方法整理弃医从文后鲁迅在东京德语专修学校学习德文的状况。第二章“寄托于诗力的救亡之梦——恶魔派诗人论《摩罗诗力说》的构成”则是“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系列文章的缩写。我个人比较看重该书第三、四章以及“补论”的内容。北冈正子关于《摩罗诗力说》材料来源的考证,其卓越的研究成就已如上述,而第三章“产生理想之诗人像的现实——《摩罗诗力说》之‘人’的形成及其意义”则是材料考据基础上更为深入的思想分析和比较研究,对鲁迅早期“立人”思想的形成,包括体现其“立人”思想的诗人形象之建立,都有独特的观察和见解;第四章“成为‘狂人’的诗人”,则尝试建立起通过解读《狂人日记》来返观从留学生周树人到后来的作家鲁迅之演变过程的新视角;最后的补论“严复〈天演论〉——鲁迅‘人’之概念的一个前提”,则是对鲁迅“立人”思想之理论基础的进化论予以讨论的篇章,最能显示作者所达到的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深度。也由此,北冈正子得以确立起比较完整的有关早期鲁迅的阐释架构,在还原历史的同时重新构筑起青年鲁迅的形象。
在考察《摩罗诗力说》中体现了拥有“心声”的诗人形象之际,北冈正子注意到鲁迅笔下肯定性的人之形象往往是通过否定性人物的存在而构思和塑造起来的,或者可以认为,这是以鲁迅对本国历史和社会现实之否定性认识为媒介而创造出来的“人”之形象。也因此,鲁迅心目中的诗人形象与他所参照过的日、英、德文著作中有关摩罗诗人的叙述大不一样。与这种“认识方式”相关联,鲁迅接受来自严复《天演论》等的影响,其最主要的方面在于使他懂得了作为影响社会的要素,人的作用是如何重要,人乃是战胜天演之能动的行动者。
在此,北冈正子进而看到了鲁迅特有的以凝视否定性的负面来透视应该如此之正面的“相对化认识方式”。这种认识方式又导致鲁迅虽身处清末邹容、陈天华所代表的具有强烈民族自大倾向的重建“国民”之革命思潮中,却因为自“幻灯事件”后产生对“奴隶”状态的拒绝态度而形成了与一般革命家不同的“国民观”。鲁迅不能认同当时“国民”思潮中存在的那种民族自大倾向,他跨出统治与被统治或主人与奴隶的二元对立结构,试图在摩罗诗人的精神中发现“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式的超越了宰制与被宰制往复循环结构的真正独立的个人——国民。正因为如此,鲁迅没有像当时一般舆论那样以侥幸和优越的态度看待波兰、匈牙利等亡国亡种的悲惨,而是在这些被压迫民族的诗人之歌声中听到了并非奴隶的“人之声”。这构成了留日时期青年鲁迅思想精神的最大特征,同时这也是其接受进化论的基本立场和思想条件。
鲁迅曾深受影响的严复《天演论》,乃是于19世纪末帝国主义时代面临亡国亡种危机的几代中国知识者热心阅读深受震撼的一部书。然而,这部“英国赫胥黎造论 候官严复达旨”的包含诸多改写并插入译者个人观点之“案语”的特殊译著,它的哪些部分、何种观点影响到了当时志在寻找“立人”思想途径的青年鲁迅呢?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穿越由赫胥黎原著和严复并非直译的译文所构成的文本世界,辨析原著和译文之间的差异,确定严复特有的思想取向和译述“达旨”的终极目的。《鲁迅 救亡之梦的去向》中“补论”一章,北冈正子便依靠娴熟的实证方法和比较分析,对此给出了精彩的解答。
北冈正子认为:首先,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是以“宇宙过程”(cosmic process)和“伦理过程”( ethical process)的二元对立为全书的基本结构,强调在进化的所有阶段需不断抑制“宇宙过程”并将其转换成“伦理过程”才能开辟人类社会未来的道路。
就是说,社会的道德伦理进步在于不断同“宇宙过程”即外在于人类而无法彻底控制的“自然条件”进行斗争。但是,严复以“天行”和“人治”翻译“宇宙过程”和“伦理过程”两个概念,虽然保持了两者的二元结构,却未能充分体现赫胥黎这两个概念的对抗性内涵。《天演论》论述的核心在于如何于“天行”的支配之下实现“人治”,他所谓的“天行”与其说指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宇宙作用,不如说更意味着统御万物的“天”之功能。严复未能在赫胥黎所谓“伦理过程”的建构中发现人类社会实现变革的可能性,而是通过把“伦理过程”对“宇宙过程”的问题解读成“人”对“天”的关系,来探索改革现状的途径。其次,与上述误读相关联,在严复《天演论》中“天”之下为“人”,“人”之下则又设置了“民”一项,这样一种结构关系在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中是没有的。可以说,严复并没有理解赫胥黎所强调的“伦理过程”对人类社会的作用问题,因此他所说的“人”并非意味着赫胥黎所谓通过“伦理过程”得到恢复的社会构成的一员,而是对“民”施以教化并使社会和民族走向富强的能动的行动者。这反映了严复一贯主张的培养“民智民德民力”以挽救中国于危亡的思想。第三,故严复《天演论》乃是掺杂了强烈的救亡图存之个人主张的变革指南书,而非作为科学的宣传进化论的一般译著。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其主要部分便体现了《天演论》这种救亡图存之关键在于创造出能够教化于民的“人”之观点。换言之,把“人”视为挑战“天行”之恣意妄为的存在,进而将“民”置于“人”的教化之下——这一严复思想的核心,在《摩罗诗力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北冈正子的上述比较分析解决了鲁迅研究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通过将《摩罗诗力说》中的“立人”思想与严复《天演论》误译中的观点联系起来比较,确认鲁迅所接受的进化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或者赫胥黎伦理进化论,也与斯宾塞社会进化论无缘,而是更接近于严复在救亡图存意识下强调“使社会和民族走向富强的能动的行动者”之进化论。第二,这又和鲁迅当时的“认识方式”和思想立场密切相关,即以凝视否定性的负面来透视应该如此之正面的“相对化认识方式”和在主人与奴隶二元对立结构之外思考建立“真的人”之路的思想立场。这样的认识方式和思想立场,使鲁迅的进化论与赫胥黎的伦理进化论乃至尼采的“超人”进化论清晰地区别开来。第三,鲁迅的人类进化观是通过否定那种奴隶变成主人再君临奴隶之上的上下循环封闭之价值体系而建立起来的,从这个角度观之,又和严复的《天演论》有微妙的差异,这或者可以称之为鲁迅创造的鲁迅式进化论也未可知。
北冈正子的鲁迅研究已经得到了中日两国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丸山升早在1986年就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为了进一步深入鲁迅的内心世界,应该开辟更多的领域和方法。近年来北冈正子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她梳理鲁迅留学日本时期所写论文依据的材料,绵密地揭示出青年鲁迅有时用‘剪刀和浆糊’组合文章,以及即便如此,在他对剪刀和浆糊的使用方法中已经显示出自己很强的独立性”。而在我看来,北冈正子以材料考据为中心的实证研究和以多语言文本间的文化比较分析,作为独创的阐释架构实在是一种综合的历史还原法。她不仅把鲁迅研究的重心落实到文本层面,更将观察的视野和焦点拉回到鲁迅当时所身处的历史现场和文化语境上来。在这样一种脚踏实地的历史还原法之下所观察到的鲁迅,已经不期然地和我们多年来不断将其经典化甚至有些神化了的鲁迅像大不相同。北冈正子的研究有力地复原并重塑了一个普通留学生和勤奋摄取各种思想资源渐次形成志在通过文学以恢复古老民族之精神的青年鲁迅形象,不自觉中打破了以往人们对鲁迅的某种神化。
我们已知,198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曾提出“回到鲁迅本体”的口号,王富仁博士论文就一再强调要“回到鲁迅那里去”,意在摆脱多年来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从先在概念和固定思维模式出发观察鲁迅的方法。而北冈正子于同一时期在日本的研究成就客观上呼应了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中国学者的意识和要求,《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中文版的适时出版,也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
北冈正子的鲁迅研究有两大特征。一是执著于材料考据和比较研究,另一个是始终专注于留学时期的鲁迅特别是《摩罗诗力说》的问题。她那种“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与丸山升等为代表的一代日本学人一脉相承,同时在“早期鲁迅”这一研究领域中做出了别人无法替代的贡献。我们可以在北冈正子的学术研究中体会到一种特有的细致缜密而朴实无华的专业精神,并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1980年代以后日本鲁迅研究逐渐向更为科学的学术化专业化的转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