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意义,何苦要记得 ——美国电影中的朝鲜战争漫谈

《决不撤退》电影海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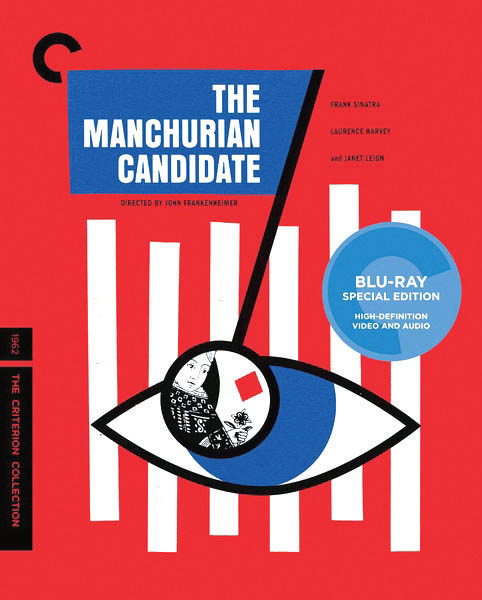
《满洲候选人》电影海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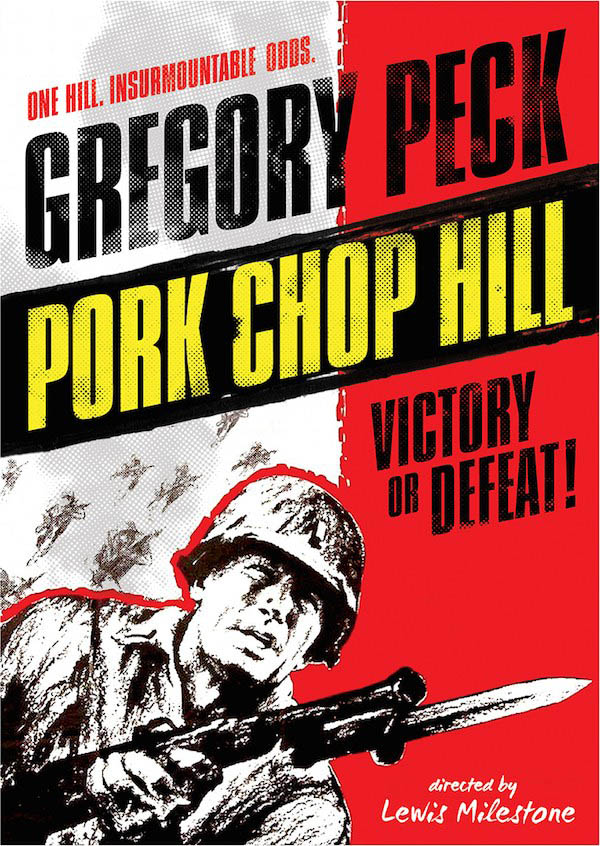
《猪排山》电影海报

《猪排山》电影剧照
在1952年的美国电影《决不撤退》中,18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吉米·麦克德米德坐在树下,正在为没能见上哥哥阵亡而悲恸失神,两个战友兴奋地跑过来告诉他,“战争就要结束了”,“我们能在家里过圣诞节了”。少年含泪的双眼顿时有了光彩。
镜头里的士兵们已经换上了厚实的冬装,大地一片萧索。影片中的时间是1950年的10月下旬,朝鲜北部山区已经很冷了。这几个年轻的士兵还不知道,早已悄悄跨过鸭绿江的数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在10月25日向他们发动进攻。他们企盼的凯旋被无限期地延后了,随之而来的是苦战、撤退和漫长的拉锯战。这一天,也在战后被我国设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而这场战争在美国却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不为人知的战争”,无论是战时、战后还是当下,都没什么公众关注度,直到1995年才在华盛顿设立了朝鲜战争纪念园。当年,他们把这场让美国先后投入200余万兵力、数万美国军人阵亡的战争称为“联合国警察行动”。
即使是爱极了大场面的电影工业,也从来懒得搭理这个被遗忘的战场,近70年来只有不到20部电影以朝鲜战争为背景,其中还包括不少以战争为背景的言情片,如《战地天使》(1953年)、《安城故事》(1955年)和《战地情焰》(1959年)。称得上战争片的可能还没有10部,除了开头提到的《决不撤退》,还有描绘海军航空兵的《战舰英雄》(1954年)、空军题材的《独孤里桥之役》(1955年)以及被称为美版《上甘岭》的《猪排山》(1959年)等等。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二战影片和越战影片要选出前十名,哪些影片能挤上名单都会有争议。
单纯以影片的质量和影响力而论,处于第一梯队的无疑是《满洲候选人》(1962年)和《陆军野战医院》(1970年),这两部片子频频出现在英美的各种官方和民间的影史榜单里。而从某种意义上,它们都不是朝鲜战争影片,只是借了个壳儿自说自话,应该分别划入冷战片和越战片的范围。《陆军野战医院》里的伤兵们与其说是从猪排山上抬下来的,不如说是溪山的幸存者。
《满洲候选人》又译作《谍影迷魂》,这个译名已经剧透得底儿掉了:战斗英雄雷蒙德·肖从朝鲜载誉归来,他以前的战友却惊悚地发现,肖被俘后曾被押送到东北某地,接受了前苏联专家的洗脑,进入了某种清醒的催眠状态,只需要启动预设的暗示信息,肖就会执行安排好的刺杀任务。
看到片名,有些人以为与满洲里有关,这是一个流布已久的误读。内蒙古的满洲里没有以任何形式出现在这部片子里,台词里讲得很清楚,主角接受洗脑的地点是“满洲”边界以北的敦化(Tunghwa),属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将“满洲”误读为满洲里,反映出今天的我们对这个词的陌生。很多人没察觉到,这是一种幸福。近年来,时不时有些声音跳出来问,抗美援朝在别人的土地上牺牲了那么多人,到底有多少意义。这个问题太大,不是电影能回答的,而作为集体意识(加上集体无意识)的共鸣容器,在所有的意义里,有一点是电影能告诉你的:我们的东北曾是他们眼中的“满洲”,现在不再是了。
1977年的《麦克阿瑟传》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演的是他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在朝鲜的作为。“回家过圣诞节”,这个朝鲜战争最冷的冷笑话,就是出自这位将军之口。导致他中途卷铺盖回国的一连串错误中,最严重的一个可能是他不相信中国会大规模参战,电影中他向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汇报说,根据他的情报,他“相信中国有30万军队部署在满洲”但不会过江作战,在与志愿军交战后,他空袭“满洲的空军基地”的申请遭到了拒绝。
从美国拍的朝鲜战争影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的语境中曾经不见东北,只有“满洲”。最初“满洲”指的是部族,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清末列强(尤其是日本)想蚕食、瓜分中国,别有用心地将东北称为“满洲”,意图从自我认同和文化传承上将其与中国割裂,这个词才成了一个显要的地缘政治名词。甲午战争以降数十年,“满洲”都被看作是这样一块可以而且正在分离出来、被外来势力争夺与“经营”的土地。
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美国的将军们当然判断捎带炸了炸鸭绿江对岸的不是什么大事。可他们错了。在1950年,他们炸的是中国的边界,而不是“满洲的边界”。李奇微将军回忆录里的这段文字曾被一再引用:“令人心寒的消息由冰天雪地的山脊传到东北方向”,“南朝鲜第6师第7团在遭到一支占绝对优势的中国部队打击后已掉头向南退却”。
李奇微回忆中,中国军队“像从地下钻出来一样”的首次亮相,在《决不撤退》中有生动细致的刻画。志愿军棉衣棉帽,手持步枪,人高马大,在冲锋号的指引下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美军。
这是美国电影中绝少见到的中国形象。一直以来,好莱坞的东方男性大约只有三个半刻板形象,几乎所有角色都可以套进去(即使是在好莱坞小有成就的成龙、李连杰也不例外),要么是《娇花溅血》(1915)里那个善良但是无力的大烟鬼,要么是插科打诨的陈查理,要么就是一次次妄图毁灭西方文明的黑帮头子傅满洲,还有半个是批发古老东方智慧的老者。虽然有善有恶,这些形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性魅力的缺失。简言之,一定要绝后。
从好莱坞崛起以来,贯穿整个黄金时代到冷战结束,绝大部分中国角色吃重的电影,都要将这种“污染”西方血统的可能性降至没有。这是19世纪后半期社会达尔文学说经由舞台留给好莱坞的“遗产”,《满洲候选人》也在这支脉络的传承上。被催眠的军人回忆说,他曾“看到那个中国家伙站在那儿,笑得像傅满洲”。
而好莱坞正面表现朝鲜战场的几部片子,可能是极少数刻画了中国人又不关心这件事的电影。这些中国男人只是军人,不是“黄祸”,是可以平等视之,甚至是让人畏惧的对手。与想象出来的傅满洲的那些小打小闹相比,志愿军的进攻当然可怕多了。在影片中,人还没到,嘹亮的冲锋号已经在美国士兵的眼中写满了仓皇不安。这样的场景,在美国的朝鲜战争电影中几乎成了一种“固定表达”。可这时,这些战争片没有谁关心根除“黄祸”的“大业”,它们更关心自己的士兵们怎么回家。
朝鲜战争一直被遗忘,在美国的公共视野中从来都没被真正记起过,原因之一也许是美国人在其中找不到意义。在二战中,美国人上下一心,在海上打败了来犯之敌日本,端了德国法西斯的老巢,这是确凿无疑的正义;越战让一代美国人痛彻心扉,年轻一代自下而上的反思和斗争,也是一种意义。而在朝鲜战场上,在为那些艰苦的战斗和消逝的生命寻找意义时,却只有茫然。
战争正在持续,宣传机器开动的马力应该是最充足的时候,《决不撤退》在价值观上也有无法弥合的裂痕,主角汉森上尉前半段始终处于被命令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里硬拽出来,不得不敷衍了事但求活着回来的情绪中,影片似乎是想表现他和吉米等人在战斗中激起勇气和热情,但在长津湖冷酷的冰雪中,这点热乎劲儿怎么看都差强人意,只找到了些微支撑:海军陆战队的荣誉感。
即使影片拍摄时战争还没结束,即使被打得很惨还有战友的伤亡,对敌人的敌意也是相当稀薄的。到了《猪排山》,同仇敌忾的氛围就荡然无存了。《猪排山》是一部远被低估的战争片,在技术上对一次战役的重现拳拳到肉,观众仿佛身临其境地看到,1953年4月16日“联合国军”与志愿军在石岘洞北山的战斗中,双方如何攻防,美方几个连队如何配合,对双方枪械和装备的展现也力求准确。
而这一切,是用公事公办中夹杂烦躁不安的调子拍出来的,没有荣誉,没有信念,只是一个不得不完成的麻烦任务。大唱高调的结尾像是被临时贴上去的,格里高利·派克饰演的克莱蒙中尉在等到援兵后,没有一丝喜悦,他的连队有八成士兵被这个不起眼的山包吞噬了,而这也是公事的一部分。
影片花了很多笔墨展现的一条线索,是有个黑人士兵屡次想当逃兵都被主角按住了,士兵直言,你应该去看看我在家乡的窝,我都不会为那破地方战死,我又为什么要为朝鲜战死。几笔就揭开了美国至今未愈的疮疤:自家事管不好,还一次次送士兵去打对他们没有意义的战争。最后这个士兵加入众人奋起战斗,只不过是在援兵久等不到的状况下不得已的背水一战。只是为了活下去,就像被囚禁的人为了食物而屈服一样。
上世纪50年代的好莱坞,热衷的是用亲情伦理大悲剧的各种俗套来复兴二战前的史诗巨片,古希腊罗马的传奇英雄们忙着在银幕上兜售民主、自由与博爱。这一年,《宾虚》大获成功,这股风潮几乎达到了巅峰。在1959年,《猪排山》是寂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