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安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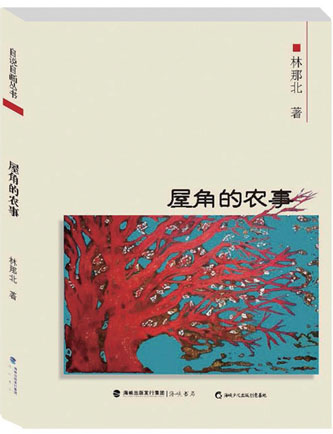
每一次收到林那北的作品,都会在心中翻卷起浪花,诸多感想澎湃而起,写点什么的想法却总在刚提笔又被各种借口填塞,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作罢。好在这并不消减她赠书的热情,仍以高质高量的生产堆积着我这个受赠者的窃喜。
这一次,当林那北把新作《屋角的农事》寄到单位,当看到她的一幅幅漆画插图,感受到她为了安顿那些植物所做的辛苦搬运,久违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已记不清是在哪个午后的暖阳下,还是某个夜晚的静谧中,我暗藏的心愿也这么破土而出了。
曾经务过农的人都害怕和泥土打交道,这一点,林那北的先生最清楚不过,他肯定不止一次地给太太讲述自己的知青生活。“我先生插过队,他对泥土的全部记忆与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担子,在满是水蝗的田里弯腰耘草连在一起,泥土浓缩了他青春期无法排泄的全部苦痛,看我忽然疯子般奋战于土中,既吃惊又不满。”还有,林那北在找寻泥土、为树挖坑的过程中遇到的各位农民工兄弟,都在不经意地传递着土地的苦难意味。“农村的孩子即使把天下所有自信都丧失一遍,在土地面前都仍然可以趾高气扬。一出生地就在眼前,一走路就与土滚到一块,然后想方设法竭尽全力试图甩掉土——恨是另一种亲密关系。”
然而,他人的经历并未动摇林那北问耕的意志,肩周炎、网球肘的困扰也没能阻止她种植的步伐。不禁想问:她如此执著,想向土地要什么?
如果生长在农家,农事绝不至于让她重燃热情。父亲是县文化单位的干部,母亲是人民教师,继续追溯,外祖父是台江下杭路藤椅店的老板。越陌生的东西越有距离感,“果多大?甜不甜?这些还全是迷。有迷的树和有迷的人一样,让人猜不透才更有魅力。”可见林那北对农活有了好奇心,愿意设问也乐于求解。那么,好奇心以外呢?
从何时起,我们的盘中餐失去了儿时的甘美,有时候也怀疑,是不是因为食物丰富了,人的味蕾变得刁钻了?直到人类疾病的种类也日渐“丰富”了,我们才意识到,没有化肥、没有防腐剂、没有残留农药、没有激素的蔬果正在走入历史、渐行渐远,还有一种叫做转基因的东西正浩浩荡荡地爬上千家万户的餐桌。超市上那些有着精致包装的大米小米黄豆绿豆,但凡印个“有机食品”的字样,都以数倍甚至更高的价格傲视着来来往往的顾客。儿时的林那北,和亿万人民共同经历过“衣裳陈旧,饭菜潦草,日子寒酸”的年代。后来的林那北,衣无忧、食未必无忧,否则,她不会从种植的第一天起,“就做出不沾农药的重大承诺”,和邻居们相互赠送有机肥时,“像提贵重礼品般送上门去,所获得的欢迎程度超过了送一袋米或一包海鲜”。显然,林那北拒绝接受超市、菜市场的蔬菜,把大把的时间和心思花在种植上——一个整天和文字打交道的人,时不时化身为农民,这何尝不是一种寓意深刻的行为艺术。
《屋角的农事》语言活泼俏皮,畅快淋漓地展现林那北幽默爽利的风格。但也不难发现,文字后面,有双敏锐的双眼,正或冷或暖,传递着向往、观照着现实。
在新居安装空调时发现已经空巢的鸟窝,林那北联想到人类的拆迁悲剧:“但愿此时鸟们都没宅在窝里,为了寻找爱情与粮食它们应该正满世界撒野,于是没有目睹家被强拆的这一幕,否则就埋下仇恨的种子了。但即便如此,当它们傍晚倦归之时,见满目疮痍,不也一样忧伤悲愤吗?”为了平复想象出来的“仇恨”和“悲愤”,她又试图让安装空调的师傅“用木板在墙外架起一个笼子”,“类似于建一个补偿性的拆迁安置房”……读到这些,莞尔的瞬间又突然感伤莫名。
植物是沉默的生命,林那北却希望它们平安喜乐:买菜苗时,把和高壮的苗并排的几株一起买走,为的是“要走一起走,甘苦共受,荣辱同当”,她坚信,“百年修得同船渡”同样适于植物;“花不鄙视草的粗野,草不嫉妒花的文雅,和谐相处,从不内斗”;无花果“盆子底部戳有透水的洞”,“它如果有本事,根完全可以从洞口穿过,伸到土里,与芒果树根幽会”;对植物呈现出“绝不舍得排泄出来造成污染”的姿态,她断言其是“更高一级的生物”,为“它们却坚持把生杀之权谦让给比自己低一等的人类”而愤愤不平……在这样的文字中穿行,你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作家质疑和反思:人类何以高高在上、妄自尊大?只因上可去九天揽月,下可抵深海擒龙?不断的掠夺和拓展恰恰暴露了生存中沉沉浮浮的不安。对这个星球而言,人类已经不是通过排泄制造污染那么简单了,还有呢?是更多的破坏,还有呢?是更多的失去。
无疑,《屋角的农事》流露出了林那北对土地的眷恋、对城市扩张的隐忧,也替身居高楼却丧失土地的人们表达了种种渴望。对卖掉老家房子又买城里电梯房的油漆工,她好几次动了劝劝的念头,“把城里的房退掉或卖了,重返老家,不过终于还是没有开口”。就像那些飘摇在树上的叶子,要从树干汲取营养,就得牢牢攀附于枝头,在社会变迁中随波逐流的人们,即使看得清形势也未必有能力左右自己的命运吧?
林那北不是躬耕南阳伺机出山的诸葛亮,也不是倦怠官场追求自由的陶渊明,种植是她对抗浊世的手段之一,这种行为当然瓦解不了越来越强势的钢筋水泥,更不能阻止这世界此起彼伏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的纷争。她搬运泥土,播撒种子,让瓜果长成它们原本的样子,让那些本来隔山隔水的植物、以为一辈子不可能的相逢变成了可能,和读者分享她的付出和喜悦,跟着她体悟那些“关于生命的隐秘荣光”。她的所为,说到底,不过是坚守一隅、从心所愿地进行铺排、施以关怀,这是她的理想世界:彼此珍惜,互不伤害。
我深信,时间和林那北是两不相辜负的伙伴。她当过记者,写过专栏,后来又当小说编辑、当总编、当社长,在纸质阅读江河日下的网络时代,她不仅撑起了杂志社的运营,还和她的精兵强将们将新媒体为我所用,建立数个微信公众平台,把创刊30周年、35周年作家手迹展、书画展搞得红红火火,为一个刊物赚足了人气。写作和种植以外,漆画是她为自己经营的另一番风景,那些或缤纷、或浓烈的色彩,明快地表达着她对美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由此,乐于尝试新鲜事物的林那北,也在不断的收获中把自己活成春天的模样,这是她对自己最好的安顿,这样的处世态度,也影响着越来越多的相熟和不相熟的朋友。
繁忙的农事不仅改变了她的生活节奏,也在改变着她的先生、著名评论家南帆。以《小院子的春华秋实》为序,南帆坦言:“有一天我遵命提一根塑料管浇水,水流汩汩穿过手心浸入泥土,突然感到生活慢了下来。透过丝瓜藤蔓的间隙,我看到了天空中悠然的白云和飞鸟。一阵风习习吹过,空气中隐含着另一种芬芳”。林那北在后记《滚一身泥巴》中回顾种植的经历,也感慨“原来我们可以跟世界建立起如此相濡以沫的关系,你温柔以待,它们便倾力以报”。序言和后记,仿佛是这对文坛佳偶间的一次深情对视和相互欣赏。从开始种植到作品问世,一年时间,刚好是春华秋实的一个轮回,宛如岁月的河流,逝者仍如斯,但它又是如此从容、清澈,照见了飘过的白云,也留下了飞鸟的倒影。
想起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当我的锄头叮当地打在石头上,音乐之声传到了树林和天空中,我的劳役有了这样的伴奏,立刻产生了无法计量的收获”。
愿那些失去土地的人们,不要失去安顿身心的能力。
(《屋角的农事》,林那北著,海峡书局2015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