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自律与他律及文学批评范式刍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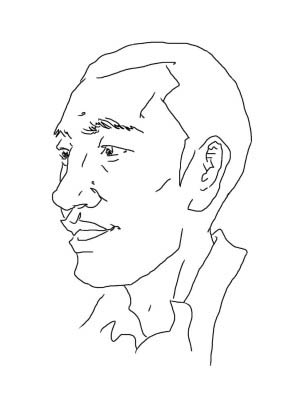
主持人语
“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在中国当下文学语境下提出并不意味着我们选择了文学批评史上的“新批评”或者“形式主义”批评,而是强调“以文学的方式谈论文学”。将文学研究偷换成语言研究当然完全不是我们说的“回到文学本体”谈论文学。强调一切文学研究从文本出发,“出发”自然也不是最后的“终点”。正因为如此,我同意郭宝亮教授所说:“从文本中来,到文化中去的文体学的方式,属于一种新的批评范式。这种新范式决定了它与传统的纯形式批评不同。”事实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往往多的是一“去”千里,不知所“来”的伪装成“文化批评”及其他打着文学批评幌子的文学批评。至于“从文本中来”所来的“文本”,确实也如郭宝亮教授所言存在着丰富的“多层次”,甚至比三层还要多。再有,郭宝亮教授吁请建立中国“文体学”的批评范式。“范式”从哪儿来?当然从丰富的文学批评现场和实践中来。但中国文学研究的现实却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越来越归属为两个彼此不相关的大学学科建制的“专业”。

先从文本中来,到文化中去的文体学的方式,属于一种新的批评范式。这种新范式决定了它与传统的纯形式批评不同。文体学是一种综合性的批评方法,它要求使用者应具有较高的理论知识储备。实践证明这种范式和方法是可行的,有前景的。
“回到文学本体”是一个颇有魅惑力的话题。然而,何为“文学本体”?是不是就是文学自身?也应该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我不打算从前人众多的文学理论阐发中来说明这个问题,单从两个常识性的命题说起,大家想必就可见一斑了。
文学的自律与他律
人们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在反映论的文学本体论看来,语言只是一种工具,是用语言这种工具来塑造形象反映生活的。然而,20世纪以来的“语言论转向”则摒弃了语言作为工具的说法,认为语言就是本体。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以及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我的语言的限度意味着我的世界的限度”等,都在强调语言作为本体的意义。语言就是世界的真正边界,“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从这一意义上说,语言(形式)就是文学的本体,这与新批评理论家兰色姆所强调的文学本体论有一定的相似性。兰色姆认为,文学本体就是文学作品本身。而韦勒克则认为,本体论即作品的“存在样式”。这都说明,文学本体就是文学自身,即文学的语言、结构、叙述方式、时空特点等形式的构成要素。由此可见,文学本体即是语言(形式)本体。
但是不要忘记还有另一个命题: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既可以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理解,也可以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理解。写人和人的生存状况肯定是文学的基本含义。既然“语言是存在的家”,那么,语言本身自然要携带着人类存在的密码,呈现在文本中,“文学是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这说明文学还有一个本体:生存(生命)本体。如果说文学的语言(形式)本体属于文学自身的内在规律,它自足自洽,有着不可替代的自我运行机制,因而属于自律的范畴;那么,文学的生存(生命)本体,则与人类社会的各种法则息息相关,它不应该是文学语言自身的产物,而是依赖于人类生存的,因而属于他律的范畴,文学只不过是审美地呈现了这种人类的生存景观而已。至此,我们可以说,文学就在自律与他律之间,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
基于文学性的批评才是有效的
由是观之,文学批评的“正当”途径,首先应该从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即“怎么写”开始。我觉得,文学作品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艺术价值,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在艺术上有它的独异性,有它对文学史的特殊贡献。批评家要以自己专业的眼光发现、挖掘文学作品独具的艺术价值,寻找其语言、结构、叙述方式乃至文体诸多方面的问题。正像巴赫金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复调”,热拉尔·热奈特发现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的叙述话语,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及其诗之本质的揭示,罗兰·巴尔特对巴尔扎克小说《萨拉辛》近乎超级细读的《S/Z》……这些先贤们的批评实践难道不能给我们深长的启发吗?
回过头来检视我们的批评,不能说全部,起码也是相当多的批评,习惯从思想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方面阐释作品,特别是评论性的文字,更属于一种即兴阅读感受式的批评。这种批评的套路一般是从作品阅读中找到一种主题含蕴,说了一大堆,很少触及作品的形式肌质,有时在文章的末尾也顺带说说艺术特点,但太随意、太主观,缺少专业性和理论性。甚至有的人今天说东,明天说西,没有持续的理论立场。我觉得,批评家的理论立场或曰理论素养是非常重要的,那些大师级的批评家,他们不仅仅是批评家,而且是哲学家、美学家、理论家,因而他们的文字才是有根的。好的批评文章应该是鲜活灵动与理论有根性的结合,说出一部作品艺术形式上的特点比说出这部作品思想上的特点要难得多,它不仅需要特别的艺术感悟力,而且还要有极高的理论概括力。基于文学性的批评才是有效的批评,这对于文学批评的从业者而言,无疑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文体不是单纯的语言体式
然而,回到文学自身难道就足够了吗?我觉得,回到文学自身只是批评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没有这个文学自身,文学批评就不算是真正的“文学”批评。但是文学自身也即它的存在样式——语言形式并不是纯粹的形式,而是“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语),它必然折射出作家的心理气质、文化精神。不同的作家在语言形式的选择和运用上肯定各有不同。从一个作家独异的与众不同的语言形式、叙述方式、结构特征等形式构架——肌质中,寻找作家独特的心理密码与文化精神,才是由语言(形式)走向生存(内容)的正确路径。这种方法也可以叫做文体学的方法。
文体学在西方一直属于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文学也是唯形式主义批评家喜欢的方式。韦勒克、沃伦就曾说过:“文体学的纯文学和审美的效用把它限制在一件或一组文学作品中,对这些文学作品将从其审美的功能与意义方面加以描述。只有当这些审美兴趣成为中心议题时,文体学才能成为文学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它将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部分,因为只有文体学的方法才能界定一件文学作品的特质。”(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显然,韦勒克、沃伦在此所说的文体学和文体,正是新批评派批评家们所推崇的形式主义美学的一种方法。
然而,我觉得,如果把文体学研究只限定在文学的形式层面,那只是文学的一部分,还不能界定文学的全部特质,文学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如果说,文学的自律性正是文学的形式要素,而他律性则是文学的内容要素,文学作为有机体,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说形式实际上也是在说内容,故此,我赞同童庆炳先生给文体所下的定义,“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这个概念实质上包含着三个层次:文体首先体现为外在的物质化的以语言学为核心的文本体式,其中包括语言样式、叙述方式、隐喻和象征系统、功能模式以及风格特征种种;第二个层次则是通过文本体式折射出来的作家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与精神结构,它与作家的个性心理紧密相连;第三个层次则与作家所在的时代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相联系,体现的是支撑文体的复杂文化场域。而后两个层次就是一定的话语秩序。由此可见,文体绝不是单纯的语言体式,而是包含着多种复杂因素的话语秩序。实质上,童庆炳先生对文体和文体学的改造,就是要摒弃形式与内容二分的固有偏见,试图打通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界限,使文学研究真正成为“文学”的研究,而不是单纯的“形式”研究或“文化”研究。因此,这样的文体研究,首先是要回到文本,回到文本的形式上来,但还要不止步于文本形式,而是要到文化中去。
建构新的批评范式
从文本中来,到文化中去的文体学的方式,属于一种新的批评范式。这决定了它与传统的纯形式批评不同。这种范式也要吸收一切形式批评方法的营养,比如传统的修辞批评、新批评的细读、经典叙述学的话语分析、传统文体学的“前景化(突出)”方法等,但它更侧重于对形式背后所折射出的文化要素的挖掘。因此,它更青睐于像英伽登的现象学美学和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的方法。
罗曼·英伽登的现象学美学认为文学作品是一种意向性的存在,这种存在既有实在客体的性质又有观念客体的性质,从而建立了由物质、形式、存在三方面构成的综合本体论。进而,英伽登提出了文学艺术作品的结构层次说,他把文学艺术作品分为4个层次:语音现象层、意义单位层、再现的客体层、图式化观像层。4个层次各有独特性又有机地联系成一个整体。英伽登的美学思想对于建构新的批评范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巴赫金的超语言学方法,对于我们同样意义重大。这种超出语言学的方法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对话关系。对话关系是人们实际生活中的交际语言,而这种语言正是索绪尔所摒弃的言语。言语的对话交际性质,决定了它所具有的社会事件的性质。活生生的言语都处于一种具体的语境之中,而每一种语言都以其独有的语调而存在,“语调即评价”,这说明,言语(话语)研究不同于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其特有的文化价值是不应该被忽略的。一般而言,语言都具有表意功能,表现功能和文化功能这三种主要功能,传统语言学研究往往止步于前两个功能,而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研究则更加关注文化功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巴赫金对对话关系中的双声语现象进行了分析,比如对《穷人》中的杰符什金语言风格的分析,他从其语言的阻塞和语言的中断,发现杰符什金的语言“是怯懦的、惶愧的、察言观色的语言,同时还带着极力克制的挑战”。“杰符什金几乎每说一句话,都要回望一眼那不在场的谈话对方”。接下来,巴赫金分析了这种“察言观色语言”的结构方式。这就是在杰符什金的语言中“折射”出他人语言。正是这种“折射”改变了原来的语气和句法,使得主人公语言出现“语气的断续、句法的破碎、种种重复和解释,还有冗赘”,而这种语言现象不是修辞方式,而是包含着深广文化内涵的,那就是“在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中,渗入了他人对他的认识;在主人公的自我表述中,嵌入了他人议论他的话”。在这里,巴赫金改变了传统语言学研究的方向,进而寻找到一种全新的研究天地,对我们进行文体学研究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当然,要建构文体学的新的批评范式,还要借鉴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乃至人类学等理论方法,在广取杂借的基础上形成文体学的自身的理论框架。实际上,文体学也是一种综合性的批评方法,它要求使用者应具有较高的理论知识储备。我在对王蒙、张炜、刘震云等的研究和批评实践中,曾尝试这种文体学的方法并获具了一定的经验教训。实践证明这种范式和方法是可行的,有前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