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洛斯拉夫·潘科夫《西方以东》:在神话与现实之间

米洛斯拉夫·潘科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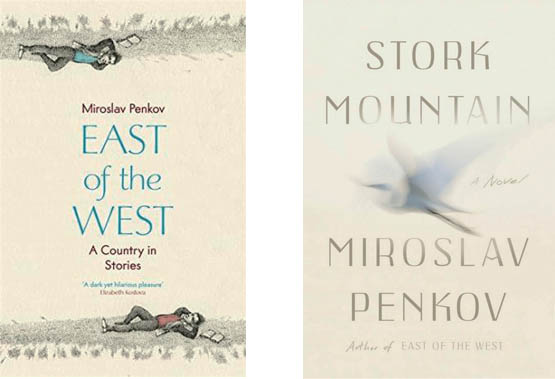
《西方以东:故事里的国家》 英文版 《鹳雀山》英文版
过去的两年间,美国文学艺术界最吸引眼球的事件之一无过于“劳力士创艺推荐资助计划(2014-2015)”的遴选——结果是迈克尔·翁达杰与米洛斯拉夫·潘科夫配对——“门徒”在“座师”悉心指点下将要在规定时间内拿出像样的长篇,才算不辜负名表的赞助。作为文学导师的翁达杰是斯里兰卡裔的加拿大作家(1992 年凭《英国病人》勇夺布克奖),名满天下;而作为弟子的潘科夫,又是何许人也?
米洛斯拉夫·潘科夫(Miroslav Penkov)1982年出生于保加利亚。2001年赴美留学,先在阿肯色大学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2005),后来又获得文学硕士学位(2009)。目前他任教于北德克萨斯大学,是创意写作课程助理教授,同时兼任《美国文学评论》杂志编辑。
迄今为止,凭借处女作《西方以东:故事里的国家》(2011),潘科夫在美国国内及国际文坛获得的奖项已多达十余项,其中包括2008年的“尤多拉·韦尔蒂小说奖”和“全美最佳短篇小说奖”;2011年的“欧·亨利短篇小说奖”以及2012年的“BBC国际短篇小说”大奖。这部包括《马其顿》《西方以东》《购买列宁》等故事的小说集具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在战争、饥荒、婚恋、流亡等背景下人们对爱与自由的向往。这些故事从不同侧面刻画出背负沉重历史、又不得不在严酷现实中苦苦挣扎的当代保加利亚人的生存状况——透过他们,读者能真正了解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和未来。潘科夫通过描写个人遭遇,展示保加利亚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震荡,因为他深信:假如读者将这些互补的故事当作整体来阅读,就像拼图游戏里的小碎片一样叠加在一起,便能够展现一幅关于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完整的历史画卷。
神话元素是潘科夫小说创作中的一大亮点。据他本人在访谈中介绍,他自幼便习惯于在母亲的怀中聆听古老的巴尔干神话传说和英雄传奇。后来在埃伦·吉尔克里斯特教授的鼓励下开始尝试文学创作,模仿斯蒂芬·金,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都是一些假模假式的美国故事……很快地,我意识到这些胡乱编造出的美国故事全都是垃圾”。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他所选的西方历史课上,当教授请他帮忙翻译一部保加利亚古代文献时,那些古老的歌谣和神话刹那间从他的心底喷涌而出:为什么要去仿效别人?为什么不能写写那些传奇与神话?现实中的保加利亚人在近代饱受耻辱,或许千年的神话和历史能够重塑他们的民族自信与自豪感?
根据小说家在《自序》中概述的保加利亚简史:该国立国于公元681年,此后约600年间它一直雄踞欧洲。后来,像希腊、塞尔维亚以及其他巴尔干国家(在土耳其语当中“巴尔干”的意思是“丛林的山脉”)一样,被奥斯曼帝国攻陷。此后直到1878年它才获得自由,重新确立它自己的历史。通过缔结条约结束纷争、而且疆域得以拓展的保加利亚令群雄大为恐慌,因此,虎视眈眈的强邻开始利用各种手段蚕食保加利亚领土。20世纪初,巴尔干战争爆发,保加利亚第一次获得机会夺回它在历次战争中失去的土地;但紧接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加利亚不幸与德国结盟,结果不仅失去胜利,也失去更多土地。20世纪中期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肃反”的旗号下,国家陷入动荡和恐慌,人民流离失所,被迫向西方逃亡。
“时至今日,(仍)有上百万保加利亚人旅居异乡,我见过无数父母(包括我自己的)鼓励他们的孩子离开家,去外面追求更好的生活:我见过保加利亚人改名换姓,抛弃他们的母语,接受新的信仰、新的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忘记他们是从何而来……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要铭记(过去)。”或者用他自己在访谈时所说——写作,只有通过神话历史与现实相互交融、相互辉映的写作,他才能够重返(精神)故乡。
收录在《西方以东》里的故事,有的讲述在奥斯曼统治之下以及在与土耳其争取独立的战斗中保加利亚人的生存状况;有的讲述巴尔干战争及其灾难性的影响;还有的讲述政权更迭之际保加利亚基督徒和穆斯林的遭遇。最后还有故事向读者展示当今的现实:大批保加利亚年轻人出走,去向西方寻求更加美好的生活。本书最后一篇,堪称最具神话色彩也是最具现代性的《德芙什美》则带领读者直线穿越时空——但偶尔也有曲折迂回——并折射当下,“如同一条蛇咬掉它自己的尾巴”。
书中最能全面展示整部小说集共同历史背景的是标题小说《西方以东》。在小说开头,潘科夫虚构了类似柏林墙的一道河流,将原本是整体的村庄分隔成两半:西部属塞尔维亚,东部仍属保加利亚,沿河都有实枪荷弹的卫兵巡逻把守。但人为的阻隔并不能完全断绝绵延数百年的两岸亲友来往。主人公诺思便常常偷渡到对岸和心爱的表妹薇拉一同玩耍,而他的姐姐也日夜梦想能偷渡去西方。不久,诺思亲眼目睹姐姐为自由付出生命的代价。母亲在哀恸中逝去,父亲终日与酒为伴。薇拉也远走贝尔格莱德。病重的父亲拒绝治疗——父亲的去世,也斩断了诺思与这片土地最后一丝联系。他满怀希望,向着薇拉飞奔而去。然而,当他历尽艰难见到昔日恋人时,发现她已另嫁他人。他梦想的生活到底在哪里?他该何去何从?小说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了悬想。
显然,小说标题中的西方决不单单是地理方位,而更像是一个隐喻、一个政治符号:在村民们眼里,它象征着繁荣富庶和民主自由。所以小说中年轻的一辈,无论薇拉、诺思,还是姐姐,都会拼命向着西方逃亡——因为他们对自己脚下属于东方的这片土地根本不抱任何希望:它承载的只是长达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奴役和屈辱。这样看来,长大成人的男孩诺思日后投奔美国,追寻他自由的梦想,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但问题是:美国或西方,真的是东方人理想中的乐土和天堂?
《德芙什美》对上述问题给出了明确答案。小说中的保加利亚人彩票中奖,获得全家去美国定居的绿卡。然而到美国不久,妻子就带着未成年的女儿跟当地的美国医生公然同居。他找不到工作,被迫接受医生的友谊,以维系每周一次探视女儿的机会。对他而言,美国不是天堂,更像是地狱;他身处其间,饱受屈辱,有时竟感到生不如死。每周一次见面,给女儿讲述故乡的神话传说,就成了他生命惟一的慰藉和全部的意义。
相比而言,《购买列宁》给出的答案虽不十分明确,但无疑更发人深省。小说中的祖父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他计划建立一座革命历史博物馆,用于收藏领袖塑像以及革命时期的各种文物。孙儿去美国留学;在电话中,祖父时常教诲,要他远离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就像要远离狂犬病一样。为增强他的免疫力,祖父开出的药方是列宁著作。通过阅读这些书信,原本以为已经告别革命的孙儿居然发现他与列宁的共通之处。此前他分析祖父的“愚忠”只是由于植根于人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缺乏独立人格的盲从和害怕被集体排斥和抛弃的恐慌,现在才明白原来信念或信仰对一个人是如此重要。祖父的信仰虽然看起来未免荒谬可笑,但他自己对西方民主自由的迷恋,又何尝没有可笑的成分?小说结尾,孙儿在易贝网上竞拍到躺在水晶棺里的列宁遗体,将它捐献给即将落成的革命博物馆。
论及他的文风,潘科夫本人在小说《烟草婚礼》(2008)的序言中曾谈到在他的家乡,人们迷信缪斯女神,认为文学创作只要灵感附体,便能一挥而就;后来到了美国,进了创意写作班,才明白一切好的作品都需要经过反复修改和锤炼。尤其是短篇小说,虽不能说字字珠玑,但绝容不得任何拖沓冗赘——简洁的风格成为他孜孜以求的目标,评论家也认为他酷似以简洁明快文风见长的伯纳德·马拉默德。
就《西方以东》而言,潘科夫的行文清晰朴素、优雅节制而不失幽默,堪称大家风范。一个场景,一种思想,别的作家可能要通过大段叙述才能充分表达,而在他的笔下,往往只需寥寥数语。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幽默不仅体现出潘科夫的艺术才华,更体现出他对人物心理的准确把握。当然,这种幽默更多时候是基于作家对人性的洞察:如主人公奉命去劝说一位移情别恋的男人,他的内心其实很纠结:“当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爱胜过亲生儿子的时候,还能对这个男人说什么?”——潘科夫一再宣称:凡是与爱关涉之处,人们都应当多几分理解与宽容。毫无疑问,他所指的理解与宽容显然不只是个人情感,更是长期专制高压政治下的自由与宽容——这一思想,在以保加利亚历史与当代种族歧视为主题的近作《血汗钱》(2013)中也有所体现。
2016年3月,受劳力士项目资助的潘科夫小说《鹳雀山》(Stork Mountain)如期推出。小说的主题仍是保加利亚海外游子对故国的眷恋:他从美国返回故乡位于希腊和土耳其交界处的神秘山林,寻觅离家出走的祖父的踪迹,并邂逅一位天真率直、富于传奇色彩的穆斯林少女——不顾世俗的阻挡,抛却一切宗教及文化偏见,二人坠入爱河——神话与现实在小说家笔下再次如此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小说出版后广受好评,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