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类型”文学创作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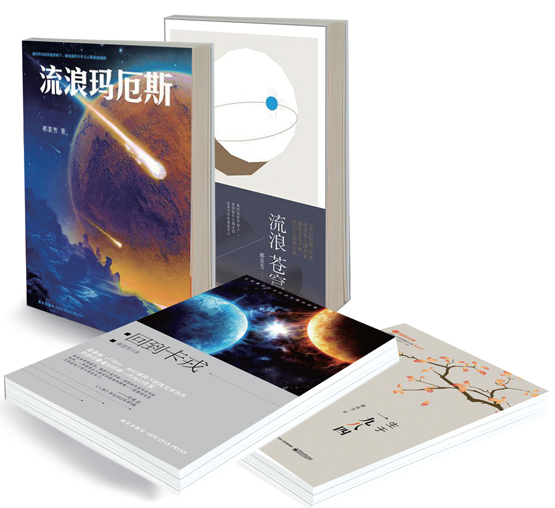
郝景芳在作品中不断探讨的一个主题就是现实与幻想的相处之道,不喜欢作品被贴上主流或科幻文学标签的她尝试的是一种“无类型”文学书写,在她笔下,文学类型的界限不再那么明显,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界限也不复存在,而按照这些故事的不同风格,又可以被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幻想及浪漫化现实,现实化幻想。
2015年,刘慈欣凭借《三体》成为获得世界科幻最高奖项雨果奖的第一位中国人,人们纷纷猜测授予中国人的第二座雨果奖奖杯会何时出现。没想到,仅仅时隔一年,“80后”作家郝景芳就凭借自己的短篇小说《北京折叠》入围并获得雨果奖,成为中国第一位拿雨果奖的女作家。
郝景芳生于1984年,天津人,在清华大学完成了本硕博教育,相继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清华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专业从理论物理转向天体物理最后再到应用经济学,目前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工作,同时,她也是一位两岁女孩的母亲。
很难想象郝景芳如何掌握工作、家庭和写作之间的平衡,她本人给出的答案是“这世界上可能并不存在真的平衡,你最多只能做到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切换”。习惯于做一件事时专注于其中的郝景芳对写作的态度也是一样,每天清晨5点起床写作,利用上班前的两三个小时在无干扰状态下进行文学创作。
对于郝景芳来说,写作是她惟一的追求,她并不在意自己的写作是什么类型,只写她想写的东西。因此,我们所看到的郝景芳作品,是模糊了类型边界的、难以被归类的作品,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无类型”小说。
郝景芳创作概述
早在中学时代,郝景芳就已在写作方面崭露头角,除开在诸种作文选集中发表作文外,她还获得了2002年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不过,按照郝景芳自己的说法,她的写作生涯起始于2006年。那时她写作了“大量风格类型不够鲜明的小说:介于纯文学和科幻文学之间,被二者同时拒绝”,曾经很在意作品能否发表的她在被拒绝多了后也就不那么在乎了,一方面按照杂志要求写符合杂志风格的小说,一方面继续写作自己想写的“无类型”小说。2007年她发表了两篇作品《祖母家的夏天》和《谷神的飞翔》,前者荣获银河奖读者提名奖,后者则在发表前便已获首届九州奖暨第二届“原创之星”征文大赛一等奖,对于一位刚刚踏上写作之路的作者来说,这是相当喜人的成绩。之后,郝景芳陆续在《科幻世界》《萌芽》《新幻界》等刊物上发表了《星潮·皇帝的风帆》《光速飞行》《冰淇淋城堡》《看不见的星球》等若干短篇小说,并于2011年9月出版她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星旅人》。除了之前发表的小说以外,《星旅人》还收录了许多郝景芳那段时间没能发表的作品,可以说是她早期创作的一个小结。这个时期的郝景芳作品中笼罩着浪漫主义色彩,仿佛悠然漂浮于空中的彩色幻梦,淡化情节,追求美感,多有童话意味,发表平台也以《萌芽》为主。
郝景芳的长篇科幻小说《流浪玛厄斯》《回到卡戎》同样创作于这个时期,并分别于2011年4月和2012年8月出版。短篇小说《谷神的飞翔》是这一系列长篇的序曲,短篇中的人物朗宁和汉斯也在长篇中再度登场。在这部作品中,郝景芳尝试对火星和地球两种不同制度进行探讨,对制度中人的思考进行探究。她的长篇作品与短篇作品一样追求语言本身的美和情节的美,这种美是淡然的、不动声色的。在长篇中,郝景芳有机会加入大段思辨,关于历史、哲学,对人类文明诸多思考结晶的引用。
对于历史和文明的熟知同样体现于郝景芳的旅游随笔《时光里的欧洲》中,这本出版于2012年4月的书是她与爱人按照历史顺序走遍不同历史阶段文明中心的产物,将欧洲历史娓娓道来,贯彻了她一贯淡然优美的语言风格。尽管体裁不同,郝景芳的旅游随笔和小说拥有同样的气质风貌,即便是叙述大事件、描述危难关头,依旧保有从容不迫的气度。
2013年以后发表的郝景芳作品较以往风格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发表平台也更多转向《科幻世界》《文艺风赏》等,那种青春的、幻梦式的叙述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沉稳扎实的叙述。2013年第4期《科幻世界》刊登的《阿房宫》《最后一个勇敢的人》《孤单病房》三篇是郝景芳在小说类型化上的尝试,她有意加入了更多情节,开始直面描述一些不那么美的东西,并不是说郝景芳的早期作品中就没有触及丑陋的话题,只是早期的郝景芳在写到丑陋的话题时仍旧用一种唯美的笔调来描述,好像在伤疤之上飘过。这一时期的郝景芳放下了那种对于美的执著,开始直面揭开的伤疤,将视线聚焦于有欲念的普通人之上,这种对于普通人的关注也延续到了这一时期她的其他作品之上,包括《北京折叠》。
郝景芳在2016年出版了四本新书:收录较多早期作品的短篇小说集《去远方》《星旅人》的篇目有较大重合;收录较多近期作品的短篇小说集《孤独深处》在语言叙事上更为成熟,类型特征更为明显,情节也更鲜明;长篇科幻小说《流浪苍穹》即《流浪玛厄斯》和《回到卡戎》的集合;非自传的“自传体小说”《生于一九八四》是一部现实作品,写一个普通女孩的成长经历。郝景芳表示自己想写的一直是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关心的是在不同的社会中的人如何生活,这也是她未来写作的核心。
浪漫化的幻想现实
郝景芳曾在《“类型”之惑》中谈到自己对于类型的看法,她将小说空间分为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认为纯文学或者主流文学关心现实空间,也表达现实空间,而科幻或者奇幻文学关心虚拟空间,也表达虚拟空间,她自己的作品则关心现实空间,却表达虚拟空间,“以现实中不存在的因素讲述一些事件,然而表达的内容却与现实息息相关”。事实上,郝景芳在作品中不断探讨的一个主题就是现实与幻想的相处之道,不喜欢作品被贴上主流或科幻文学标签的她尝试的是一种“无类型”文学书写,在她笔下,文学类型的界限不再那么明显,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界限也不复存在,而按照这些故事的不同风格,又可以被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幻想及浪漫化现实,现实化幻想。
郝景芳的许多早期作品是纯然的幻想或浪漫化现实,浪漫气息无处不在,不乏童话寓言风格的作品,如科学童话《我们的房子会衰变》和科幻童话《看不见的星球》,呈现出一种漂浮于空中的彩色幻梦感,对美有着坚持不懈的追求,相应淡化了情节。浪漫化现实的典型则是《城堡》和《去远方》,拥有自己才能看见的冰淇淋城堡的女孩,坐火车弄丢旅伴又踏遍世界寻找旅伴的女孩,她们认为真实存在的东西在旁人看来只是幻想。
这一时期的郝景芳,已经开始在科幻作品中尝试探讨现实问题,尽管作品的语言风格仍带着浪漫色彩,与后期的现实化幻想有很大不同,她的火星系列是典型代表。《谷神的飞翔》中,为了火星发展,童话小镇一般的谷神星必须牺牲,《流浪玛厄斯》和《回到卡戎》中,自由和理想不得不在制度前让步。美好的幻想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矛盾,难以调和。
郝景芳这一时期许多作品的主角都在寻求一种与现实的相处之道,《城堡》中拥有冰淇淋城堡的“我”,《祖母的夏天》中处于人生迷茫期的少年,《流浪玛厄斯》和《回到卡戎》中亲历了地球和火星两种制度无法适应的洛盈……他们是普通人,却与大多数普通人有那么些不同,或者有着非同一般的幻想,或者有着非同一般的经历,或者仅仅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性格,但他们又不够特别,不足以改变世界,所以他们只能在这个世界中格格不入,寻求着自己与现实的相处之道。最终,往往他们并不会融入这个世界的既有制度,相反,制度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小窗,他们得以保有自己的初心继续生活下去。
现实化的幻想
到了后期,郝景芳作品中的这种浪漫主义色彩逐渐褪去,更多书写现实,但她并不满足于书写单纯的现实来表达现实问题,而是选择幻想作品来表达。《深山疗养院》描述了一种可以让非清醒状态的人做出自动应答的技术,大多数笔墨却落在了青年教师面临的压力之上;《生死域》试图用一种“科学”的角度来解释生死,重点却是主角生前未了的尘缘;《北京折叠》中构想了三层空间,描绘了都市折叠的景象,目的还是为了展现现实中的阶级分化。这些作品是科幻小说,又与传统的科幻小说不大一样,展现现实的焦虑、现实的问题,通过幻想拷问如何与现实相处,故我称之为现实化幻想。
在郝景芳的现实化幻想书写中,青年教师韩知、刚刚死去的“他”、第三空间的垃圾分类工老刀,他们与英雄相去甚远,也从未妄图改变世界,而是将精力集中于解决个人层面的问题上。这一时期,郝景芳也有更加偏向传统类型的科幻小说,但主角同样是普通人,《阿房宫》中的阿达正是因为拥有普通人的欲望才会被秦始皇利用,《最后一个勇敢的人》中的仓库人正是因为普通才留下了推翻制度的火种。普通人可能没有伟大的理想、宏伟的前程,但他们有普通人的欲念,能做普通人才能做到的事情。与早期幻想及浪漫化现实中的主角相比,郝景芳现实化幻想中的主角从一开始就是融入于既有世界和制度之中的,他们有烦恼,却不去怀疑身边的世界。
《北京折叠》的中文版最初在2014年2月发表于《文艺风赏·闪电宫》,英文版经由刘宇昆翻译后在2015年发表于电子杂志《Uncanny》上,曾获第五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短篇小说银奖、首届中国科幻坐标奖短篇类冠军、2016雨果奖最佳短中篇。作品中,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分别代表了上流社会、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他们在地理上共享一座城市,却在时间上互不干预,每当一个空间的人们醒来工作生活,另两个空间就被折叠入地表,其中的人也陷入沉眠。第三空间的垃圾分类工老刀为了给养女凑幼儿园学费,接受了第二空间一位学生的委托,铤而走险进入第一空间送信,他见到了北京折叠的恢弘景象,也见到了三层空间背后的不公。
老刀是典型的普通人主角,他以垃圾分类为生,过着平凡生活,在此之前没有进入过第二和第三空间。他的烦恼也是普通人的烦恼:养女的就学问题。他在目睹了三层空间的不公后,他没有就此消沉怀疑生活的意义,而是回到他本来的生活之中,继续烦恼他原来的烦恼。这不像是幻想小说主角会做的,却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最有可能采取的选择。郝景芳说她感兴趣的描写对象是普通人,“因为普通人是非常复杂的,他集善恶于一身,他有很多自私的地方,但是他又有很多的恻隐之心,所以我会想要写作为混杂体的普通人,是如何在这样的大背景中起到作用的”。
郝景芳认为《北京折叠》不是一篇幻想小说,她写的也根本不是一个不存在的未来。这恰恰是她现实化幻想的魅力,以现实的另一种可能性来更有针对性地反映她所看到的现实。对于读者们的批评,郝景芳坦然接受,承认《北京折叠》作为一个短篇没有充分展开,给人一种匆匆滑过无法深入的感觉。这是她构想的长篇的第一章,完整的长篇在她的写作计划之中,只是她仍在等待某种准备好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