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香港故事”的本土色彩

陶 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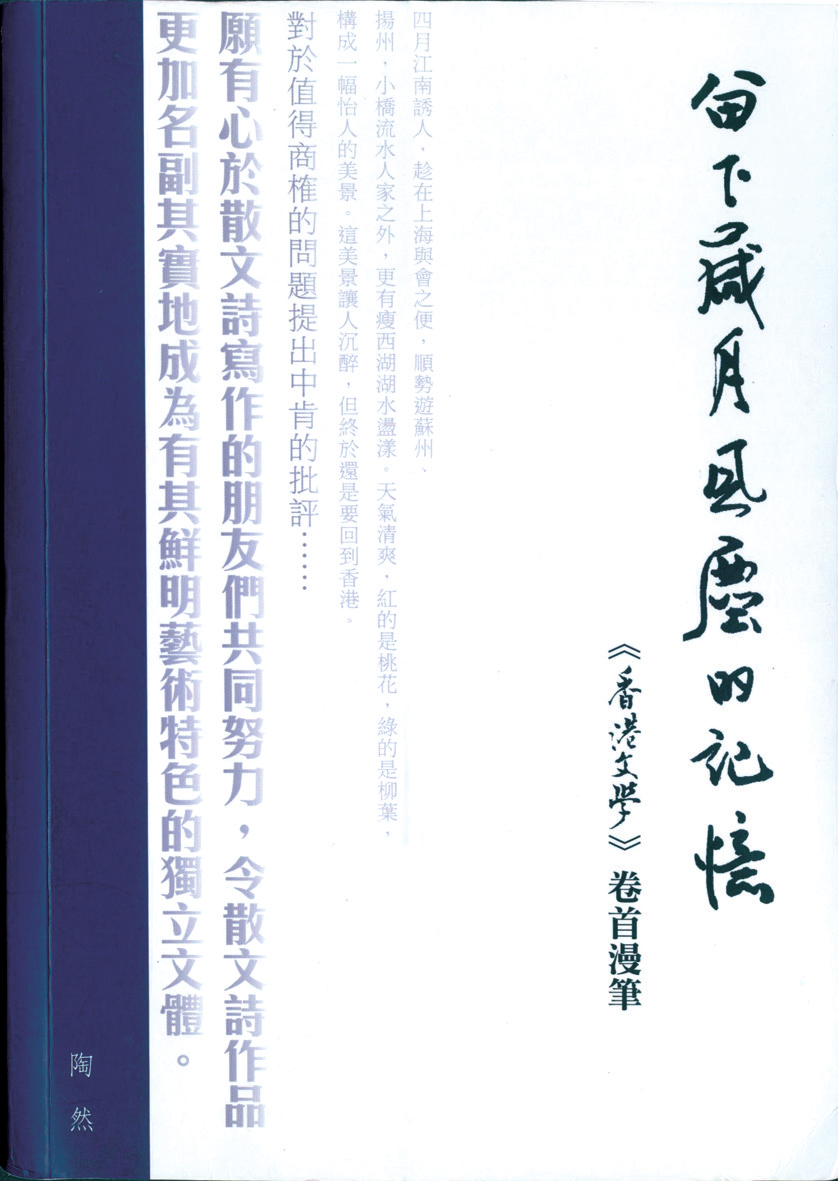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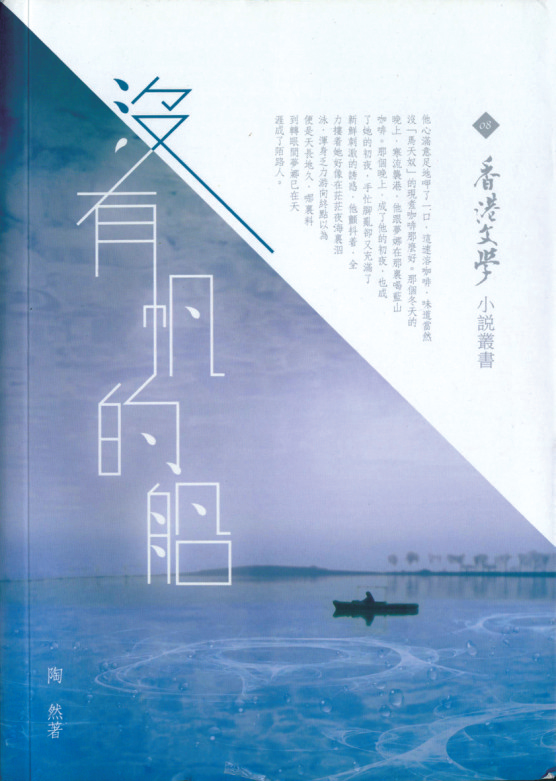
香港是一个非常广东又十分国际的都市。如何讲好香港故事,对作家来说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所谓“香港故事”,就是以港人港事为题材的作品。
在香港当代作家中,刘以鬯、舒巷城、西西,都是讲香港故事的好手,陶然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他在上世纪发表的《天平》,乍看起来是老一套的三角恋爱故事,其实,作品用爱情写出香港人面临九七回归所做出的种种不同选择。与政治冷感的作家不同,陶然能呼应时代的脉搏,迅捷地捕捉港人在移民问题上的彷徨心态,足见他细说香港故事的非凡才华。
陶然是“南来作家”,可他在香港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南来”的色彩在不断褪化,本土色彩却在直线上升。总之,他已成了地道的香港作家。《窥》写高楼大厦林立的香港,众多老百姓却在蜗居,这篇小说从题材到表现手法,均可视为典型的港式小说。新作《没有帆的船》中的同名小说所出现的旺角、赤柱、中环、大屿山、九龙香格里拉酒店、“邓肇坚运动场”,还有八卦杂志、“大家乐”、六合彩……这都是香港有特色的地名和通俗文化现象。陶然作品中还经常出现香港特有的词汇或方言,增强了作品的本土性及其地域色彩。
如果只满足于写香港景观或用粤语,那还不算什么,陶然的深刻之处,在于通过景观以及人物的自白或心态,表现港人特有的生活感受,以观照当下香港的社会状态。“香港地,不是人人都能做老板,说到底,还是打工的多,(做了老板)你就是人上人了。”《没有帆的船》中这段人物独白,表现了许多香港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可要实现这一点谈何容易。小说除了写普通人想改变打工地位外,还写出他们无不在追求至高的物质享受。陶然这样写三位青年人的不同心态:
第一个是肥仔叶西门。我的奋斗目标,是一部靓车和一所房子!
第二个是高佬李志坚。我的奋斗目标,是一部“奔驰”和在半山区的花园洋房!
第三个是靓女葛丽丝。我的奋斗目标,是做老板,做王中之王,后中之后!
这些人的人生目标与当时乃至现在香港社会的潮流仍十分吻合。陶然的作品从精神深处体现了把住“半山区”当作最高享受的生活追求——这种挣钱发财然后享受生活的典型港人心态。
在创作中不重复别人是起码要求,不重复自己则较难做到。陶然每出一本书,均有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他的《没有帆的船》不以事情发生经过为着墨点(如美琪如何被奸杀,只是一语带过),而是由汤炳麟与后母邝玉霞的矛盾展开,通过经营餐厅扭亏增盈,做到了地产公司的顶级经纪,去表现香港青年人获得财富的生活经验。“这是商业社会,一切也都以金钱来做衡量的法码了。”另一位总经理则说:“记住,这是竞争的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你们不要跟我讲什么斯文,我要看到的只是成绩!”作者不再沉默,描写和表现出一种港人认可的弱肉强食的竞争哲学,对香港社会的本质作出深刻的揭露与思考,使得香港人赚钱时不顾斯文这种只做不说的心态,得以呈现在公众面前。
在上世纪70年代,香港作家就开始走着一条不同于内地文学的道路。他们不写或很少写长城、长江、黄河、塞北,而注意自己身边的景物:写香江,写英皇道,写尖沙咀,写维多利亚公园。和这些作家不同的是,陶然还注意到港人意识上的转变,即在认同中国的同时也不忘自己的港人身份。号称“绿印作家”的陶然,早已完成了从移民到“落地生根”的转化过程。陶然着重表现香港社会的特征:“香港人什么都是快节奏,做事像打仗一样,午饭吃速食,搭车最好不是计程车就是地铁,而许多年青人看的也是速食文化,看了就丢的那种书。”此外,陶然描绘香港高楼耸立、霓灯闪烁及随之而来的灯红酒绿的生活多了一层投入感,如《没有帆的船》中提到的“半山区”的花园洋房以及疯涨的房价,《今天不回家》里花天酒地的生活,无不表现出现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反映出许多香港商人物质富有而精神贫困的矛盾状态。在《走出迷墙》中,陶然不满足于表现日常经验,而是在视野扩展上下功夫。至于《主权转移》,从标题到内容均不限于个人感受,而是努力从“主权转移”的“故事”或“心事”的个人感受中,深化作品的思想性。《旋转舞台》也不满足于只描写芸芸众生挣钱的艰辛和苦难。即使是从真人真事中取材的处女作《冬夜》,陶然也没有写成新闻报道,而是通过想象和虚构,展示出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深入体察。
《与你同行》的主人公范烟桥曾感叹:“都30岁的人了,大学毕了业,却一下子就给命运抛到这人生地不熟的香港,以前所有的资历好像给拦腰斩去,不获社会的承认,我变成一无所有了。关系嘛,也是一个也没有,我好像是半路出家的人,又好像是无根之人。”这无疑有作者的影子,或者简直是陶然的夫子自道。原籍广东蕉岭的陶然,出生于印尼万隆,少年时又到大陆上中学、上大学,毕业后到香港工作。这种“无根”的复杂经历,使陶然在谈到故乡时,难免会表现出空洞和失语。但在描写香港生活的小说中,陶然显然是把“东方明珠”当作第二故乡。像长篇《追寻》写香港人如何看待生活,如何追求理想,不同生活经历的知识分子如何选择自己的奋斗目标,无不是作者心目中“故乡”人物的所思所想。在其他作品中,陶然或写香港社会的世态炎凉,或写人性的冷漠,均是把香港作为自己的精神避风港。陶然由原先对外来侨生归国升学等的书写转向写香港的商战,体现出在现代文明挤压下,人性如何遭致蜕变。写这种题材时,陶然的心情爱恨交加:既热爱香港又十分厌恶这里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丑恶现实。他写老船民全家遭殃的《夜海》,写没有掌握稿件生杀大权的普通编辑无奈的《贺稿》,表现的都是香港的庶民生活。为香港底层工作者代言的陶然,一直在向贫富不均、弱肉强食的社会提出抗议。正如他自己所说:“开始的时候,我初来乍到香港,在新鲜感之外,由于自身在北京所受的教育,也由于本身在茫茫人海中彷徨无助的处境,心中难免不平衡,对于香港的种种社会现象便带着批判眼光。”
香港文学界曾多次讨论俗文学与雅文学的分界,一直没有结论,但有一个共识:俗文学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转变为雅文学,雅文学也可以用通俗的形式表现。陶然“香港故事”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故事新编”,这种新编很好回答了雅与俗如何互补的问题。他这类跨越时空的新编故事,有通俗的成分,但又不是大路货,而本质上是高雅,或者说是雅俗的结合。如《美人关》取材于《三国演义》中关羽的故事,但写关羽“投胎”香港,遭受警察查其身份所受到的困扰,读之不能不赞叹作品构思的巧妙和想象力的丰富。这是现代与古典的融合、雅与俗的汇合。
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是陶然讲述“香港故事”的重要手段。他写香港并不是在炫耀本土的优越性,而是对“这个世界,只要能够赚到钱就行,读那么多书干什么”一类本土经验的反思和批判。《身份确认》《法庭上》暴露了代表正义、威严的香港警察和执法部门如何假公济私、欺压市民的丑态。《没有帆的船》记叙了现代青年过分迷信金钱而形成的家庭关系冷漠的现象,从理性角度描写了商场如战场的激烈竞争状态,剖析了作家对当下香港社会拼命赚钱拼命享受的人生哲学的深入思考。
可贵的是,陶然并不满足于批判现实主义手法,他还辅之于双城拼接的时空结构、倒错的心理时间叙述以及意识流技巧。其中《黑旋风卷上太平山》就用了荒诞派和魔幻手法。陶然还以内心独白和对话梳理了传统道德与流行时尚的关系,生动展现出人性之恶和难以扭转不良社会风气的无力感。如《一万元》没有停留在对收银员简慕贞多收一万元的原因探寻上,而是以此揭露香港有些人“笑贫不笑娼”的人生观。陶然有的作品营造了喜剧氛围,更多则是以喜剧开场而以悲剧结束,如《岁月如歌》通篇贯穿着悲与喜的交汇;《平安夜》所描写的悲剧,却以喜剧的形式出现。还有《一万元》写主人公“未入洞房,先进牢房”,喜剧顷刻间变悲剧。众所周知,商战小说是一种类型文学,弄不好容易类型化、公式化,但陶然的商战题材小说,故事情节不重复,人物形象不雷同,呈现出类型化叙事与个性化描写相互交织的特征。
近年来,陶然无论是写微型小说、短篇小说,还是写中长篇,均以写实兼浪漫的笔法,写出了香港众多市民的传奇人生,凸现了他在本土化乃至经典化写作道路上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