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文本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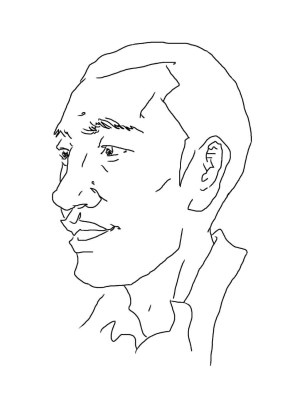
何 平
主持人语
“文学批评”的实践性,既是文体意义上的从阅读批评对象到审美感知、价值判断,再到以一定的修辞、语体、形式等“撰写一篇文学批评”的整个过程,当然也应该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编辑、出版和翻译等文学行为。翻译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它的最终实现是通过不同语言之间转译的完成程度来考量的。转译的过程包含着丰富的文学批评“细节”,对这些丰富“细节”的观察往往可以看出译者的转译是不是在“文学本体”之上达成的。
近年来,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越来越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被译介到海外,我们期待海外也能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当海外学者对这些作品进行本体性批评时,他们所针对的文本是译文,而译文又是建立在译者对原文文本的选择、细读和阐释之上的。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进行的文本批评就显得尤为重要。许诗焱在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兼任中国文学英译期刊Chinese Arts & Letters(《中华人文》)编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积极参与者。许诗焱以葛浩文的翻译个案的过程及其过程中的丰富“细节”为例,讨论译者在原文文本的选择、译文文本的生成、译本的传播与接受等环节中所进行的文本批评,使我们得以进入葛浩文的翻译现场。这样的研究也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许诗焱
译者在翻译时要对文本进行细读。如果对原文的文体、语言、形式、结构等缺乏基本的审美感受、体验和判断,译文就不可能成功。从原文文本的选择到译文文本的生成,再到译本的传播与接受,译者的文本批评其实体现在翻译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该重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文本批评,选择最值得翻译的作品,构建最好的译文,并对译本进行有效的推介,让中国文学在“走出去”的道路上呈现出最佳的状态,被更加“文学地”加以对待。
作为一个外语专业的人,看到“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这个话题,我首先想到的是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译者在翻译时要对文本进行细读。如果译者对原文文本的文体、语言、形式、结构等构成要素缺乏基本的审美感受、体验和判断,将这个文本转换为译文文本就不可能成功。而且,文本的语言转换还只是狭义的翻译过程,如果我们讨论广义的翻译过程,从原文文本的选择到译文文本的生成,再到译本的传播与接受,译者的文本批评其实体现在翻译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本文就以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的葛浩文为例,看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进行的文本批评。
作品选择
葛浩文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交流也远不如现在这么便捷,作为“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孤独领地里的独行者”,葛浩文的很多翻译项目是他在大量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基础上的主动选择。正如他自己在访谈中多次强调的那样,“每次我发现一部令人兴奋的著作,都忍不住有一种要把它翻译成英语的冲动。”这种“冲动”体现了译者对文本的感知和鉴赏,本身就是一种文本批评。
最能体现葛浩文文本批评功力的,莫过于他对萧红作品的研究与翻译。葛浩文70年代初在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专业攻读博士学位时偶然读到了萧红的《呼兰河传》,立即被这
个文本所吸引。当时萧红在美国几乎无人知晓,“不但我所认识的同行朋友们只有一两位曾经读过《呼兰河传》,连夏公(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也只提过一次萧红的名字”。葛浩文在完成关于萧红的博士论文之后,开始了对萧红作品的翻译。1979年,他所翻译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他又陆续翻译了萧红的其他作品。英国汉学家詹纳(William Jenner)曾说,“葛浩文把萧红带到西方世界,功不可没。”
刘绍铭在为葛浩文的《弄斧集》所写的序言中进一步指出,“葛浩文在推介萧红作品给她同胞所做的努力,也一样功不可没。”1976年,基于他的博士论文的专著《萧红》(Hsiao Hung)一书在波士顿出版。1979年,该书的中文版在香港出版,葛浩文在序言中写到:“我不敢说是我‘发现’了萧红的天分与重要性——那是鲁迅和其他人的功劳,不过,如果这本书能够进一步激起大家对她的生平、文学创作和她在现代中国文学上所扮演角色的兴趣,我的一切努力就都有了代价。”1985年,《萧红评传》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研究萧红文学创作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的萧红研究热潮,改写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随着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莫言作品译者的葛浩文也声名鹊起,很多人认为他的翻译对于莫言获奖功不可没,但他自己认为:“当初翻译莫言作品时,莫言还没像现在这么出名,而我也只是有个中国名字的美国学者,但是我和莫言彼此欣赏。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有点小骄傲,并非为我翻译得好而骄傲,而是为我在20多年前就发现了他这样的优秀作家而骄傲。”其实,在莫言获奖之前,葛浩文所翻译的《狼图腾》《河岸》《玉米》已将姜戎、苏童、毕飞宇送上了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的领奖台,而这些作品在他看来都是他必须翻译的“好小说”:“凡是中国作家出版的,我认为是好小说的,就会翻译出来,让作品走向世界。”
文本细读
就狭义的翻译过程而言,对原文的文本细读是翻译的第一步,译者对于原文文本的阐释是翻译的基础。但是,译者对文本的细读和阐释通常都隐藏在译本的背后,大家所能看到的只是最终出版的译本,不论是对于文学研究还是对于翻译研究来说,这都是一个遗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石江山(Jonathan Stalling)经过近3年的筹备,于2015年1月在俄克拉荷马大学设立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目前收藏葛浩文、顾彬和叶维廉的大量翻译资料,包括手稿、信件、出版合同以及翻译过程中所利用的参考材料等(馆藏资料均由翻译家本人提供,大多数资料从未公开发表或出版)。我于2015年赴美访学,有幸成为该档案馆的第一位访问学者,在对葛浩文翻译资料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他对于原文文本细读的材料。
比如,葛浩文与林丽君合作翻译《推拿》的过程中与作者毕飞宇之间的邮件。他们向毕飞宇提出了131个问题。有些是关于原文中难以理解的词语,如 “扒家”、“有数”、“活络”、“苦钱”、“冲钱”等,大部分都是他们不熟悉的地方方言;还有一些是关于成语的用法,如“含英咀华”、“天花乱坠”等,他们发现成语字典中的解释与原文语境不符,所以向作者咨询。他们在文本细读中对词语确切意义的探讨和挖掘,体现了他们对于文本语言特色的敏锐感知。除此之外,他们还对原文文本中的逻辑关系提出质疑:“都红的手像手,一共有五个手指。沙复明一根一根地抚摸,沙复明很快就从都红的手上有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新发现,都红的手有四个手指缝”——这是故意讽刺沙复明吗?他眼睛虽然看不见,但不可能不知道人的手都有四个指缝。如果只有两个,那才是真的新发现。对此,毕飞宇回答:“这里不是讽刺,相反,是对爱的描述。沙复明爱着都红,所以,都红的手‘像手’,‘一共有五个手指’,‘有四个手指缝’。这里不是废话,是一种特殊的语气和语调,表示沙复明对都红的手很在意,很用心。这是一种特别的感受,需要用特殊的“废话”才能表达。
131个问题中有很多类似的问答,不仅深入文本肌理,对文本进行丝丝入扣的剖析,还帮助作者发现了隐藏在文本中的问题。比如小说中对手机的描述:应该是“SM卡”还是“SIM卡”?小孔丢的究竟是“卡号”还是“手机卡”?“小孔拿出来的到底是哪一个手机?292页说是深圳的,293页第2段又说是南京的手机?是她搞错了吗?如果是,故事没有说清楚是她弄错了。”毕飞宇回答:“很不好意思,老葛、丽君,因为我没有用过手机,我犯了错误。感谢你们,是我错了。”
由此可见,译者对文本解读的细致程度要远远超过普通读者,甚至是专业的研究者。也许在译者看来,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仅仅是为翻译做准备,就像他们在给毕飞宇的邮件中所写的:“我们问这么多问题,是希望把你的小说翻译得清楚易懂而又通顺流畅,不是质疑你的语言好不好。你不要多心。”但这些问题不仅对于翻译有价值,同时也是从译者角度对文本的一种解读,是非常有价值的文本批评。正如毕飞宇给他们的回复:“怎么会?面对你们的问题,我是很开心的,一方面,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感受到你们的认真。你们还帮助我发现了不少问题。这种认真是你们对翻译的态度,但是,在我看来,更是对我最大的友善。每一次看到你们的问题,我都是把手头的工作放下,然后,一口气回答完。我真的很高兴的。”
译本推介
在完成译本之后,葛浩文还经常为其撰写译者前言、翻译后记等“副文本”(paratext)。根据热奈(Gerard Genette)的观点,“这些存在于文学作品的正文周围、调节与读者关系的材料,在引导读者的阅读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些与正式出版的译文文本一起出现的“副文本”,基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的解读和阐释,紧贴文本的语言、结构和风格,在条分缕析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显性的文本批评。比如在《干校六记》的译者后记中,葛浩文通过文本中的例子分析风平浪静的文字表面之下所隐含的针砭与讽刺,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缺失、社会和时代对知识分子才华的浪费、中国农村的落后和愚昧等,由此总结出杨绛的写作特色:“杨绛的写作风格低调含蓄,但她并非刻意回避重大历史事件。她作品中大部分内容都极其个人化,看似平淡,却意味深长。再加上不经意间流露的作者评论,尖锐而贴切,着实令人难忘。”
俄克拉荷马大学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的藏品中,还有很多与译本推介相关的其他“副文本”,包括葛浩文多年以来研究中国文学的论文、参加学术会议的演讲稿以及与媒体的访谈记录等。随着葛浩文在国内知名度的增加,这些材料陆续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刊物上发表。值得一提的是,葛浩文1999年在台湾饮食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莫言的禁忌佳肴》于2013年由宋娅文翻译成中文并刊登在《长江学术》上,编辑张箭飞在文章末尾致谢:“在校译、审稿的过程中,葛浩文教授数度电邮编辑,讨论如何理解原作中的关键概念、引文和双关语,挑出错漏,修正误译,调谐行文……经由他的提醒,我们注意到中文原文与英语译文之间的差异并由此感知到译者的文心雕龙。”这段话充分体现出文本批评与文学翻译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现代出版社已将他的研究论文、序跋与书评、访谈等结集出版,在两卷本的《葛浩文文集》中,译者的眼光不仅局限于海峡两岸近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还延伸至英国作家、捷克作家的作品,并对当代中国文学在海外的翻译、研究状况进行评析。这一来自译者的批评视角,对于国内的文学评论、研究与创作具有启发意义。
近年来,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越来越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被译介到海外,我们期待海外也能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当海外学者对这些作品进行本体性批评时,他们所针对的文本是译文,而译文又是建立在译者对原文文本的选择、细读和阐释之上的,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进行的文本批评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该重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文本批评,选择最值得翻译的作品,构建最好的译文,并对译本进行有效的推介,让中国文学在“走出去”的道路上呈现出最佳的状态,被更加“文学地”加以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