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与郭澄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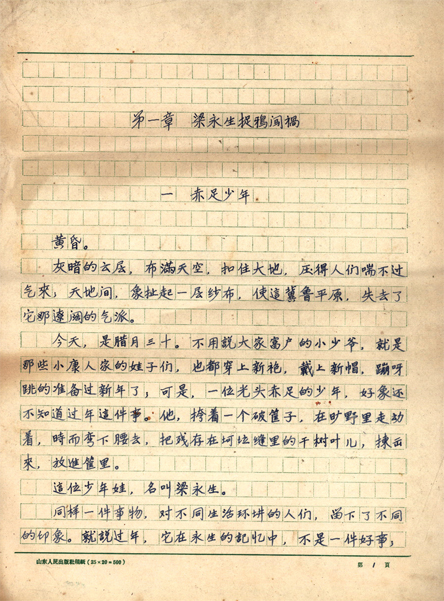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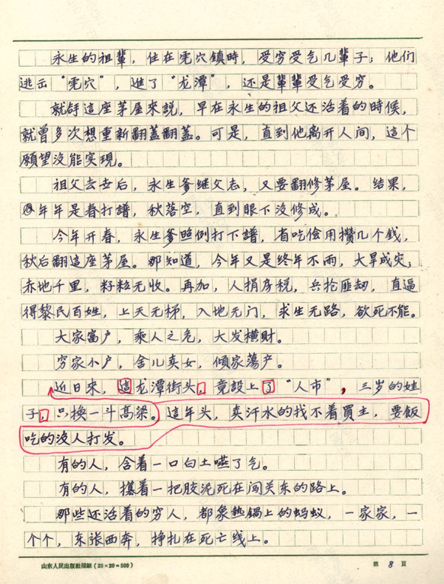
《大刀记》手稿
新中国成立后,在20世纪50年代成长起一大批工农出身的作家。浩然与郭澄清就是这支浩浩荡荡文艺大军里的一员。
按照年头说,浩然比郭澄清小一岁,若按月份算,只小5个月,可以说他们是同龄人。浩然的原籍是河北省宝坻县,现在已属于天津市的一个区;郭澄清的原籍是山东省宁津县,这个县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分别隶属于河北省和天津,把浩然与郭澄清认为是老乡也是有依据的。
浩然与郭澄清一样,都出生在农家,从小就参加革命工作,经历了战争的锻炼和考验,十几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着多年的农村基层工作经历,为他们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生活素材。
浩然是冀东人,始终生活、工作在燕赵沃土上,以三卷本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奠定了在文坛的地位。郭澄清是山东人,始终生活、工作在齐鲁大地上,以三卷本的长篇小说《大刀记》而闻名于文坛。《艳阳天》和《大刀记》发表、出版后都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
浩然与郭澄清从50年代初期就开始发表作品,都以歌颂新人新事,歌颂新的生活起步,根据现有资料,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已经是1965年了。
为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扩编”《社迷传》,这一年郭澄清从山东来到北京,住了很长一段时间。6月26日晚,浩然到北京东城区的炒豆胡同看望暂居在此的郭澄清。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谈到了近12点浩然才回家。
在浩然留下的文字材料中,没有他对郭澄清初次见面后的印象,但从后来事情的发展上看,两个人的交往还是很好的,可以称之为朋友关系。
1965年5月中旬,同为山东籍的青岛作家姜树茂来北京最后一遍修订他的长篇小说《渔岛怒潮》,以便出版。7月13日下午,姜树茂来到浩然家串门做客,谈他的短篇小说创作。聊到晚上吃饭前,浩然又特意约来郭澄清等人,一起畅谈至深夜。
8月22日中午,浩然的朋友、内蒙作家张长弓带着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诸有莹来到家里。到下午4点时,浩然又约来张峻、郭澄清等人,一同到当时很有些名气的京城餐饮老字号“灶温”吃饭,边吃边聊又到很晚。
如同天生的缘分,这年年底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农村文学选读”,其中一本《公社书记》中,选用了四位作家各一篇短篇小说,而浩然与郭澄清就在这四位作家之中。
1965年10月,郭澄清的中篇小说《社迷传》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不久后,他便赠送了浩然一本。浩然在这年12月和次年2月两次阅读了郭澄清的这部新著,虽然感觉在艺术上稍差一些,但还是有新东西的;凡是有新的东西,就应当给予肯定。于是,浩然写了一篇推荐文章《一个崭新的贫农形象》,发表在1966年4月26日的《光明日报》上。这类的文章,浩然在五六十年代是很少涉猎的,大约只写了四五篇。
在这篇约4000字的文章里,浩然对郭澄清的新特点给予了赞扬,对不足也有所提及。在文章中,浩然写道:
我认为,你的《社迷传》里一个值得肯定的特点,是创作了一个崭新的贫农形象高大虎。这个“新”字,表现在你给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注入了新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新的事物,也是最为真实的现实,这是作家应当大为鼓吹的东西。
你身在农村的火热斗争里,看到了这个新的事物,并抓住了它,具体、生动地体现在《社迷传》那个贫农高大虎的形象描写和塑造上,所以,我热情地肯定你的这一点,并要向你学习。
由此可见,我们写农村生活的人,不仅要追着时代的脚步,捕捉新的故事、提炼新的主题,也得挖掘新农民的新的精神因素;跟着而来的,是相应的表现方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6年12月的一天下午,浩然从单位回到家里,看到郭澄清留下的一份材料和一个条子。晚饭前,郭澄清再次来到。两个人畅谈到晚上9点半才分手,浩然将刚刚出版不久的《艳阳天》第二卷赠送给郭澄清。不久后,浩然将郭澄清的材料转给了《红旗》杂志社的编辑朋友。这份“材料”是稿件,抑或是其他什么,因没有详细记载,就不得而知了。
1970年,郭澄清开始了专业创作,比浩然重新回到专业创作岗位整整早了一年。这一年,郭澄清到北京参加修改《奇袭白虎团》的京剧剧本,住在二七剧场,他虽然几次给浩然打电话,要与浩然见个面好好聊一聊,但经历过“文革”初期的暴风骤雨,使浩然在许多问题上接受了教训而显得顾虑重重,与好多人断了通信联系。尽管他也担心有可能引起误会,还是找了种种借口没有应允。浩然显然是有些多虑了。
1972年7月6日,正在故乡访问、写作的浩然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告知郭澄清到北京送稿,要来看他。第二天浩然就赶回了北京,先到出版社与郭澄清见了一面,又去处理完其他事情后,才再次赶回出版社,接着与郭澄清交谈,一直谈到晚上近10点。7月8日晚,郭澄清来到浩然家里看望,并提出希望浩然能够促进一下出版社,为他的长篇小说《大刀记》印几本征求意见本样书。在笔者的印象里,当年确曾看到过这部书的征求意见本,不知这里面是否包含有浩然的“功劳”。
《大刀记》作为郭澄清的一部重要代表作,1975年出版发行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赢得了众多的好评;而浩然同时期出版发行的《金光大道》,作为其70年代的代表作,目前为止全国惟一一部完整记载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全过程的长篇小说,使浩然这个名字在读者心中进一步加深了印象,也同时产生出了更广泛的影响。河北作家刘国震曾在一篇文章中对郭澄清的《大刀记》和浩然的《金光大道》做过一番比较。他在文中是这样写的:
《大刀记》写作于1971至1974年间,197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年曾被改编为连环画和电影故事片、评书等,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这是郭澄清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可以说,没有《大刀记》,郭澄清很难被纳入“经典作家”的行列。但因为此书有“文革时期”这个不好的出生背景,在“文革文学空白论”的束缚下,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的许多当代文学史,对这部书取得的艺术成就,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又因为它描写的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抗日战争生活,官方对这段历史的评价与认识,“改开”前后几无差别,所以,它也没有像同一时期出版的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题材的经典巨著《金光大道》那样遭受那么多误读与攻讦。
《大刀记》与《金光大道》虽然题材不同,但也有它们的共同点。两部作品的主人公梁永生与高大泉,作为他们隶属的那个阶级中的优秀分子,都在为受剥削受奴役的劳苦大众寻找一条改变自身命运,实现公平正义的幸福安康之途。他们都接受了共产党的纲领与理想,又因为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梁永生选择了寒光凛凛的“大刀”——武装斗争(民主革命);高大泉选择了金光灿烂的“大道”——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两部作品,都是“道路小说”,都具有史诗品格。这一点,读一读《大刀记》第一卷前面长达239页的《开篇》,读一读《金光大道》第一部前面那个只有49页的《引子》,就很清楚了。从“大刀”到“大道”,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逻辑和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自然延续。
郭澄清与浩然一样“生不逢时”,虽然也写了大量的作品,出了不少著作,但大多数都没有赶上稿费高的时候,或者根本就没有稿费。在1965年7月14日浩然写给杨啸的信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昨天晚上约郭澄清(他在给“中青”扩充《社迷》为中篇七万字)、姜树茂(青岛人,写四七年海上渔民斗争长篇)、张英(与我同室住,上海人,写电业工人长篇)和玉兄谈了一次,对当前创作问题、稿费问题扯了许多。如今《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对工农作者已不发稿费,送一些书,对于作家,最高者每千字六元,短篇集根本不给稿费了。郭之《公社的人们》只得九十几块钱。
信中说的“郭”,指的就是郭澄清。《公社的人们》则是指作家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郭澄清的短篇小说集;在版权页上印着该书的字数近10万字,印数为5万册。
1976年5月,郭澄清突患脑血栓,至使半身瘫痪。1978年12月20日,浩然与好友李学鳌闻讯后来到北京宣武医院,看望正在此治疗的郭澄清。这大概是两个人见到的最后一面。几年后,浩然来到河北省三河县段甲岭镇挂职,在三河一边继续创作,一边实施他的“文艺绿化工程”,没有必须要参加的会议或活动,很少返回京城;而郭澄清则一边同病魔顽强斗争,一边积极进行新的创作,于11年后的1989年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