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北鸢》:在家族的罅隙里点染民国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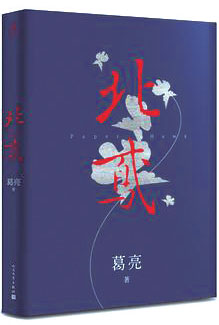
风筝,以“命悬一线”与“一线生机”的特殊释义,在《北鸢》里诠释着人生的悲喜。继《朱雀》之后,《北鸢》是葛亮又一部对民国人物及风物抽丝剥茧的“中国故事”。如果说《朱雀》是交错叙事(现时与历史),那么《北鸢》则是线性叙事(断代),小说视卢、冯两大家族为创作重心,以文笙与仁桢的成长经历为写作线索,将一群不平凡人的非凡经历娓娓道来,借此传达归属民国的大家气度和文化风骨。
这是一部“大制作”的小说,家族、性别、地域、诗画、曲乐、民俗放置于“年代”框架之中,关涉人物众多,叙事盘根错节,时间横亘军阀割据与抗日战争两处乱世。《北鸢》在故事设计上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对称性。文笙与仁桢如同葛亮放飞的两只风筝,牵引着卢家与冯家的上升和跌落。
卢家的跌宕是与“土匪”交战。文笙连缀起卢家、姨母昭德一家、舅父盛浔一家三条叙事支线。我认为在“卢家传奇”部分乃至全篇,昭德、昭如姐妹都是耀眼的女性。姨母昭德是军阀石玉璞之妻,夫亡家破之后,千金散尽,人去楼空,她疯了,蜷缩于对亡子的追忆。面对土匪的胁迫和挑衅,昭德为了保护妹妹家人的性命,选择与土匪同归于尽。小说精彩的一笔是对她的补叙,正是她交给昭如的“红木匣子”帮助教会从日本人手上赎回了11个孩子的命。昭德目送昭如一家安全撤离,“放心地叹了一口气,将手指伸进了手雷的拉环”。“哥儿,好好地活,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一个“叹”字,写活了昭德的“疯”,这是她了无牵挂后的情感释放,无须再躲进“童心”,以逃避痛苦。昭如实为卢家的真正当家人,收养文笙,抚养月娥,她迸发的力量集聚于丈夫卢家睦去世后,接手“东店”,既为月娥置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冥婚”,又最终成全了文笙与仁桢的姻缘。“我能做的就是看着这一个家。家道败下去,不怕,但要败的好看。”卢家几十年风雨飘摇,昭如始终以坚强隐忍支撑家族不覆。
冯家的动荡是与“侵略”抗争。仁桢的成长历程与冯家兴亡相起伏。日本侵华是冯家盛衰的转捩点。与“文笙线”不同,“仁桢线”的叙述对象主要为家庭成员,即仁涓、仁珏、言秋凰。冯家的慧月姐妹与卢家昭德姐妹互为呼应和参照,作者为她们设计了相似的人生和相异的结局。仁珏、范逸美、冯明焕、言秋凰四人又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叙事圈,和田润一的出现打破了人物原本各守其命的稳态,播撒分裂的各种可能。而仁珏的死,将仁珏的爱恨、冯明焕的悔恨、言秋凰的遗恨、范逸美的仇恨再次聚合成人生同一程。
小说的对称式结构,或许是作品对中国传统对称审美的一种暗合。葛亮立足“个人”与“家族”的主题,描画了清晰的社会图谱,人物排列停当,再将想要表达的时代风景、文化元素进行准确取舍与合理归置。应该说,作品在故事层面精致、风雅,但在构思上也相应缺少些突破,沿用的仍是较为寻常的家族叙事套路(代际)和矛盾冲突元素(情理)。
意象与意境的有意识塑造,是《北鸢》对中国古典美学的主动回归。意象是情与物的契合。《文心雕龙》多次涉及心物交融说:如《物色篇》提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诠赋篇》说“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神思篇》道来“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纵观小说,“风筝”有三个重要内涵:“命悬一线”——“昭如被围”、“抓捕仁珏”、“刺杀和田”等都是葛亮安排的千钧一发的极端场景。“一线生机”——在危机降临时,都能有一个承担者来化解困局。“顺势而为”——折射着更深一层的悲凉,相对于之前两种诠释,它更符合普通人的真实心态,但苟且求全却是乱世奢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线就是风筝的规矩”。风筝只有断了这线,才能快意潇洒;人若断了情感与责任的牵绊,才能获大自由。以上三种阐释,是对“风筝”意象美学意义和哲学意义的开发。
放风筝这件事,对于文笙而言,形同本能。“他已习惯了独来独往,面对天空俯仰间,被他人赏鉴。”小说中出现的“虎头风筝”是更有深义的意象。首先它是“四声坊”龙师傅与卢家睦的践约,“这风筝一岁一只”,家睦与文笙的父子缘分全藏这里头了。其次,它是“生”的希望。“虎头纸鸢栩栩如生,斑斓得将这晦暗的秋景染出了一道明黄”,只有它能划破日本军队破城后“虚浮而异样的平静”生活。第三,风筝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符号。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老虎》,翻滚着革命的力量,连接起昭如、文笙与叶师娘、雅各,表达人类共通的友爱、怜悯、感恩生生不息。
小说涌动着悲剧诗意。清丽婉约的文字安静书写出刺痛人心的命题。葛亮的两部民国长卷虽有宏大叙事的格局,但很少对宏大主题进行阐发。创作取材乱世,却竭力摆脱开“民族国家执念”。言秋凰与仁珏母女的牺牲和成全,以“情”消解了“义”,一切行为皆因“必有隐情在心潮”。仁珏与范逸美之间,闪烁着隐秘的暧昧,仁珏牺牲了幸福和性命,要守护的并非逸美的家国大义,而是两人的同性情谊。“和田在这个女孩的脸庞上,看到了一种他琢磨不透的东西。她的反应,不符之前的诸种想象。在他的经验里,对于女人的软弱与坚强,他都成竹在胸。可是她,令他意外,同时感到沮丧。”和田对女性的理解,是预设“她”的行为动机源发于“国”,可他并不知晓,仁珏就是简单为了“情”。剥离种种附加后的纯粹,是葛亮的文学减法,反而颇具触动人心的真切感染力。同时,情之所动、行之所为,又与仁珏所受的“高等教育”的理性形成反差,理智终未敌得过爱情的力量。名伶言秋凰同样如此,委身和田,从容赴死,只因她还是个母亲。她亏欠了仁珏母爱,于是舍出自己的性命来弥补,刺杀和田只是单纯为了给女儿报仇。葛亮笔下的民国女性往往都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没有对人物进行“脸谱化”和“政治化”处理,而是立足于最寻常的亲情与爱情书写。
文笙与仁桢虽是小说主人公,成长经历相对完整,故事丰富,两人目睹家族兴衰、收获革命历练、参与文化传承,但人物较为平稳,缺少些打眼的个性。相反,副线人物更为跳脱生动。究其原因,葛亮在塑造他们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的主旨设定,因而可以调动强烈的矛盾冲突,或设计出激发人性善恶的极端环境。琢磨《杨门女将》里穆桂英的“铁打的身心”,仁桢说,“这样的悲喜,哪是我们平凡人受得了的”,但文笙认定她始终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从《北鸢》中可以获悉,他俩的“不平凡”并非是自身传奇,而是两人恰巧成为了所有传奇的见证者。
小说中随时可察葛亮对绘画、戏曲的熟稔,艺术赋予作品清雅湛明和触手生春。同时,葛亮作品的“古典”也表现为对“风清骨峻”和“辞采华美”的文学自觉。海外“70后”作家特别重视从“民族”和“传统”中寻求突破,彰显古典美学。他们在现时进行“中国形象”再造,致力于文化传承。“江南有三个关键词。第一是生活。从明清以来,江南文化即已展示其宗教世俗化与艺术生活化的倾向。第二是自然,有园林之设计、书画之创作、寺院之修建、山水之欣赏、艺术之创造等,诸种文化建设为自然增加了人文的附加值。第三是知识,内涵科举、庄园、书香、书院等历史文化现象,环绕其四周的有江南各种学术文化流派:吴中画派、扬州学派、常州词派、阳湖文派、西泠十子。”(程章灿:《纸上尘——历史的表里》)从《朱雀》到《北鸢》,在空间上,葛亮以江南为中心,文学创作正是对这三个关键词的全面开发;在时间上,他将“民国”视为历史叙述与文化发掘的主体背景。葛亮为当下“70后”作家“回归传统”的“寻根”提供了实践文本。
《朱雀》是时代的悲歌,《北鸢》是人物的传奇,从点与面共同建构民国场景。“风遂人愿,万事皆好。”而《朱雀》和《北鸢》恰是在种种不遂人愿的人生中设局与解局,就如威廉·布莱克在他另一首诗《天真的预言》里说:“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是永劫。”
创作谈:
时间煮海
葛 亮
《北鸢》关乎民国,收束于上世纪中叶。
祖父在遗著《据几曾看》中评郭熙的《早春图》曰“动静一源,往复无际”,引自《华严经》。如今看来,多半也是自喻。那个时代的空阔与丰盛,有很大的包容。于个人的动静之辩,则如飞鸟击空,断水无痕。
大约太早参透“用大”之道,深知人于世间的微渺,祖父一生与时代不即不离。由杭州国立艺专时期至中央大学教授任上,确乎“往复无际”。其最为重要的著作于1940年代撰成,始自少年时其舅父陈独秀的濡染,“予自北平舅氏归,乃知书画有益,可以乐吾生也”。这几乎为他此后的人生定下了基调。然而,舅父前半生的开阖,却也让他深对这世界抱有谨慎。晚年的陈独秀隐居四川江津鹤山坪,虽至迟暮,依稀仍有气盛之意,书赠小诗予祖父:“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不久后,这位舅父溘然去世,为生前的不甘画上了一个凄怆的句点。同时间,也从此造就了一个青年“独善其身”的性情。江津时期,祖父“终日习书,殆废寝食”, “略记平生清赏,遑言著录”。祖父一生,无涉政治。修齐治平﹐为深沉的君子之道。对他而言,可无愧于其一,已为至善。祖父的家国之念,入微于为儿女取名﹐我大伯乳名“双七”﹐记“七七事变”国殇之日;而父亲则昵称“拾子”﹐出生时值1945年﹐取《满江红》“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之意。这些时间的节点,成为他与世代间的联络最清晰而简洁的注脚。
及至多年后,祖父的编辑,寄了陈寅恪女儿所著《也同欢乐也同愁》等作品给我,希望我从家人的角度,写一本书,关于祖父的过往与时代。我终于踌躇。细想想,作为一个小说的作者,或许有许多的理由。一则祖父是面目谨严的学者,生平跌宕,却一步一跬、中规中矩;二则他同时代的友好或同窗,如王世襄、李可染等,皆已故去,考证变得相对庞杂,落笔维艰。但我其实十分清楚,真正的原因,来自我面前的一帧小像。年轻时的祖父,瘦高的身形将长衫穿出了一派萧条。背景是北海,周遭的风物也是日常的。然而,他的眉宇间,有一种我所无法读懂的神情,清冷而自足,犹如内心的壁垒。
以血缘论,相较对祖父的敬畏,母系于我的感知与记忆,则要亲近得多。外公曾是他所在城市最年轻的资本家。这一身份,并未为他带来荣耀与成就,而成为他一生的背负。但是,与祖父不同的是,他天性中,隐含与人生和解的能力。简而言之,便是“认命”。这使得他得以开放的姿态善待周遭。包括拜时代所赐,将他性格中“出世”的一面,抛进“入世”漩涡,横加历练。然而,自始至终,他不愿也终未成为一个长袖善舞的人。却也如水滴石穿,以他与生俱来的柔韧,洞贯了时世的外壳。且行且进,收获了常人未见的风景,也经历了许多的故事。这其间,包括了与我外婆的联姻。守旧的士绅家族,树欲静而风不止,于大时代中的跌宕,是必然。若存了降尊纡贵的心,在矜持与无奈间粉墨登场,是远不及放开来演一出戏痛快。我便写了一个真正唱大戏的人,与这家族中的牵连。繁花盛景,奼紫嫣红,赏心乐事谁家院。倏忽间,她便唱完了,虽只唱了个囫囵。谢幕之时,也正是这时代落幕之日。
本无意钩沉史海,但躬身返照,因“家”与“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络,还是做了许多的考据工作。中国近代史风云迭转。人的起落,却是朝夕间事。这其中,有许多的枝蔓,藏在岁月的肌理之中,裂痕一般。阳光下似乎触目惊心,但在晦暗之处,便了无痕迹。这是有关历史的藏匿。
我写了一群叫做“寓公”的人。这些人的存在,若说起来,或代表时代转折间,辉煌之后的颓唐。小说中是我外祖的父辈。外公幼时住在天津的姨丈家中。这姨丈时任直隶省长兼军务督办,是直鲁联军的统领之一,亦是颇具争议的人物。民间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多与风月相关。1930年代,鸳蝴派作家秦瘦鸥曾写过一部《秋海棠》,其中的军阀袁宝藩,就以其为原型。此人身后甚为惨淡,横死于非命。整个家族的命运自然也随之由潮头遽落,瓜果飘落。少年外公随母亲就此寓居于天津意租界,做起了“寓公”。“租界”仅五大道地区,已有海纳百川之状,前清的王公贵族、下野的军阀官僚,甚至失势的国外公使。对这偏安的生活,有服气的,有不服气的。其间有许多的砥砺,文化上的,阶层与国族之间的。只是同为天涯沦落人,一来二去,便都安于了现状。
这段生活,事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北地礼俗与市井的风貌,大至政经地理、人文节庆,小至民间的穿衣饮食,无不需要落实。案头功夫便不可缺少。一时一事,皆具精神。复原的工作,史实为散落的碎片,虚构则为粘合剂,砌图的工作虽耗去时间与精力,亦富含趣味。
与以往的写作不同,此时我更为在意文字所勾勒的场景。那个时代,于人于世,有大开大阖的推动,但我所写,已然是大浪淘沙后的沉淀。政客、军阀、文人、商人、伶人,皆在时光的罅隙中渐渐认清自己,所谓“独乐”,是一个象征。镜花水月之后,“兼济天下”的宏愿终难得偿,“独善其身”或许也是奢侈。
再说“动静一源”,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一静一动,皆自根本。“无我原非你”。在这瀚邈时代的背景中,他们或不过是工笔点墨,因对彼此的守望,成就故事中不离不弃的绵延。时世,于他们的成长同跫,或许彼时是听不清,也看不清的。但因为有一点寄盼,此番经年,终水落石出。记得祖父谈画意画品,“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迄,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于时代的观望,何尝不若此,需要的是耐心。历久之后,洞若观火,柳暗花明。
小说题为《北鸢》,出自曹寅《废艺斋集稿》中《南鹞北鸢考工志》一册。曹公之明达,在深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之道。字里行间,坐言起行。虽是残本,散佚有时,终得见天日。管窥之下,是久藏的民间真精神。
这就是大时代,总有一方可容纳华美而落拓的碎裂。现时的人,总应该感恩,对这包容,也对这包容中铿锵之后的默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