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中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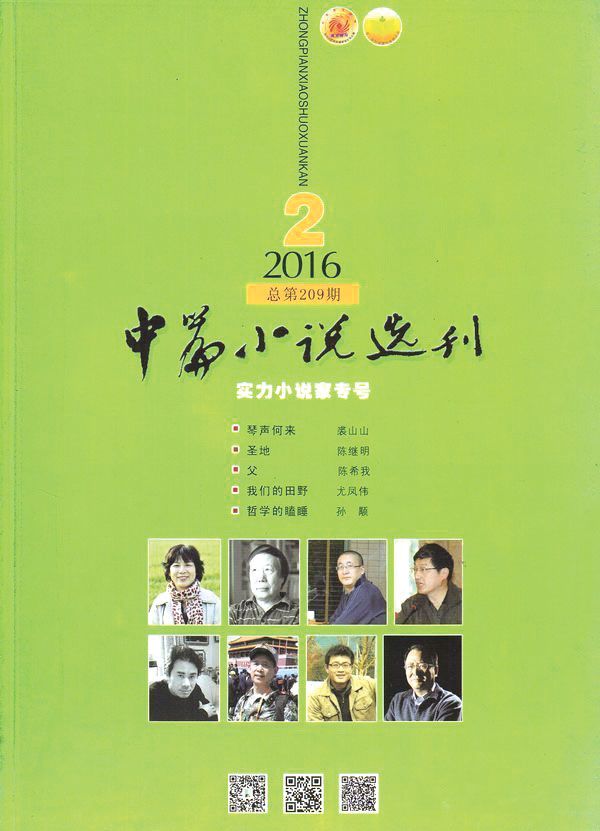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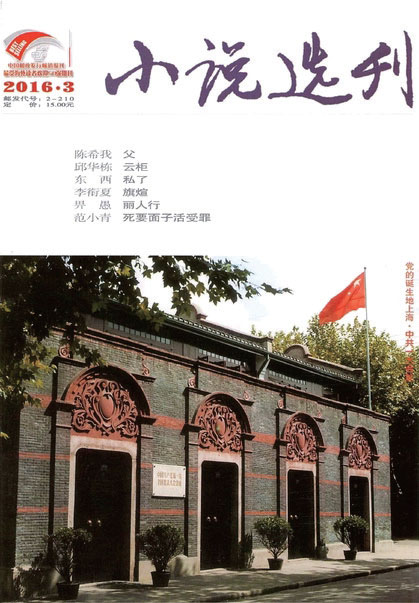
在如今的文学创作领域,一个被广泛公认的现实是,中篇小说是各类文学体裁中最繁荣的一种。以严肃文学最重要的展示平台文学刊物为例,我们看到,不但各种原创刊物纷纷把中篇小说作为主打内容,那些直接面向零售市场、精准跟踪读者需求的文学选刊更是如此。各类选刊中,不但有《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这样专门选发中篇的刊物,就连《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实际上也是以中篇为主,选发短篇小说更多是着眼于扶持有创作潜质的新人。而且,中篇小说不仅在作品数量上丰收,在艺术品质上多年来也始终保持高位运行的态势,整体上实现了对社会现实的多视角无缝呈现,对活跃在人们视野中的各种公共话题都进行了广泛关注,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物的现实际遇和精神空间都在作品中得到全面的展示。
尤其令人惊喜的是,中青年作家不断创作出优秀中篇作品的状况,又给知名作家带来动力。除了莫言、余华、贾平凹、王安忆等少数作家集中力量在长篇领域深耕,王蒙、张炜、陈世旭、梁晓声等创作资历深厚的作家也在频繁地拿出极具新意的中篇作品。可以说,中篇小说的创作队伍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数量最大、年龄覆盖面最广的。
那么,作家纷纷把创作热情倾注于中篇小说原因何在呢,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局面又是因何产生的呢?在中国古代,诗词、杂剧、小说之所以盛行于不同历史时期,和当时特定的社会氛围、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相关,我们探寻中篇小说兴盛的原因,也应该在文学之外寻找答案。应当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分化裂变、社会形态的日新月异,一直在为包括中篇小说在内的各类文学创作提供着基础性动力,但最终只有中篇小说这一体裁抵达当下的繁荣。在我看来,这一局面的形成是与新闻媒体的作用密切相关的。
自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开始,《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电视栏目和各种都市类、财经类报刊,通过对社会热点事件的深度报道,实现了对公共舆论的引领,刷新着人们对中国现实的认识。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外的书籍、观念、思想涌入闭塞多年的国门,国人实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思想启蒙,那么,在这一轮的媒体浪潮中,国人又开启了第二次启蒙,即看到了曾经被遮蔽的更加复杂、立体的现实。于是,人们开始带着问题意识重新观察身边的世界,渴望了解那些仿佛在一夜之间发生的深刻变革究竟意味着什么,又会对自己的命运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至今,很多作家回顾起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最初几年,文学被急剧边缘化的场面仍然心有余悸。但是,作家也是传媒的受众,是电视观众、报刊读者中的一员,他们在各种调查式报道中看到的或者在现实生活中目击到的场景,直逼自己的心灵底线,对自己的灵魂造成挤压,迫使作家逐渐将社会问题、热点事件纳入自己的写作中。作家希望在作品中全景展示某一社会热点事件的发展过程,同时体现出自己的批判立场和情感温度,最符合这一标准的文学样式,显然非中篇小说莫属。
而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根据传播学的原理,当读者对某个新闻事件了解得越多,获得的信息量越大,该事件原本不为人所知的各个侧面就会更加充分地暴露在读者面前,读者也就会有更加强烈的意愿去探究更多真相。这种真相,不仅仅是事件本身各类细节,还包括事件中人物心理世界的变迁。以近年来得到广泛转载的《杀人者》(甫跃辉)、《滚钩》(陈应松)、《人罪》(王十月)等中篇作品为例,这些作品所取材的马加爵杀人案、长江挟尸要价事件、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因为各类媒体的轰炸式报道而家喻户晓。即使这些事件已经成为公共话题,占据了大量的报刊版面和电视时段,被不同领域的专家轮番解读,这几篇中篇小说对人物灵魂的剖析、拷问,显然不是强调客观理性的新闻报道可以望其项背的。鲁敏关注失独老人话题的《零房租》,同样有着新闻原型,她在创作谈中说,“那则新闻有个所谓温馨结局:老人与少女,互相帮助、共享亲情。我完全不信那个。可能因为我较悲观而狭隘。再说我想写的不是故事,而是人间的关系,人际的隔阂与无力。这种人际,包括陌路人的,更特指亲人之间的:母与女、父与子、夫与妻,活人与死者,得意者与不幸者,在本质上,这些关系都是差不多的——彼此间,做不到真正的融洽与亲切”。这样的文字质地与思辨色彩,难以在新闻报道中找到。从这个角度来说,对读者的阅读体验来说,构成中篇小说的“假想敌”的,并不是形式上与之更接近的短篇小说,而是报刊媒体中的深度报道。
如果我们细加分析,中篇小说和新闻报道之间其实是一种亦敌亦友的关系。各类媒体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一个新闻热点形成后,报刊、网络都会进行全面及时的跟踪,作家足不出户,无须身临现场就能获得足以支撑小说框架的全部素材。作家体现在作品中的批判精神和情感温度,又会和新闻报道的专业分析形成有效互补,使读者得到极为丰富深邃的阅读体验。
当今的中篇小说,所关注的早已不仅仅是具体社会事件,读者感兴趣的各种社会话题,都可以在中篇小说中找到回响。和某些短篇小说中那些姿态轻佻、指向含糊、思想脆弱的文体实验不同,中篇小说在以更加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更加深邃的现实情怀,深度介入现实。荆歌的《珠光宝气》等古玩题材小说,滕肖澜的《美丽的日子》《倾国倾城》等都市婚恋类小说,裘山山的《死亡设置》、张欣的《狐步杀》等刑侦题材小说,南飞雁的《红酒》、杨少衡的《蓝名单》等官场小说,蒋峰的《翻案》、但及的《藿香》等民国题材小说,杨小凡的《总裁班》、申剑的《完全抑郁》等商战小说,海飞的谍战小说,阿袁的《米青》、张者的《桃夭》等校园题材小说,这些作品涵盖了各种热点话题,故事内核极具戏剧张力,同时善于以圆熟精到的笔法描摹人物内心冲突,读者由此形成强烈的代入感,深深沉浸在成人童话般的故事氛围中。一部中篇小说的阅读过程,就是一次乘兴而去尽兴而返的精神冒险。
除了可以展现复杂多变的故事脉络和人物内心世界,中篇小说另一个令短篇小说难以企及的优势是可以在数万字的篇幅中,对各种引人入胜的细节进行淋漓尽致的精细描绘。在当前的中篇作品中,细节早已不再是局部服从整体名义下的绿叶式陪衬,而是从文本中获得独立,玲珑浮凸于读者面前,如万花筒一般展示着大千世界的精彩,并以此宣告着自己的主权。陈谦在《无穷镜》中对华裔高科技精英硅谷生活的描摹,滕肖澜在《美丽的日子》《在维港看落日》中对上海、香港两地婆媳斗法的紧张过程的呈现,常小琥在《收山》中对烤鸭技艺的揭示,阿袁、张者对高校中情爱秘闻的书写,正是通过一串串连贯性的细节,牢牢牵引着读者探秘的目光,以此确保了故事的可信度。总之,作家精心编织、打磨细节,在细节里营造出一个清晰逼真的世界。读者则反复抚摸、品味细节,在细节的带领下,进入原本陌生的阶层、空间。可以说,对于当前读者的阅读习惯来说,细节几乎和故事一样重要。既然如此,自然是能够容纳无数庞杂繁密的细节的中篇小说,而不是缺乏回旋空间的短篇小说更能吸引读者。
中篇小说的兴起,当然离不开文学刊物所给予的充裕版面。作品总是需要平台的,和多年前因为订阅量大幅度下滑导致难以维持不同,当前的文学期刊,很多都能获得政府、企业的资金扶持。和任何一种投资一样,文学刊物也需要对投资人进行一定的回报,能较为直观地体现刊物品质的方式,无非是知名作家的原创作品。但是,文学的投资者往往并非文学从业者,即使他们对文学有所了解,经常也限于莫言、贾平凹等寥寥几个作家,而持续地拿到他们的新作,对于众多一年要出版6期或者12期的期刊来说,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期刊如果能拿到作者知名度稍逊,但艺术质量的确上乘、故事性较强、并获得广泛转载的作品,也是工作成绩的体现。这种情况下,中篇小说就因为篇幅较长、容量较大、更讲究阅读趣味,在和其他文学体裁争夺版面的过程中获得了某种优势,刊物往往也就更主动地寻找高质量的中篇作品。于是,中篇小说逐渐获得了稳定的生长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中篇小说创作的优势地位,很大程度是与短篇小说、诗歌、散文较为缺乏社会关注度的局面相比而显现出来的。中篇小说数量的剧增,其实尚未成比例地实现质量的提升。即使是当前中篇小说中公认的佳作,且不与《阿Q正传》《林家铺子》《灭亡》这样以个人悲剧凝聚家国情怀和民族立场的经典相比,即使是和新时期以来的《腊月·正月》《人到中年》《你别无选择》《烦恼人生》等中篇作品对时代本质的强劲穿透相比,这些作品在质量上的不足都是明显的。在当下很多作品中,黑车司机、坐台小姐、古玩掮客、官二代、富二代等不同阶层的人物涌入一个个光怪陆离的故事,故事则涌入篇幅越来越长的文本,作家过于强调故事的戏剧化特征,人物成了展示情节的道具,导致作品成为文学语言包装下的通俗传奇故事。这些作品看似题材不一、情节各异,内在的美学品格和思想指向却日趋雷同。而小说故事发展的驱动力,更多是靠作家一步步营造剧情,而不是故事本身的内在逻辑。看得出,有的作家的确试图对主题进行深度发掘,但基本上仍在故事表层叙事中盘桓,未能有说服力地揭示人物悲剧命运背后的规律性原因。这些都说明,作家没有浮出生活的水面,尚须更加深入地洞悉时代本质,提炼出能真正反映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其实都具备某种自足的生命力,一旦被作家搭建起基本框架,就可以裹挟着人物冲向终点。
总之,当前的中篇作品中对“实然”的呈现可谓纤毫毕现,但对“应然”的追寻尚付阙如,这也是当前中篇小说创作中最大的不足。要克服这一点,作家还是应该从对情节、细节的追逐中抬起头来,以悲悯的情怀和超越性的目光观察现实,从而萃取出真正凝聚时代本质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