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生态少年文学发展浅析 弘扬生态意识 追求和谐共存
1972年《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一书的最初版本问世,阐明了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对人类自身生存所构成的巨大威胁。这本书原为德内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丹尼斯·梅多斯等受“罗马俱乐部”委托所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其中所涉及的一系列环境破坏现象和生态恶化趋势对知识界、思想界冲击很大,并促使环境运动、绿色运动成为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运动的主要潮流之一。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也促成了“生态文学”(Ecological Literature)的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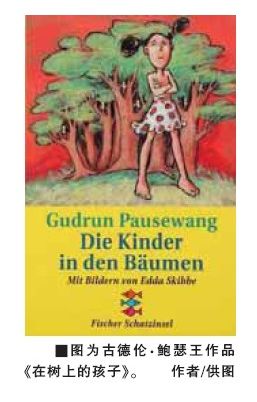
反思生态环境污染
与以上因素相呼应,这一时期的西方少年儿童文学作品也开始涉及生态环境相关主题,出现了首批揭露和反思环境污染问题的生态少年文学作品。
当代美国儿童文学作家珍·克雷赫德·乔治(Jean Craighead George)的《到底谁杀死了知更鸟:生态之谜》(1971)就是生态少年文学作品的范例之一。故事说的是,在号称最清洁的城市萨德勒波罗,发生了一件怪事。该市的吉祥物——知更鸟突然不明不白地死掉了。少年托尼从小就对环境问题特别敏感,他通过明察暗访,最终查明了知更鸟之死的事实真相,为把该市建成真正的清洁城市作出了应有贡献。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通过丰满的文学形象,引导人们关注环境问题,给读者留下了自我判断、自我鉴别的广阔空间。
当代德国儿童文学作家古德伦·鲍瑟王(Gudrun Pausewang)的《在树上的孩子》(1994)描述了孩子们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破坏森林生态环境的行为。书中的主人公桑塔纳一家原本生活在南美原始森林的边缘地区。该区域土地的所有者赛诺·利珀尔为了赚更多的钱,打算不惜一切代价烧荒以获得耕地。通过桑塔纳家的孩子们的努力,利珀尔的儿子温贝尔托意识到保护环境和森林的重要性。因此,他爬到高高的树上,坚决阻止父亲放火毁林。文中孩子们的行为表明,鲍瑟王认为人类只是土地和森林的利用者而不是拥有者。只有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观,放弃无节制的开发逻辑,才能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留给子孙后代一块圣洁的土地、一泓干净的水源和一片蓝色的天空。
鲍瑟王的另外两部作品,《最后的孩子》(1983)和《穿过云朵的少女》(1987)则涉及核战争及其危险。《最后的孩子》描写了核爆炸发生后,年仅12岁的男孩罗兰德令人惊异的拯救之旅。作者借此书呼唤着灾难中的人性和温暖,让读者战胜恐惧中张扬生命意志,同时珍惜当下宝贵的和平时光。而在《穿过云朵的少女》中,鲍瑟王则通过主人公雅娜的遭遇,描写了核爆炸辐射给劫后余生者造成的巨大身心创伤。
这些作品都围绕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主题,展现了少年儿童纯洁美丽的心灵世界和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此外,鲍瑟王还透过对人物内心世界和命运的多层次描写,构筑一种多层交织叙述模式。
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主义关注一切生命的价值,尤其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认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并由此形成生命共同体。一旦生态网络遭到破坏,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就岌岌可危。因此,在地球这个共同体中,一切生命体都应当同生共存、同享共荣。许多西方生态少年文学作品也体现出这种思想。
美国作家加里·保尔森的《手斧男孩》(1987)描写了一个名为布赖恩的少年,因飞机失事而迫降在加拿大某处树林内,仅凭一把斧头维持了生存的故事。与以往的《鲁滨逊漂流记》等冒险故事不同,布赖恩不是把自然视为征服的对象,而是视为一同生活的良师益友。
克雷赫德·乔治的另一部作品《狼群中的朱莉》(1972),描写了一位爱斯基摩少女米娅克丝(朱莉),依靠头狼阿玛罗克的帮助在野外生活的感人故事。但是,最终阿玛罗克却死在乘飞机狩猎取乐的人手中。当米娅克丝发现,杀死勇敢、美丽、无辜的阿玛罗克的不是别人,正是她所尊敬的父亲——一个曾经激烈谴责企图灭绝狼群、独占阿拉斯加的白人政策的人时,她感到彻底的绝望和被出卖。她扼腕痛惜,大声疾呼:“昔日狼曾经是爱斯基摩人的好朋友,如今这一切都结束了。”
当代澳大利亚儿童文学作家柯林·梯勒的《提米》描写了少年丹尼与小野兔提米之间的美丽友情和浪漫冒险故事。失去双亲、寄居在姨妈家的丹尼以温暖的眼光看待失去了妈妈的提米。两个幼小的生命同舟共济,努力掌握生存本领。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丹尼抚平了内心的创伤,开始学会理解和亲近自然,爱护和尊重动物,尤其是关爱弱小的生命。作者着力刻画充满野性的提米如何逐渐向丹尼敞开心扉,进而主动接近他的全过程,说明了“亲情友情”、“心有灵犀一点通”等并非仅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
具有印地安人血统的当代美国儿童文学作家佛瑞斯特·卡特的《少年小树之歌》(1976),描写了主人公小树在山上与爷爷奶奶一同生活的甜蜜日子。小树跟爷爷奶奶一起在大山里生活,他在山中与大自然同呼吸、共命运、齐成长,积累了无数闪光的美好回忆。然而,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只留下了他一个人。小树漫无目的地徘徊在印第安地区,他呼喊着,寻找着,挣扎着。这期间,陪伴他的几只狗也相继死去,随着最后那只“蓝孩”也闭上了眼睛,“温暖他的灵魂的日子”戛然而止,小树的故事也徐徐落幕。
此类作品还有贝特西·贝尔斯的《午夜狐狸》(1968)、苏珊·杰弗斯的《西雅图酋长》(1991)、罗恩·本尼的《鹰之眼》(1995)、蒂姆·温顿的《蓝背鱼》(1998)和伊莎贝尔·阿连德的《野兽之城》(2002) 等。
重视人类精神生态变化
生态文学不仅关注自然界中的生态破坏,也重视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变化。因为究其本质,自然的破坏也会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不良影响。当代美国儿童文学作家南希·法默的《蝎子之屋》(2002) 全面探讨了克隆技术给人类带来的道德和伦理困惑、肉体与灵魂的冲突以及生命的本质和价值,强烈呼吁人们重视克隆技术对人类精神生态造成的负面影响。
从英格兰作家奥尔德斯·伦纳德·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开始,许多生态文学作品都设想了一个“人性”被机械剥夺殆尽的阴暗的未来社会。法默的《蝎子之屋》也是如此。作为克隆人,马特小时候被关在罂粟田中的一个小木屋里,终日与蟑螂、骷髅为伴,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非人生活。之后,就像头脑里植入芯片的机器人一样,马特按照主人的命令,没完没了地从事一种单调乏味的工作。在所有“真人”的心目中,马特充其量只是一只“牲畜”或一条“虫子”。但马特高尚、勇敢、坚强,面对在劫难逃的命运,他以超然的勇气和毅力,捍卫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在勾画马特一连串惊心动魄、曲折跌宕的历险之余,作者最终得出了一个末世论的预言和警示:“科学的发展未必会给人类带来幸福。”
对于克隆技术,人们往往持两种不同态度。其一是,基于伦理道德方面的理由,反对任何对生命的复制;其二是,出于治疗目的,赞成有限的生命复制。如今科学研究已经越过了对动物克隆的伦理障碍,克隆羊多利早已诞生,胚胎克隆技术的成功也被视为里程碑式的科学成就。展望未来,科学家们将以治疗为目的,进行更多的克隆实验。这样,有朝一日,克隆人将有可能不再只是电影、小说里的主人公,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人物。
法默的《蝎子之屋》作为一部科幻小说,恰恰探讨了这些“尚未”存在的事情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在这部作品中,法默并没有空喊口号,而是启发式地全景展现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尽管任何读者都不会把自身等同于克隆人马特,但至少会对马特所受到的虐待感到愤恨不平。此外,人们也会联想其他一些问题,例如,假设真的存在“我”的克隆,它将是“我”自身还是其他的存在,或者有一天“我”是否也会成为可被利用的内脏仓库?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当代少年生态文学视域非常辽阔,主题从直接的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出发,一路延伸到人与自然的神交契合、灵犀相通,直到人的精神生态及其所面临的危机。少年生态文学蓬勃的生命力在于始终聚焦并弘扬生态意识,从文学视角将这种意识高度形象化和艺术化。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