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文学史现场:关于作家的“双面人”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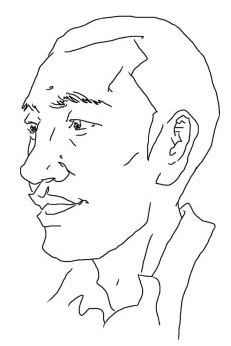
主持人语
“文学研究最理想的境界,应该是在研究文本的基础上,综合有关作家创作心理、创作背景的种种因素,去揭示文本与人本的深刻联系、感悟文学的玄机。”
樊星教授注意到特定情势下“人”“人格”“人性”的畸变,而“人本”的“双面人”或者“双重人格”必然会转移到“文本”。从“人本”通向“文本”,以“文本”返观“人本”,樊星教授的观点在文学批评中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且,文学批评越来越“刻意”的学理化,这种随性的札记本来应该是文学批评文体的一部分,现在好像更多地被散文或随笔收编,但批评家的札记写作应该成为批评的职业能力。

如何回到文学的现场,通过作家、评论家的回忆,去还原文学作品的发生契机、文学思潮的流变轨迹、文学论争的前因后果,进而还原文学的生动鲜活、丰富复杂,对于理解文学的玄妙、理解文学的“超理论性”至关重要。文学研究最理想的境界,应该是在研究文本的基础上,综合有关作家创作心理、创作背景的种种因素,去揭示文本与人本的深刻联系、感悟文学的玄机。
同时,文本不是文学的全部。在文本之后、之外,还有多少人心的活动、人与人的斗争、人与权力、时势的周旋以及淹没在历史深处的种种说法,惹人遐想。
回到文学本体,也许不仅仅意味着回到理论的探讨。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如何回到文学的现场,通过作家、评论家的回忆,去还原文学作品的发生契机、文学思潮的流变轨迹、文学论争的前因后果,进而还原文学的生动鲜活、丰富复杂,对于理解文学的玄妙、理解文学的“超理论性”至关重要。
回忆录中的现场
这些年,读过一批作家的访谈录、回忆录,还有一些学者的反思录,常常有穿越历史、回到文学现场的真切感。是的,文学研究最理想的境界,应该是在研究文本的基础上,综合有关作家创作心理、创作背景的种种因素,去揭示文本与人本的深刻联系、感悟文学的玄机。就像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已经做到的那样。
读从维熙的回忆录《走向混沌》,注意到“反右”运动中,大家虔诚悔“罪”,“可是一到现实生活里去,亲眼目睹的现实,又支持自己右派思想泛滥……我发现自己成了一个两面人”的曾经体验。这是怎样的“人格分裂”?多年后读李洁非的《典型文坛》,其中也有专文《来与去》研究郭小川的“双面人”心态:“外在是一面,内心是另一面。”“展示给别人看的那一面,他相当有战斗性,对‘斗争’充满激情与渴望……但在心灵隐秘的一角,却总是遥远地有一个‘政治斗争真可怕’在飘荡,这声音时时刻刻令他担心会不会不知什么时候‘斗争’就突然搞到自己和家人头上……”可见在革命年代里,政治运动的频繁、政治高压的厉害,使革命者内心的苦闷与恐惧也那么深重。
在邵燕祥的回忆录《沉船》中,也记录了诗人在那个年代的迷惘与痛苦:“我懂得的政治也只是书本上的政治。”而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政治运动中,诗人陷入了人格分裂的痛苦中:“有两个自己在商量着,妥协着,辩论着,争吵着。”从认认真真地自我检查、批判,到“乐于回答同志们的尖锐的、琐屑的、促狭的问题”再到“有些不耐烦”,直至“以玩世不恭的心情来应对或沉默了”。这样的心路历程在那个政治高压的年代里具有怎样的代表性?有多少“右派”是在翻来覆去的“大批判”中看破了极左政治的荒唐可笑的!如此说来,那样的“人格分裂”、“人格演变”(姑妄名之)也可以算作觉醒的开始吧。
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一书重现了过去年代里文人之间残酷斗争的黑暗现实,其中写郭小川一面对周扬不满,不与周扬见面,也不参加作协会议,一面在私下里说:“毛主席啊,我们真跟不上……”有时又“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左派”,可见他的苦闷、以及苦闷中闪烁的自信。那一代革命者,谁没有过类似的自信?可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多少人因为自信是“真正的左派”而彼此互掐,到头来却两败俱伤(例如周扬与胡风、周扬与丁玲);又有多少人看破了颠来倒去的折腾,“躲进小楼成一统”(像茅盾、牛汉、曾卓),或“冷眼向洋看世界”……李辉曾经记下了贾植芳的一声叹息:“左派文人差不多都好斗,像钱杏邨、郭沫若、成仿吾,还有周扬。”(《他们眼中的周扬》)可谓一针见血!为什么左派文人好斗?而且常常是互相之间你死我活的缠斗?从上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论争”到延安文坛上的宗派斗争再到1949年以后的一系列从文艺争鸣开始的政治斗争,都那么声色俱厉、仇恨满腔。是时代风气使然,还是文人逞性所致?另一方面,为什么仍然有左派能够与难以理喻的狂热保持距离?例如延安时期的萧军,还有在“文革”狂热中保持了良心的浩然,就因为他天性朴实吗?(陈徒手:《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
在上述“两面人”现象的深处,是政治高压与良心未泯的激烈博弈。这样的博弈足以表明,即使是在特定的年代里,有些作家的良心也并没有麻痹。经过一次次荒唐的政治运动,多少人渐渐回归了正常的理性。
也有另一种“两面人”。例如张光年谈周扬:“表面上谈笑风生,内心是孤独郁闷”。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人“常常批评他的政治性不强,对老朋友下不了手”。(李辉:《与张光年谈周扬》)还有夏衍谈何其芳:“他受当时的组织,当时的风气的影响,作为个人来讲,他很谦虚谨慎的,但文章写得很厉害。”(李辉:《与夏衍谈周扬》)生活中有人情味,政治运动中就变成另一个人了。是为了与时俱进,还是另有难言的苦衷?
耐人寻味的还有,“文革”过后,周扬良心回归,多次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真诚道歉。可为什么“丁玲一直到死,都没有听到周扬说一句道歉的话”?(陈徒手:《丁玲的北大荒日子》)为什么李之琏(曾任中宣部秘书长,被打成过“右派”)也说周扬“对人道歉是应付人的,从来没有真诚”?(李辉:《与李之琏谈周扬》)有的人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有的人为什么做不到?除了宗派之间的不解之恨,有没有性格的深刻龃龉?
到了新时期,思想解放,政治高压也很快烟消云散了。然而,不时降临的敲敲打打还是在持续拷问着作家的良心。好在时代真的不同了,上述批判都没有使作家们噤若寒蝉,同时也就不会再有“文字狱”的死灰复燃。
作家的“双重人格”
但“两面人”现象有了新的表现。有时对一个问题转眼之间判若两人的表现不可思议,说明了什么?是为了心有余悸而采取的自我保护?还是发自肺腑的划清界限声明?
而王蒙在《王蒙、王干对话录》中的自道则别有洞天:“我身上有两种倾向或两种走向都非常鲜明,比如一种是幽默,一种是伤感……”“我感觉到的一个悖反就是游戏和真诚……我的作品有许多真实生命的体验……但我丝毫也不否认我有玩弄文字的游戏、有些甚至到了常人所不能接受的成分”。他的小说时而感伤(如《蝴蝶》《海的梦》《恋爱的季节》等),时而幽默(如《冬天的话题》《坚硬的稀粥》《狂欢的季节》等),与性格的“两种倾向”显然有关。
莫言亦然。在贫困乡村长大的他曾经说过:“我的写作动机一点也不高尚”,“当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给父母争气,想证实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虚幻。”(引自赵玫:《淹没在水中的红高粱》,《北京文学》1986年第8期)虽然他后来多次说,想当作家的动力是受到一个“右派”的影响,为了一天三顿吃饺子。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他刚出道时的那番真诚剖白,那是无数苦孩子奋发努力的共同心声。另一方面,他在《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檀香刑》中又实践了“要弘扬农民意识中的光明一面”的主张,表明他没有止于“想出名”、“一天三顿吃饺子”的渴望。还有,他写故乡,经常表达的是对故乡既爱又恨的复杂情感,也是“双重人格”的另一种表现吧。此外,因为喜欢说话,他从小到大得罪了不少人,于是将笔名定为“莫言”,可到头来还是喜欢说。而他的小说《丰乳肥臀》引发争议,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几年后,风平浪静下来,莫言如是说:“你可以不读我所有的书,但不能不读我的《丰乳肥臀》。”那狂气一点没变。这可以说是“双重人格”的又一种表现。
作家的“双重人格”摆脱了政治运动的禁锢,却常常在不经意间也会招来麻烦。好在那些麻烦都是过眼云烟。在新时期,对文艺作品的批判常常只是起到了为那些作品做广告的喜剧效果。而这又是那些批判者始料未及的吧!
毕竟,时代变了!
如此看来,“双面人”或者“双重人格”现象具有非常丰富的意义:在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里,它折射出良心的痛苦、周旋的空间;在思想解放、文化多元化的岁月里,它常常是作家个性丰富性乃至文学风格多样性的投射。
文学研究就这样与心理学研究水乳交融。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因此可以常说常新。
文本不是文学的全部
读李辉的《沧桑看云》,就注意到他写出了作家的性格悲剧。他这么分析冯雪峰的性格悲剧:“与暴躁相伴随的是激情,是愤世嫉俗;与偏激相伴随的是独辟蹊径,是固执己见;与骄傲相伴随的是自信,是洁身自好。”(《凝望雪峰》)由此使人想起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话:“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还有,作家如此反思老舍大起大落的命运:“可以批评一切,也可以接受一切。”(《消失了的太平湖》)这是老舍对老北京习性的概括,也在冥冥中成为他个性悲剧的写照。
不同的个性常常会在命运的冥冥安排中发生碰撞。由此上演出无数“文人相轻”乃至相斗的一幕幕悲喜剧,已如前述。还有那些一个个值得探究的社会、文化、思想、法律问题。
读韩少功、王尧对话录《大题小作》,其中韩少功对当代名著《芙蓉镇》的批判耐人寻味:《芙蓉镇》在表现国企员工与个体户的矛盾方面显得“肤浅和虚假”,并且断言“没有任何地方的‘文革’史料可以支撑《芙蓉镇》这种虚构。”事实究竟如何?可惜不见古华的回应。
显然,文本不是文学的全部。在文本之后、之外,还有多少人心的活动、人与人的斗争、人与权力、时势的周旋以及淹没在历史深处的种种说法,惹人遐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