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哈德:真正的控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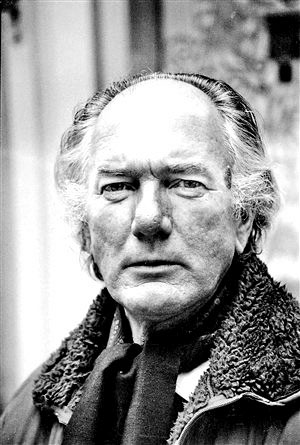
托马斯·伯恩哈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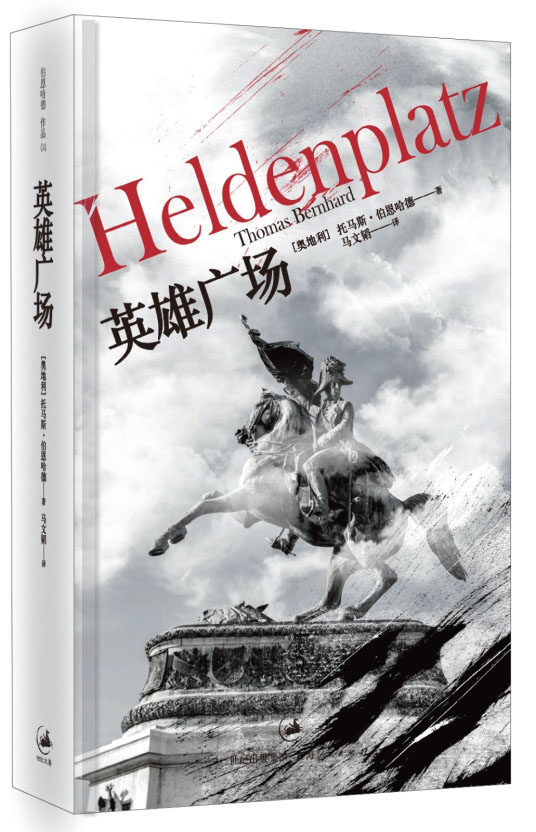
5月,我去天津看了陆帕版的《英雄广场》。从第一场的沉闷到第二场热血沸腾,(我几乎想突然打断演出,给予鼓掌或尖叫)再到几近恐怖的第三场,结尾的声响效果使我不自觉堵上了耳朵。
相比直接采用剧本演出,陆帕更钟情于小说改编,那些脱离戏剧冲突的细节或者留白部分更为吸引。那些确切的细节和缓缓移动的场景,所传达的心理和情绪要远大于故事。而且,他所有戏剧的统一性更体现了他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所说的,“戏剧是通过导演去了解人的方式,而演员则是通过不同的角色了解自己”。而在伯恩哈德的原作中,我们也看到了不厌其烦地寻找和确认自我的过程。也许,这正是伯恩哈德吸引陆帕的地方。
在《英雄广场》《历代大师》《我的文学奖》《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中,我感受到一种激烈的情绪,就像帕慕克说的那样,“在那些书页里面,欣然接受他那无法遏止的愤怒,并和他一起愤怒”。另一方面,理性又驱使我去沉思这愤怒从何而来。于是渐渐地从敬佩、同仇敌忾,走向更为广阔的情绪。童年的被遗弃、少年时期的教育、战争、差点把他送进棺材的疾病,以至亲故的离去,都给了他深重的打击。他依靠写作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批判与死亡成为他书写的两大主题。他的每一部作品,仿佛都是死亡的操练:与死亡斗争,又与死亡和解,这是一个满身伤痕,即使到临了过上所谓幸福生活,也要通过批判来安抚痛苦和死亡伤痕与记忆的人。直到生命力快要衰竭的最后,他还是写出了振聋发聩、颇受祖国非议的剧作《英雄广场》。他所批判的对象,涉及到国家的政治、宗教、文化、教育、艺术等等。似乎所有行业的人群,都能够从他的作品中获得愤怒和深思,正如伯恩哈德当年做法庭记者时的老上级赫伯特·莫里茨所说:“有关伯恩哈德的讨论将越来越成为一个专业课题,我指的不仅仅是文学专业。”
《英雄广场》的故事情节很简单。法西斯占领奥地利50年后,舒尔斯教授仍然不堪忍受国家的种种,(包括自己与家庭)最终选择跳楼自杀,之后,他的仆人和家人分别从不同角度讲述他的过往,并在葬礼后聚餐,已经患有精神疾病的教授夫人不堪当年广场噪音幻觉骤然身亡。
陆帕的舞台设置是极简主义的,色彩也极为素朴,随处透露着死亡与阴森的气息。语言成为这部戏剧的主要表现方式,连演员的行动也是微弱的。陆帕将伯恩哈德的原剧作伸出去的支离、芜杂和绝望的边界都给芟夷了。这种低调、沉静、简约的甚至有些静谧的表达方式,逐渐绽开了一种强大的破坏力量,甚至要比伯恩哈德外向式喋喋不休的叩问和呐喊来得更为猛烈,可以说,陆帕几近精确、晦涩、甚至神经质地复活了伯恩哈德。
第一场是寂静的铺叙,冗长与沉闷,也暗示了家庭温情世界的瓦解。两个仆人一边整理衣物,一边讲述舒尔斯教授的生活。这暗示它不是纯粹的反权威、反暴政的政治戏剧,而且是一种对自身所属家国序列的厌倦。女仆齐特尔夫人则和他关系密切。舒尔斯教授除了指导她做家务外,还建议她给92岁的母亲读托尔斯泰、果戈里。年轻的女仆赫尔塔则静静倾听,间歇性地反复陈述舒尔斯教授要带她去“格拉兹”。她是剧本中惟一失序的人物,来路不明,善于偷窃;无人问津又认真缅怀主人公;似乎理解死亡,却又蒙昧地陷入极端的悲伤。陆帕使她幽灵般地成为一种象征,或者僭越者,在第三幕结尾,缓缓地面对观众戴上了象征着教授夫人地位的黑纱帽。这是原剧作所没有的。
齐特尔太太漫不经心的讲述,复活了教授的形象。在舞台上,陆帕还让这回忆成为布景上的一个倒影(这种一边舞台演出,一边播放纪录片式的片段的时空折叠法,好像已经成了现代戏剧的某些标识)。叙述展现了教授狂躁的一面:一方面他希望仆人能够接受他安排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秩序;另一方面,又憎恶外在的秩序。他的妻子因当年英雄广场的纳粹带来的破碎记忆而患病,想要移走餐厅,但他坚持要近邻英雄广场的餐厅。两个“从事人文社科独身”的女儿让他更加厌恶,她们继承了他,成为下一代自私、专断、冷漠的人,同时也是他的“掘墓人”。在精神生活上,他将是否喜欢萨拉萨蒂、古尔德作为判断“同路人”的标准:“不喜欢古尔德的人是危险的人”。他在家里执行着暴政,所有的亲人都背离了他,顺从的齐特尔太太成了他精神亡国的惟一臣民。他只允许他的兄弟罗伯特教授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只有他是他精神上的孪生者,就像尼采说的,“一切创造者,都是铁石心肠”。他在寻找英勇的同道,却以近乎苛责的方式来对待周围的人。
第二场舒尔斯教授的葬礼刚结束,弟弟罗伯特和教授的两个女儿在人民公园的长椅旁逗留。罗伯特拄着双拐,很难靠自己的力量站立,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喷薄着愤怒的光芒。和两个孩子相比,他毕竟久经沙场;与已经死去的哥哥相比,他又是一个善于忍受的人。这一场采用的是先抑后扬,罗伯特叔叔拒绝“胆大好斗锋芒毕露”的侄女安娜的请求——为诺伊豪斯修路抗议的签名,除非“他们要把我的房子夷为平地”,他“退缩到自己的内心去找庇护”,在侄女的义愤填膺之下,他的真正自我爆发,他揭示了这个国家的一切问题,从政党、宗教、知识分子、作家、文艺界,到任何一个角落。仿佛他才是真正的控诉者。“你眼前的一切都是丑陋不堪,都是彻头彻尾的愚钝,无论朝哪里看一切都在衰败,无论朝哪里看一切都在荒芜……从根本上说我很能理解你们的父亲,我感到奇怪的是,奥地利人民竟没有早就全部自杀。”“可怜的尚未成年的奥地利人民,所能做的只剩下演戏了。”
第三场,罗伯特喋喋不休地继续揭露着这个国家不可救药。他不仅炮轰国家的虚伪和愚钝,还愤怒它失去主体性,一个曾经充满艺术独立性的欧洲民族,却开始处处模仿美国。城市缺少自我,市民是屠戮者,独立的个体只可能隐遁起来。他甚至还呼吁那些在他看来麻木的人,“你不要忘记,您所在的国家公众遭受危害的程度首屈一指,在这里愚蠢在发号施令,人权遭受践踏……”最后,舞台上的教授夫人看向观众,而她濒临崩溃的静谧被窗台玻璃的破碎声打破,这与伯恩哈德剧本中的猝死不同,却带来同样的震慑力量。
这部戏被人们惯常地认为是反思纳粹及其恶劣影响的作品,但通过作品能够感受到这种情绪的强烈延伸,所有人都在外界找到一种卡夫卡式的“纳粹”时,才是更深层意义上的存在之痛。《英雄广场》中教授的自杀,可归因于堕落庸俗的奥地利文化,如《历代大师》中雷格尔妻子的“死”也要归因于充满缺陷的环境,正如主人公反复念叨的:如果广场上的雪及时铲干净,妻子便不会摔倒,如果早点抢救半个小时,就不会拖延治疗,如果不是庸医,就不会导致死亡。这个逻辑强大、无情,甚至近乎苛刻,但却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它表达着任何一点糟糕都要被清除出去的暗示,而世界永远处于不完满中。
与死亡密切相关,我们在作品中看到伯恩哈德内在的艺术谱系:作家、画家、音乐家。《英雄广场》中的舒尔斯教授也是在艺术无效的情形下才选择死亡。他谈到“艺术个人主义”:“几乎不能容忍除我之外还有别的人拥有和享受这些艺术家”,但同时,他又无法想象别人不能理解和喜欢古尔德、萨拉萨蒂。在《历代大师》中,他对艺术的缺陷了如指掌,用一种近乎夸张甚至诅咒的方式将其大卸八块,这种方式和艺术品之间构成某种势均力敌。愈是艺术个人主义的,愈是亲近的,愈是孤独的,也愈是真诚的、危险的和缺陷的。
伯恩哈德的作品有一个明晰的线索就是“自杀”。偶然的诱因是1938年纳粹横行时,《英雄广场》中教授最小的弟弟在诺伊豪斯跳窗自杀,这当然和伯恩哈德的经历密切相关。他外公的哥哥死于自杀,童年时听外公反复做过哲学与文艺式的描述;父亲在30多岁时也酗酒自杀,他童年时曾因不堪忍受纳粹少年训练营的教育试图自杀,甚至目睹过几个同学的自杀,而战争的死亡气息时刻在他的身边弥漫:“我要活下去,所有其他的都没有意义……这是一个已经放弃努力的人,在看到别人在他面前停止呼吸的情形时,所做的决定。”伯恩哈德的后半生一直在逃离死亡,“向死而生”。他毫不留情地洞察国家、社会和人性中的庸俗、无能、贪婪。即便后来他遇到人生中的“母亲”——年长他30多岁的贵族寡妇海德维希·斯塔维安尼切克,也没有让他的作品主题变得明朗温暖,而是有条不紊地保持着关于死亡主题的创造力。在戏剧中,他把死亡和世界的不完备放在一起,用近乎病态或者将死者“其言也恶”的真诚语言,唤醒沉睡的读者和观众。有意思的是,他的作品有一种近乎喜剧的荒诞和夸张,这似乎也与死亡有密切关系,他说,“谁在垂死的病榻上,还能写出喜剧和笑剧来,那么他就无所不能”。《英雄广场》结尾,教授的儿子卢卡斯还打算与新认识的演员女友去观看喜剧《明娜·冯·巴尔海姆》,这不是对卢卡斯的简单否定,而似乎暗藏着一个隐喻。
《英雄广场》上演后,引起了国内观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和戏剧人的大讨论。他们认为《英雄广场》是一部演给中国人看的戏,因为我们在这样一个“自毁家园的叛徒”中陡然看到了自己的家园的影子。然而,正如陈丹青所说,伯恩哈德的作品虽然充满伤痕之“嗔”,但我们仍然缺少这方面的戏剧美学的建设。我们不能只是看着陆帕的戏剧意淫。乔治·斯坦纳说:“文学批评应该出自对文学的回报之情。”实际上,从艺术批评甚至伯恩哈德所有的批评领域,都应该这样给予回敬。这位甚至看起来比鲁迅还要激进的批评家对我们来说有些遥远,我们缺少这样的真诚、勇气和魄力,甚至能力。
另外,《英雄广场》还启示我们:小说与戏剧的联姻永不过时。那些燃烧着信念和灵性的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伯恩哈德,在被戏剧化的道路上复活,即便这种素朴的“回报”带有某种复制性,包括剧中那些渗透着陆帕的理解的形式上的添加。经典和传统一旦被忠诚的艺术翻新,就属于另一种意义上的回敬。我们还缺少这样的作家,更缺少这样的戏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