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地带》:书写历史 观照当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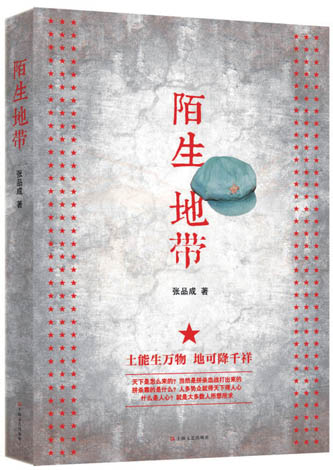
文化的发展通常经历着衰落和勃兴的循环,历史的变迁常常在社会的喧嚣与骚动之后给予人们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冷静和睿智。作为生活记录者的作家们一方面以作家的身份创造和衍生着自己的话语,一方面也以记录员的身份在与其他文本的相互印证中探寻着还未被说尽的秘密。二者在交融中形成一种新的历史话语。而这种历史话语由于在某个点上恰恰触摸到一个民族的秘史,从而具有了烛照历史角落、发现新的历史生活的作用。张品成以新视角切入红军历史的《陌生地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这样的价值。作者通过长达20余年的对于红色历史的触摸与省思,最终形成了一种新的更为客观、理性的历史识见。
《陌生地带》讲述了红军长征前在革命老区江西赣南地区船山地带发生的一段往事。作者巧妙地设置了闭合—开放—又闭合的叙事结构,在完整又开放的空间中展开故事。以失去双亲的兄弟崔工胜、崔工利的悲喜遭遇为主线,以三位种棉高手潘耕晨、涂天让、查恒有的传奇经历为辅线,双线并进,互为补充,在对历史细节的触摸和评价中,更为全面、客观地表达作者对于现实的某种思考。作为一部以新历史主义视角切入的作品,《陌生地带》在艺术风貌上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人民才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它强调人们所认识的历史不应该是历史家独语的历史,而应该是叙述者描述的复数的历史,主张通过多元阐释,更全面地辨识历史真相。它自新时期传入中国,又产生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式变体,成为新写实小说的一个支流。作家们力图通过对被湮没的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触摸与反思,更为本真地追寻历史。《陌生地带》的新历史主义实践首先体现在对历史长河中小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在传统的历史书写中,历史的主体多为英雄人物。但是在新历史主义作家的视野里,虽然也肯定社会能量的存在及重要作用,但是更肯定作为小人物的个人在社会历史事件中的能动作用。甚至可以看出作者隐约包含的历史观,即历史并非是大写的历史,而是小写的历史,人民才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陌生地带》有两组潜在的人物形象。一组是以崔工胜、崔工利、江左、江右兄弟为代表的军人形象;另一组则是以潘耕晨、涂天让、查恒有、杨天亮等为代表的普通民众形象。他们无一例外并无可能被写进史册,但他们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决定或者推动了历史的进程。作者从他们卑微的生存愿望出发,如:崔工胜的入伍就是在天灾之后找口饭吃。三位种棉高手则或是因天灾,或是因为逼婚,或是被恶霸所不容,遭遇了各自的人生困境后,最终走向了革命战争。
人对于英雄主义的独特思考,也是《陌生地带》的特别之处。作品中塑造了最具英雄梦想的两个人,一个是崔工利。小小的他入伍之时,年纪不过十一二,心里却装着和哥哥不一样的梦想。但是,当智慧并没有和年龄及阅历一起增长的时候,热情带来的往往是更大的悲剧。他只想当英雄,却不问战争中的英雄意义何在。英雄梦随着生命的逝去而消失,带给读者深深的叹息和思索。另一个具有英雄气质的人则是洪天禹。这是一个具有封建色彩的现代长官形象。他原本为土匪出身,在历史的因缘际遇中侥幸被“招安”。他确实是怀着一腔热血投入战争的。在“能否做一把尖刀”一节中,作者用非常文学化的手段描述了他紧张、激动的心情。但是,很快英雄的热情就被同僚们的潜规则同化。作者设置这两个人物形象,互为补充,从上而下揭示了历史可能潜藏的虚无:即历史活动掺杂了大量的人的盲目意志和私心杂念。历史并非是绝对理性的、直线发展的。
呈现更加丰满的历史
新历史主义理论并不苛求历史的定论,因为在新历史主义作者看来,“人不可能去找到‘原生态’的历史,因为那是业已逝去,不可复原的,而只能找到关于历史的叙述,或仅仅找到被阐释和编织过的历史”。基于此理论,在对历史进行观照的时候,作家们更注重致力于不同的角度、视点甚或结构故事的方式,以便在历史和文学的互文性理解中去实现对二者的实质性把握。具体到《陌生地带》,作者一方面用具有隐喻性质的人物关系来结构全篇,一方面又在布满悬念的叙述与揭秘中,使得这些历史在不断的阐释中深厚起来。
《陌生地带》呈现给读者的首先是具有隐喻意义的人物关系。作者一开篇便介入了一段矛盾冲突,将崔工胜、崔工利两兄弟令人揪心的现状和深厚的感情呈现出来。父母双亡,又逢天灾,哥哥迫于生计去当兵,却放心不下年幼的无人看护的弟弟。百般无奈间,只好托人将其带入了部队。二人相依为命,却在走进队伍后分裂成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在故事的结尾,作者安排了哥哥开枪打死了弟弟。这样的关系,这样的结局,足够令读者震撼并沉思,二人的隐喻意义也因此而彰显。作品在具有隐喻意义的关系设置中呈现出“一半是历史,一半是寓言”的艺术风貌。
《陌生地带》令读者眩迷的艺术魅力还表现在大量的悬念设置上。全剧有一个贯串始终的悬念,那就是“陌生地带”到底所指何物?围绕着这个悬念,作者铺设了各种小悬念,如露珠闪烁其间,吸引着读者步步深入。其中有两条尤为重要。一条是种棉高手被谁人所雇佣?要去往何方?另一条则是洪天禹的部队到底会怎样发展?在看似必胜的战争中,为何悄然败落?这两大悬念之间既离合又交融,层层推进,最终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既开放又闭合的叙事系统,张弛有度间展现出作者驾驭故事的能力。
总之,作品将历史和文学融合起来,企图通过边缘视角颠覆单线历史,在对人物关系与情节的巧妙铺设中,使我们能在历史的夹缝中更清晰、宽广地看待历史,以便完成自我的批判与思考。但是读者也不可避免地发现 “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处在或关乎某个历史情境的。一切文本都具有社会历史性,是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体制和阶级的产物”。任何作家通过文本来建构历史的时候,不可能完全脱离自己所处的历史语境而单独存在,作家以阐释者的身份在想象和虚构中进行着对“讲述话语的年代“和”话语讲述的年代“的双向辩证,传达出自己对历史现象的价值判断。
细节的介入使历史更加鲜活
战争是人类的灾难,是人类文明史的丑恶伤疤。因而作家们对于战争的书写大多集中在对战争场面的描写上,以此来彰显战争的残酷本质。血与火的交织,英雄与失败者的残酷对比,虽然令作品情节跌宕,激动人心,但在某种程度上,历史成为胜利者单一的历史,个人真实的意愿被掩盖在对成功者光荣事迹的讴歌中。《陌生地带》独辟蹊径,作者不从宏大的历史事件进入,而是通过重新选取战争场景,将各种被主流文化所摈弃的边缘性文化因素考虑进来,诸如风俗、佚文、轶事等,力图开拓出战争题材场景选取的新道路,在更广泛的视野里,重新思考历史。
个人的失去,是文学最大的损失。《陌生地带》在战争场景的选取上以战争中的人作为切入点,不仅毫不避讳地书写他们在战争中最真实的心理场景,更开拓性地抓取了历史记忆中民众自发的反战场景,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作者描写战争中敌对双方的士兵,笔墨的重点却不在如何的仇视,反而写出了他们不得不面对战争的无奈。如,当戏班不能如期唱戏时,富有经验的战士嗅到了即将到来的战争气息。“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像蒙了一块抹布。”而在平时的时候,隔着江水两岸,他们彼此熟悉,互相起着外号,甚或坐到一起吃饭,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这段令读者颇感新奇的生活片段。
《陌生地带》非常重视对于风俗、轶事等的描写,如“三僚就是这么个地方,每家每户都从事算命看风水。远看近观,那地方的风水也不错。远看,屋宇田陌走向,状如太极。”将人物放回到现实境遇中,既增强了作品的地域特色,也增加了真实性和说服力。细节的介入,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同时也补充了历史的完整性,使得人物血肉丰满,真实可感。
对战争场景书写的拓展,来自于作者对于历史的深入挖掘。我感喟于张品成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努力。他用5年的时间,两次重走红军长征的路线,不止一次只身涉险,甚至遭到猛兽袭击。用这样的方式看到的,自然不会是已僵化在文字中的定史,而多了一些鲜活,有了一份厚重。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作者对当下的思考和焦灼。
总而言之,《陌生地带》是张品成承继他在历史和文化的变动中找寻隐藏的历史话语的努力,意欲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的角度对历史进行重新解读和定位。在对船山革命历史的书写中,体现出作者对当下生活的一种观照。
(《陌生地带》,张品成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