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商人的特异风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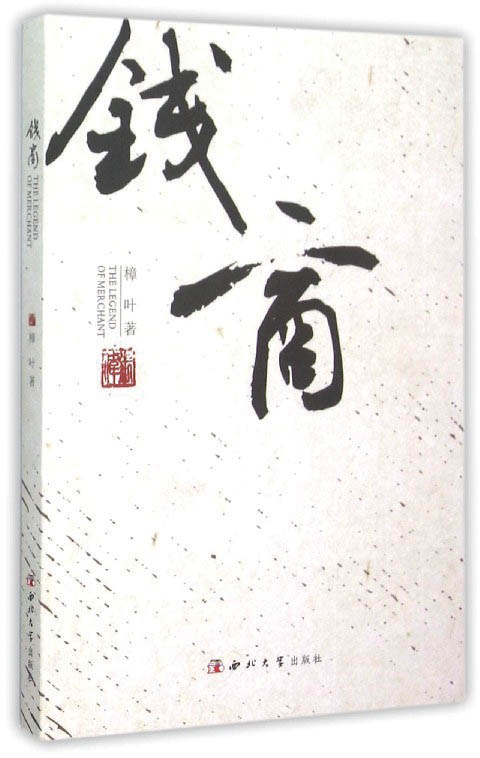
在我的印象中,樟叶的长篇小说写作,或在题材上写人所少写,或在内蕴上言人所未言,常有令人意外的拓辟与发现。他的《五福》写近代陕西的辛亥革命,《晚春》写民国期间的西安围城,《石语》写景教碑的盗与护的交锋,都是他擅于开生面、走蹊径的一个个例证。新近推出的长篇新作《钱商》,聚焦于晚清时期的陕西钱庄商人的货殖营生,写陕西渭南的畅氏家族在生财求利中的励精图治、与时俱进,由此描摹出了一幅晚清时期陕西商人锐意进取的壮阔画卷。
我在阅读中感受较为突出、印象也更为深刻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作品对于晚清时期陕西钱商影影绰绰的历史的钩沉与打捞,二是对于陕西关中钱商从性格到精神的内在歌吟。这两点就使得这部历史题材的作品做到了常中有异、平中见奇。
对于陕西人,一般人都会有一种误解,那就是精于文墨而拙于经商。实际上,自明清时期起,陕西商帮就名闻天下,以“西秦大贾”、“关秦商人”的名头,跻身于全国十大商帮之列,甚至与晋商、徽商相齐名。明末清初的科学家宋应星就曾说过:“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但这样一些崛起于西北、影响至全国的史实与史事,在今人笔下,多见于史著与史料,很少见诸于文学作品,因此,陕西商人曾有的辉煌本事,就鲜为人知。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钱商》一作显示出了他的独步一时和无可替代。作者不仅饱带一种为历史上的陕西商人鼓呼和代言的热切激情,而且也发挥了他着意为陕西商人描形造影的文学才情。他在深入调研和细切爬梳陕西商人的史迹与史料的基础上,切近历史本相和人物原型,进行艺术概括和文学想象,以渭南畅氏家族为主干,连缀起兴盛号钱庄西延兰州、南下自贡的两条线索,勾勒出晚清时期陕西商人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作为与意义。可以说,仅就使陕西商人进入文学殿堂而言,这部作品就自有其重要的价值。
当然,《钱商》一作不只是以点带面地再现了陕西商人的辉煌历史,描画了陕西商人的憧憧身影,作品更令人为之惊喜的是,还以如椽的大笔塑造了畅方正、畅以训、杨茂堂、罗玉梅等栩栩如生的陕西商人群像。畅方正运筹帷幄中的持重儒雅、畅以训精明强干中的高瞻远瞩、罗玉梅贤淑良慧中的不让须眉,都以高人一筹的智商与情商,既构成了畅氏家族的骨干力量,又代表了陕西商人的精英群体。他们顺应着时局的发展,适应着市场的变化,不断调整经营方略,使长安兴盛号钱庄由钱币流通向小额贷款转换,又由贷款向茶叶、石油领域倾斜,写出了他们在审时度势的运作中,使传统的金融业务走向复式的实业与工业的过程。由烟麻丝茶的经营和陕北石油的开发,显示了以畅氏家族为代表的陕西商人由传统型商贾向现代性商人转变的过程;与地下钱庄的殊死较量,与潜藏的不法之徒呼延松的周旋斗争,又体现了陕西商人的惩恶扬善与去邪扶正。这样一些持守规则和维护正义之举,又使以畅氏父子为代表的陕西商人,充满了秦人的刚劲豪气与民族的沛然正气。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曾经说过:“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钱商》里的畅方正、畅以训等人,低调而实干,言利又言义,都堪为秦人里的豪士、商人里的君子。
《钱商》一作细细读来,也还会有描写不够细切、看着不够过瘾的缺欠。这主要是作者把笔墨过多地放置于各种事件和各地实业的铺陈上,使得主要人物在血肉丰满和气韵生动上,都留有明显的不足。这也给作者在这一题材上的继续开掘,留下了一定的余地。因而,我满怀希望地期待着作者在这一题材领域里新的探索与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