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写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
吴仕民长篇小说《铁网铜钩》
谱写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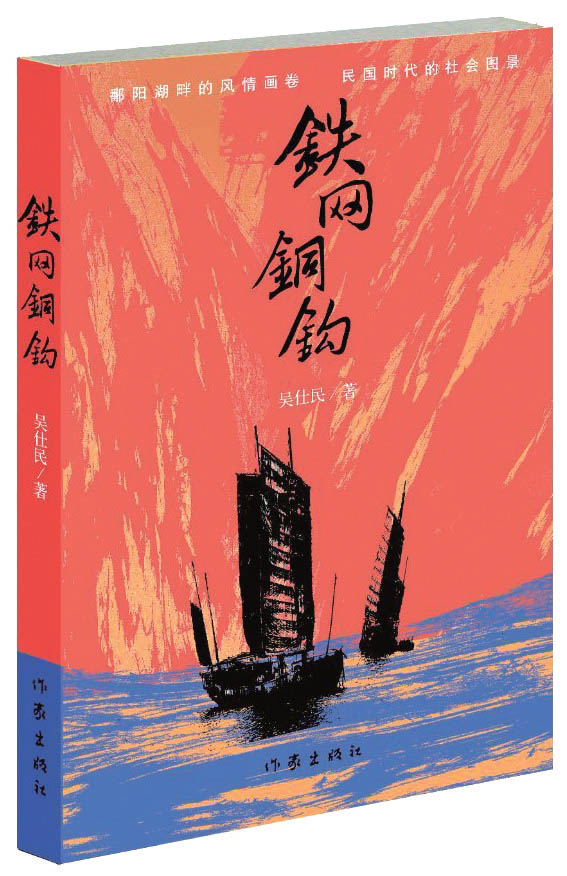
这是一部气势恢弘的作品。作者笔触探向鄱阳湖北宋以降、元末明初及至民国千年历史风云,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灵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精心布局,由世居鄱阳湖畔铜钩赵家与相隔不远的铁网朱家两村500年前划定湖界衍生的世代恩仇为主线,描绘出惊心动魄的人间悲喜剧。
作者十分熟悉鄱阳湖历史脉络,驾驭作品得心应手。通过作者的笔端,让我们看到了鄱阳湖的真实历史。日月更替,山河换形,这片水域逐时而长,变成纵横800里的水乡泽国,成为中华大地第一大淡水湖。湖名起初叫彭蠡,也叫彭浦,在秦汉时定名为鄱阳湖。当然,作者笔锋是从赵氏北宋王朝灭亡南迁而来的赵姓村落和与明朝皇帝朱元璋似有丝丝缕缕关系的朱姓村落开始。在传统的宗法制度下,小村往往受到大村大姓的欺侮和挤压,只好带着怨恨,无奈迁往外地,留在湖边并占据有利位置的都是大村大族大姓。也正是在这大村大族大姓间,在鄱阳湖上常因捕鱼发生冲突,往往由争吵、对骂到挥拳动脚,甚至动刀动枪,造成伤亡,留下血的教训。但是,几百年的恩仇,在抗日大义面前,赵家和朱家道出共同的心声:“日本人是心腹大患,村子间的争斗只是手足之痛。”放弃前嫌,携手抗日,书写出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
小说人物众多。从朱元璋、陈友谅到蒋介石,从统帅到士卒,从族长到村民,从县官到地痞、土匪、赌徒、妓女、汉奸,描写了诸多人物的众生相。这些人物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长篇小说成功与否,其实就看人物群体是否塑造出来,人物的个性是否突出。显然,《铁网铜钩》成功了。仁生的父亲被铁网朱家人打死,临死前父亲叮嘱他“不要想为我报仇……两个村世世代代结仇、报仇,就会成为永远不能了结的仇恨……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了,离开……”这件事,在他幼小的心灵如刀刻锥刺般留下了深深的、痛苦的印记,他似懂非懂地明白了父亲临死前对自己嘱托的含义。然而,爷爷始终强化着这一恩仇,“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不报父仇,不是好子孙。你父亲在地下会不得安宁,我死了也不能闭眼。” 仁生面对爷爷和父亲两个遗嘱,并且内容充满矛盾,应该遵从哪一个?他必须做出人生艰难的抉择。仁生已经学得铁匠手艺,在贪得无厌、虚伪奸诈的县长拖延搅合下,鄱阳湖波诡云谲,赵朱两个家族蓄势待发,准备大举械斗。仁生并不情愿地被推举为“铜钩赵家”领头人。而在此后,由仁生为主线,将赵家和朱家所有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推演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故事,小说也由此显得十分厚重。
小说语言特色鲜明。“船拗不过舵,人拗不过命”,“人生充满烦恼,风来浪也白头。”这是《铁网铜钩》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告诉读者的一道人生哲理。“有万年江山,无千年皇位”,又道出了一个铁定的社会规律。“出得征便挂得帅”,这是社会发展步伐所确定,果然时势造英雄,仁生这一代人,虽与当地百姓在“刀尖上过日子”,但“渔民们离不开湖水,就好像婴儿离不开母乳,所以渔民们还得冒着风险向风里浪里行。”在特殊历史时刻,赵家和朱家三代人,同仇敌忾,共同抗日,掀开充满民族豪情的一幕。但是,抗日战争结束了,县里也来了新县长,人们生活状况似乎没有任何变化,日子过得更紧,对鬼子投降后生活会改善的希望逐渐破灭,打败鬼子的喜悦早已被生活中的窘困、忧虑所取代,人生悲剧还在上演。朱家认为“桥归桥,路归路”,“鬼子走了,亲人还是亲人,仇人还是仇人。”新的更大的武装械斗正在酝酿,仁生虽然想到械斗的后果将不堪目睹,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显得十分渺小,他试图阻止这场械斗,却被自己同宗同姓族人五花大绑,准备以他的人头来执行族规。“江河改道,就不应在旧河道上行船,而应在新河道上摇桨。”小说以独有的水乡语言告诉读者,“鱼游满江,船走四方”,水泽之上,渔家竟是“以湖为家,天当被来船作床,风雨无阻,日夜出没在风波之中”。现在,当千船万人云集鄱阳湖上,准备相互残杀之际,出现了历史性转折,解放军的三艘帆船将两个家族的船队分开,那个敢于抗婚的朱小鲤,一身戎装立在船头,向朱家和赵家喊话:“铁网村和铜钩村的父老乡亲们,我是朱小鲤,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现在我们县解放了,全省和全国都要解放了。……不能再延续旧社会的仇恨,不要再以刀枪对准自己的兄弟,不要让旧的观念、旧的传统像渔网渔钩一样束缚我们。大家收船回去吧,我们要把心连起来,把手拉起来,在鄱阳湖边共同建设美好的新生活!”这种独到形象的语言描述,给小说平添张力。
《铁网铜钩》细节描述十分细腻。小说描写仁生和仇家的女儿朱小鲤有一次很不平常的相遇,居然同坐一条船,桨入水中会把她的影子搅碎,一会儿又会复原。姑娘面对仁生的拘谨,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连水上游动的水凫都惊得赶紧潜入水中,从而在水面上留下一串串同心的圆圈。当仁生快接近村子,一头扎进水中,游回村去,小说细节描写情景交融:小鲤停下桨,看见仁生在水里像鱼一样自由自在,双手有力地划水,身子两边溅出层层浪花,搅起圈圈小浪,那小浪一圈又一圈地扩散,一直荡漾到船边。她很想看看仁生在水里游泳时那纹在背上的鲤鱼是什么模样。但不知为什么,一泛起这个念头,她觉得自己的心跳有些加快,心里也好像涌起了圈圈细浪。就是这样一对年轻人,相互承诺又失之交臂,最终处在命运不同交叉点上。朱小鲤成为解放军战士,站在解放家乡的队伍行列里;而仁生却被同族人第四次强征(土匪、日寇、国军都抓过他),被动地站在准备大举械斗的船头。或许等待着他的是另一种命运的归宿?小说在此戛然而止,却是余音袅袅。
《铁网铜钩》作者对鄱阳湖一带风俗民情、人文掌故运用自如,使小说趣味横生。在讲述赵、朱两个家族历史渊源时,小说描述为了利于防范冲突,史上对捕鱼工具也作了规定。朱家只得使用网具,包括大网、拖网、丝网、罩网、耙网等等;赵家则只能使用钩具,包括大钩、小钩、鱼叉、铁刺、卡子等等。因此形成了后来的“铁网朱家”和“铜钩赵家”两个独特村名。这一特殊的人文故事,使小说特点凸显,也由此铺垫通篇小说的伏笔。在描绘铜钩村时,有一组画面映入眼帘:一群小孩正在玩“十字棍”游戏,孩子们分成两拨相对站立,每人手里拿着一根五尺来长、大拇指般粗的竹棍。游戏规则是,一方用自己手中竹棍猛向对方头部砸去,被砸方可以用手中竹棍横起招架遮挡,也可以闪身躲避,并迅速攻防转换,击中对方则为胜。据说当年太平天国军队路过这里时,童子军训练有这种套路,被赵家村人传习下来。小说不经意间将此游戏与历史渊源衔接起来,突显了其人文价值。小说还讲述了一些奇特的风俗,比如小孩生病,当地忌说小孩有病,而称“做狗”。渔家的营生在水上,这是当地的民情所在,小说娓娓道来:“三日不下河,吃掉一只老鸡嬷。”就是说三天不出船捕鱼,就得吃老本。而对于当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上的征战典故,更是讲述得绘声绘色,使得小说具有了独特的人文品格。其实,一部作品的价值,除了它的艺术创造,还要看其人文内涵。具备了这些,一部长篇小说便会自立于读者面前。这恰恰是《铁网铜钩》的特点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