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与接受——《新诗十讲》(孙玉石)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6月02日12:05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孙玉石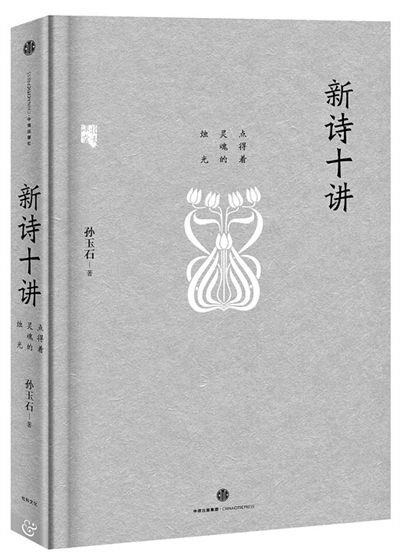 孙玉石 著 中信出版社
孙玉石 著 中信出版社作为入选“2015年度中国好书”的《新诗十讲》,作者用诗的语言,全方位咀嚼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经典新诗,以及其背后的时代与国家、文学与爱……通过富有生命感的精湛解读,深入挖掘了中国新诗创造者所传达的意向、美学与思想,为我们打开诗歌审美世界的大门。
中国新诗,摆脱旧体诗而独立萌生发展,自二十世纪的1917年以来,到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已经走过了九十多年的历程。从刘半农、郭沫若等或写实或浪漫或明白易懂的白话诗,经过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等人的象征派、现代派、意象派诗,到二十世纪80年代后产生的朦胧诗、后朦胧诗,以及现今各种各样表现方法复杂多变的现代诗,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艺术趋势,是作者的传达方式越来越追求复杂和多元,对于诗歌的阅读与接受,也越来越多了一些隔膜和障碍。也就是说,就这一类表现方法复杂的新诗而言,诗的创造者与接受者之间,出现了比较大的理解上的鸿沟。
新诗自从诞生时起,就存在不同形态的艺术探求和美学差异。伴随这种现象而来的,对于诗的朦胧性和神秘美的讨论,也一直存在反对还是赞成的分歧。如郭沫若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天上的街市》,大多都明白清楚,很好懂。当时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含蓄的作品,如沈尹默的《月夜》:“霜风呼呼地吹着,月光明明地照着,我和一棵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朱自清1935年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里,就没有选这首诗,他认为,这首诗作者表现得“不充分”。其实它所采用的,是一种传统诗里有的,也是新的艺术表现方法:在略带象征性的自然景物与氛围的描写渲染中,具备一种朦胧性和神秘美的特征。
回顾已经过去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值得回味的历史重现。面对文学艺术乃至诗歌的出现,我们作为阅读者和接受者,应该调整和转变已经习惯于阅读“明白清楚”的文学作品的心态,对于那些更复杂更含蓄更富蕴藉的作品,由兴趣的单一而走向多元,感觉上由远离陌生而接近熟悉,审美上由不懂、拒绝而走向认知、接受,使自己从情趣与习惯上“不拒绝陌生”,经过不断地熏陶和养成,提升对于这类有深度“余香和回味”美的作品接受理解的审美能力。
从象征主义诗学方面,如何把握和养成自己进入这类含蓄蕴藉、表现复杂的诗歌作品的观念与方法?最重要的,是要注意把握具有复杂性神秘美的文学作品,从多个方面认识和理解这些诗特殊的传达方法,与我们习惯接受的传统传达方法不同的特点。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从法国的象征派诗创始者波德莱尔开始,提出诗人个人思想感情与“客观对应物”之间“契合”的现代性象征诗学理论,自此产生了通过象征的物象暗示传达感情的诗歌艺术。二十世纪初美国、英国的意象派诗、艾略特《荒原》所代表的现代派,虽然在意象的理论、玄学与象征结合的智性诗理论方面有不少新的发展,但以物的意象象征诗人要传达的感情,还是诗歌现代性追求的一个基本特征。二十世纪30年代李健吾非常简化地说明诗里面传达感情方式的三种形态:写实主义是描写出来的,浪漫主义是呼喊出来的,而象征主义是烘托出来的。我们读一首诗,首先要通过直觉感悟、理性思索、反复琢磨,弄清楚这首诗里的意象、蕴蓄和烘托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这些诗的语言、意象的特殊内涵,以及它们各自之间存在的特殊联系。何其芳在二十世纪30年代说过,这些诗的不好懂,是因为作者创作完作品之后,把语言与语言、意象与意象之间的桥“拆掉了”,读者要追踪作者的想象,自己把桥搭起来。这些诗,在语言、意象的内在联系上,留下了很多空白,让读者靠自己的想象去补充、连接。二十世纪30年代,苏雪林在一篇文章里,道出了李金发那些难懂的诗的特点:“观念联络的奇特”,语言意象上“省略法”的运用,是“象征派诗的秘密”。1935年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里也说:“他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或情感: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的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儿,你得自己穿着瞧。”
为此,这类作品往往使用省略、跳跃、模糊意图等方法,通过对新奇的意象语言的捕捉,对新的哲理思绪的发现,以及内在抒情逻辑的巧妙搭配,创造诗所传达的别开生面和朦胧蕴藉。李商隐的《锦瑟》,因为那些意象典故朦胧地搭配在一起,构成一种情绪的谜,至今解说甚多,却没有定论,而它的美,却为多少人所倾心喜爱。
我曾读过一首短诗《蜻蜓私语》,读这首诗后我这样理解:诗人是写自然的小景物,抒写人生的某种慨叹,也是在以诗论诗、以诗论己,传达自己思考并坚守的诗观。仅从后一角度来看,在这首诗里,诗人是借对“蜻蜓”意象被注入的内涵的独到发现,言说他自己诗歌创造的价值和意义,言说自己一生的艺术追寻与坚守。它告诉人们这样一个艺术创造的真理:自由而辛苦飞翔的蜻蜓,在“金黄的稻穗”中饱吸“营养”的蜻蜓,“你透明的腑脏”所显示的“生命的意义”,乃在于用自己生命“不断的扑捉与飞跃”,而且要永无休止地思考着“怎样才能走出自我的视域”,创造新的大地。诗人张默曾说过:“本来新的艺术领域,就是由不断的探讨,不断的观摩与不断的发掘中得来。”
诗的误读往往来自对于现代诗传达方式的陌生。对复杂的美在一段时间里可能感觉陌生,但接触多了,增强了理解复杂美的东西的敏感性,陌生也就会变得熟悉。郑敏二十世纪40年代写的《金黄的稻束》,过去人们也认为不好懂,但今天看起来,已经很容易接近和接受了。这首诗前些年还进入了高考的试题。
在二十世纪30年代朱光潜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心理上的个别差异与诗的欣赏”的著名文章,谈道“明白清楚”不仅是诗本身的问题,同时也是读者了解程度的问题。“明白清楚”的程度不仅有关作者的传达力,也尤其有关读者的欣赏力,也就是读者修养上的差别问题。他说:“修养上的差别有时还可以用修养去消化”,而“不容易消化的差别是心理原型上的差别。创造诗和欣赏诗都是很繁复而也很精纯的心理活动,论诗者如果离开心理上的差别而在诗本身上寻求普遍的价值标准,总不免是隔靴搔痒”。他借用法国心理学家芮波提出的两种心理原型,将此分为“造型的想象”与“泛流的想象”。而后进一步认为,“生来属于‘造型类’的人们不容易产生和欣赏‘迷离隐约’的诗,正犹如生来属于‘泛流类’的人们不容易产生和欣赏‘明白清楚’的诗,都是‘理有固然’。”朱光潜先生希望由此“彻底认识诗的作者与读者在性情,资禀,修养,趣味各方面都有许多个别的差异,不容易勉强纳在同一个窠臼里”。但是这种心理原型分析理论也有一个局限:忽视了人的后天养成在欣赏作品能力方面的重要性。也就是说,随着个人学术根基、艺术素质、文学欣赏层次的逐步积累提高,他接受和理解复杂的、朦胧惝恍的作品的能力、敏感性,也会不断得到提升。一方面的放弃和迟钝,可能造就另一方面的敏感,更多阅读经验的积累,就会提高人们理解复杂文学作品的能力。
引述自己这些阅读经验的事实,是想说明一个普通的道理:对于晦涩难懂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歌的理解、接受和欣赏的能力,不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心理原型”决定的。我自认自己不可能在“心理原型”上发生从“造型型”向“泛流型”的转变。这种敏感能力的获得,主要还是在后天里,更多阅读一些陌生性的文学作品,积累起来而形成的一种性情、资禀、修养、趣味,同时也获得了阅读中的兴趣、敏感、能力。由此,我也时常告诫自己这样一句话:“不拒绝陌生。”通过自我努力,养成对于陌生难解的作品思考解读的兴趣。
读一些蕴蓄性很强的美丽的诗,往往就像猜一个美丽的谜语。它是一种趣味,一种隐藏美的神秘,一种对欣赏能力的自我挑战,也是一种征服、破解之后爱与美享受的获得。为此,我想给广大读者留一道谜语式的思考题:前些时候夜里,我在晚上睡觉前,翻阅尹宏先生编的《纪伯伦散文诗全集》,偶然读到里面所收冰心翻译的《沙与沫》中,有这样一则散文诗:
斯芬克斯只说过一次话。斯芬克司说:“一粒沙子就是一片沙漠,一片沙漠就是一粒沙子;现在再让我们沉默下去吧。”
我听到了斯芬克斯的话,但是我不懂得。
这里,我请大家猜一猜,这位伟大的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在这段“美丽的谜语”里想告诉人们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孙玉石)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