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个体”的文字——评东西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王干)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4月05日09:59 来源:人民日报 王 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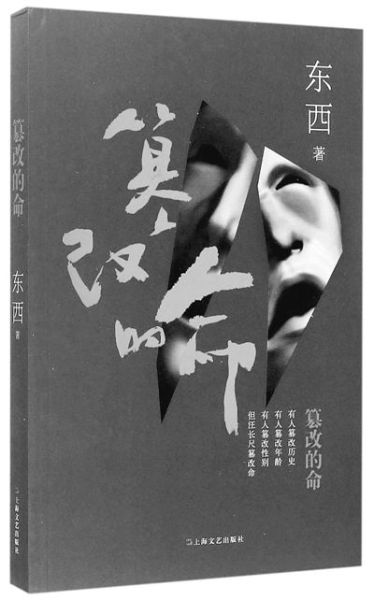 《篡改的命》 东西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篡改的命》 东西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新写实主义小说书写小人物的处境,关注小人物的生活际遇、日常细节。东西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带读者重返上世纪90年代,回到一个社会大转型、价值观大转换的激变期,重新打量小人物的个体命运。社会的巨大发展,付出了道德溃退的代价,强烈的物质刺激让人扭曲、异化,而小人物在历史发展中找不到位置,导致理想缺失或悬空,他们要付出巨大的精力以应付沉重的生活。这些小人物各有各的偏颇和局限,因而最容易受到伤害。《篡改的命》在鸡蛋与石头相撞时,站在鸡蛋一边,对小人物的挣扎投出关怀的目光。
小说中的汪家三代人,并不是90年代后小人物的代表。历史学家考量历史进程、推动社会发展时抓大放小,而作家的价值却是在书写独特个体时,烛照一颗因困惑而幽暗了的心。写“个体”难免显得偏颇,但可以构成“片面的深刻”。《篡改的命》强调每一个小人物个体的重要性,强调小人物也应该分享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的成果,警告人们人性的病变——甚至整体的异化正在发生——是全球性的危机,具有普遍意义。
《篡改的命》中的主要人物,都属于独特的个体。父亲汪槐曾被人顶替,失去成为工人的机会,儿子汪长尺高考过线未被录取,汪槐去“死磕”,结果未能如愿,还失去了双腿;汪长尺高考超线20分,被人顶替,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没有成为知识分子,更没能成为汪槐期待的“干部”,日子过得糟糕,最后为了改变儿子汪大志的命运而自杀;汪大志被汪长尺送给了林家柏,汪大志过上好日子后获悉真相,却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身世。当然,在这些人物生活的时代,他们的代表性并不强,特定的事件、特定的性格、特定的条件、过多的偶然,可以是事实,可以成为新闻,却不能认定其典型性和普遍性。汪槐和汪长尺能够让读者感动,主要是因为他们作为“父亲”的这一身份,而不是他们的偶发际遇。但他们在这部小说中的价值却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时代身份,他们是独特的个体,转眼就消失在时代的背景中,被遗忘。
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也写了这种历史大背景中的小人物。该小说中有比汪家父子更独特的小人物,名字叫奥斯卡,他是一个侏儒,不仅外貌独特,而且具有特异功能,他的尖叫声能击碎玻璃。奥斯卡也是命运的篡改者,他不希望自己长大,所以跳楼,结果真的不再长高;他把自己投入疯人院,因为厌倦了自己的生活,希望安静地回忆往事。假如把格拉斯笔下的奥斯卡和东西笔下的汪家人比较会发现,他们虽同为小人物,不可能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但身上的“能量”有区别。汪槐始终是一个被动者,他没有更改个人命运的能量。汪长尺篡改了儿子的命,却是一个灰暗的失败者。格拉斯笔下的奥斯卡则不然,他不断地主动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被命运之手玩弄,所以,奥斯卡是一个从心所欲的成功者。成功者的悲哀和失败者的灰暗,前者是反衬,后者是烘托,笔法不一样,但都是走向一条命运的下坡路。他们是历史缝隙中的独特个体,处在被遗忘角落的活生生的小人物。
奥斯卡把自己投入了疯人院,汪长尺则选择了自杀,这都是小说艺术中个体消失的形式。汪长尺的消失具有隐喻意味。与其说汪长尺是在和富人林家柏进行对抗,不如说是汪长尺在和财富对抗。汪长尺穷困潦倒,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更无法改变儿子的命运,于是,匿名将儿子送给膝下无子的林家柏。以父爱为桥梁,精神向物质投降。财富以一种最权威的声音,覆盖了汪长尺的人生,宣告他不配谈父爱——为了儿子他可以喝林家柏的尿,可以自杀,他可以成为一个“影子父亲”,却无法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父亲。在这场与财富的对抗中,汪长尺不堪一击,被财富所淹没。实际上,这样的个体,已经不再具有“人”的光辉,他从“人”中消失了,而不是从“集体”中消失并最后独立出来。
东西通过人物的悲剧命运,表现了人不断地丢失作为“人”的精神和个性的过程:汪槐从一个“死磕”的人,变成一个不顾颜面的乞讨者;汪长尺由一个超过高考录取线20分的青年,变成一个隐忍不发戴着“绿帽子”的底层中年人,他失去了成为大学生的机会,进而失去了“丈夫”这一身份,最后失去“父亲”这一身份。东西把人在压力下的一次次退守,一次次煎熬,一次次收缩,描述得非常清晰。汪长尺的这一特征,在西方小说的人物塑造中,是难以想象、几乎不可能出现的事情。西方电影理论特别强调,一部电影的主人公应该是一个主动者——而不是一个被动者。因为只有主动者才能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从而成为故事的主角。一个不具备生命能量的人,几乎不算是一个故事的合格主人公。我们可以说:《篡改的命》是一部书写了一种东方型人格的小说。当代中国社会,实现了从“集体”到“个体”的转变,中国文学也实现了从对“群体”的书写到对“个体”的书写的转变。在这些转变完成多少年后,东西在《篡改的命》中书写了“个体”的消失,再也没有“群体”作为归属。汪槐、汪长尺们,改变命运的少数机会一旦被剥夺,在自由竞争中很难获得优势,可是,他们改变命运、过好日子的愿望却比任何人都强烈——强烈而盲目。这一书写,展露了20世纪90年代以降,社会底层小人物价值混乱、暧昧,贫富差距引起的欲望与迷失。
消失的个体,建立在作家东西具有开拓意义的艺术创造之中,是精神图谱的呈现,提醒我们注意那所见的,也要注目那所不见的隐藏世界。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